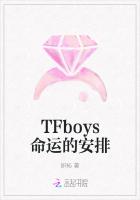如果说,知县的徇情,还有武松曾为自己“上京去了这一遭”的关系,带有某种私心;从小说的故事情节中,我们却看不出陈文昭与武松有任何的关系,他也没有收受武松贿赂之嫌。他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会为武松枉法,分析起来,完全是因为他本人“常怀忠孝之心,每行仁慈之念”,正是在孝义这一点上,陈文昭与武松有了共鸣,产生了“哀怜武松是个有义的烈汉”的感情。因为长兄为父,父母之仇不共戴天,武松为兄报仇就是行孝;兄弟之间则讲究一种义,故为兄复仇还是在行义。而作为当事另一方的那些人,却是有失人伦:潘金莲本就是个“若遇风流清子弟,等闲云雨便偷期”(第二十四回)的行为不端的妇人,对武松亦百般挑逗勾引,更与西门庆通奸,已犯淫罪。“万恶淫为首”,在那个时代,单这一点已可处潘金莲死罪。何况她还伙同奸夫害死亲夫,罪当凌迟(参《元史·刑法志一》“奸非条”,《元史》卷104)。而西门庆则不仅引诱潘金莲成奸,且为人“奸诈”,“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放刁把滥,说事过钱,排陷官吏,因此满县人都饶让他些个”。王婆呢,乃是个“为头是做媒,又会做牙婆,也会抱腰,也会收小的,也会说风情,也会做马泊六”的人,又是她设计将西门庆与潘金莲牵合成奸。这两人既是地方上的恶势力,又是这桩通奸杀人案的罪犯。在一个“常怀忠孝之心,每行仁慈之念”,“平生正直,禀性贤明”的官员面前,潘金莲等的罪孽无疑更其深重了。陈文昭面临着一种抉择:杀武松以执法,有干伦理的维护和发扬;要维护光大伦理就必须“枉法”,从小说情节的发展看,我们可以作出肯定的判断:伦理的因素,增加了陈文昭对武松的“哀怜”、也增添了他对一干罪人的痛恨。在律令与伦理矛盾的时候,陈文昭本能地倒向了维护伦理那一边,使得他不惜“枉法”为武松开脱。就是知县的为武松开脱,小说也说他系“念武松是个义气烈汉”;省院官员的为武松开脱,除了陈文昭的事先为其“干办”外,也有武松“系报兄之仇”的原因。省院议罪说:“据王婆生情造意,哄诱通奸……唆使本妇下药毒死亲夫,又令本妇赶逐武松,不容祭祀亲兄,以致杀伤人命:唆令男女,故失人伦,拟合凌迟处死。……”这判词几乎处处扣住“人伦”二字,诉说着潘金莲、王婆、西门庆的丧伦灭理,其用意至为明显:是要用人伦来与律令抗衡,取得上官和社会的认同,达到为武松减罪的目的。作者写陈文昭们的枉法,实亦是为塑造武松的理想人格精神服务的:官员们都为其精神所感动,不惜自己掉官帽而为其开脱。于是武松成了“天人”。
一部大家都认为是完全写实的作品在这里似乎变了味,向着抒写儒家的道德理想偏移。或者说在这里,作家将反映现实与抒写理想结合了起来。
再来看石秀杀嫂的故事:杨雄的妻子潘巧云与和尚裴如海通奸,被杨雄的义弟石秀发现。石秀用计先杀了裴如海和给裴如海通风报信的头陀,又与杨雄一起,在翠屏山杀了潘巧云和丫鬟迎儿。杀人后两人亡命梁山。
这竟是个连官都不报就私自报仇杀人的范型了。
同是杀嫂,但武松杀嫂与石秀杀嫂在我们看来实有不同:潘金莲、西门庆的被武松所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被杀数人还可算是罪有应得,因为案件牵涉到通奸杀人。而武松的行为也带着某种“替天行道”的性质,所以,对他带着某种赞叹乃是常情,对陈文昭等的枉法应也无太多的反感。潘巧云、裴如海、头陀、迎儿在我们看来却是罪不至死,尤其是头陀和迎儿,即使是按那个时代的律令,他们也绝不会被处死的。
冷静分析起来,石秀杀人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潘巧云反诬自己行为不端,要还自己一个清白;一是为了杨雄。下面的几段话露出了个中的信息:杨雄道:“兄弟,你休怪我。是我一时愚蠢不是了,酒后失言,反被那婆娘瞒过了,怪兄弟相闹不得。我今特来寻贤弟负荆请罪。”石秀道:“哥哥,兄弟虽是个不才小人,却是顶天立地的好汉,如何肯做这等之事!怕哥哥日后中了奸计……”
石秀笑道:“……你又不曾拿得他真奸,如何杀得人?倘或是小弟胡说时,却不错杀了人?”杨雄道:“是此怎生罢休?”石秀道:“哥哥只依小弟的言说,教你做个好男子。”
……迎儿说罢,石秀道:“哥哥得知么,这般言语,须不是小弟教他如此说……”
……石秀道:“哥哥,含糊不得,须要问嫂嫂一个明白缘由。”那妇人只得……一一都说了。石秀道:“你却怎地对哥哥倒说我来调戏你?”那妇人道:“……实是叔叔并不曾怎地。”石秀道:“今日三面都说得明白了,任从哥哥心下如何措置。”(第四十六回)潘巧云因为怕自己的不端行为败露,所以在丈夫面前反诬了石秀几句,按照现今的法律,连侵犯名誉权的罪行怕也不能成立。只是为了自己在结义兄长面前的清白,为了一己之忿,石秀便连杀裴如海、头陀两人,已可见他的狠恶。在杨雄未亲自问明妻子与和尚的奸情前,他曾对杨雄说:“当头对面,把这是非都对得明白了,哥哥那时许与一纸休书,弃了这妇人却不是上着?”到杨雄问明了奸情,自己的“身上清洁”了以后,他却再也不提休弃的话了,而是说:“任从哥哥心下如何措置。”一当杨雄说要结果妻子时,他竟还帮着剥了潘巧云身上的“头面首饰衣服”,又把丫鬟迎儿的“首饰都去了,递过刀来说道:‘哥哥,这个小贱人留他做甚么,一发斩草除根。”似乎怕杨雄面对妻子,不忍心下手,而让其先了却丫鬟。杀了丫鬟,杨雄便再也不能不杀潘巧云了。潘巧云与丫鬟迎儿与其说是死于杨雄,不如说实际上也死于石秀之手,而且石秀携带了“包裹、腰刀、杆棒”(上几处引文均出第四十六回),准备好了杀人亡命的退路,显见得前面所说休弃云云乃是言不由衷,他早就蓄意要将潘巧云杀死——这也正是前面我将此一故事概括为“石秀杀嫂”的原因。石秀的性格是狠恶中透出令人害怕的精细。我读《水浒传》,对石秀、杨雄,尤其是对石秀的这些行为只觉得憎恶。不仅我们这样认识石秀,金圣叹亦曾说过:“石秀可畏,我恶其人。”(《水浒传会评本》第四十四回夹批)
王望如亦评曰:“贼秃如海闍黎,杨雄不能杀,而石秀杀之;秀杀于忿,不杀于义也。石秀之于杨雄,不等武松之于武大,况杨雄尚在,死巧云无法,死闍黎亦无名也。巧云因醉骂之疑,生调戏之谮,石秀负怨而必欲白,故先杀胡道,次杀如海,……以为白冤则得矣,若曰义,将何以处雄也。”(《水浒传会评本》第四十四回尾评)
石秀与武松一样也不是法盲,他对杨雄说:“你又来了,你既是公门中勾当的人,如何不知法度?你又不曾拿得他真奸,如何杀得人?”(按律:“诸妻妾与人奸,夫于奸所杀其奸夫及其妻妾……并不坐。”《元史·刑法志一》,《元史》卷104,此条还可证武松为兄报仇杀潘金莲、西门庆当斩,因为他并非本夫,又非于奸所杀奸夫奸妇,而武大的被害,又并无铁证。)数语可以为证。然而他自己却也和武松一样去犯法。那么,又是什么促使作者要写石秀这个知法人去犯法,甚而还要自己充任“法官”,“枉法”地将他大加赞扬呢?我觉得,也要从文化的角度去寻找原因:
尽管我们(包括明清时代的一些人如金圣叹、王望如)认为石秀杀人是因了忿而不是为了义,作者却不一定这样看。你看,在作者的心目中、笔底下,石秀与武松虽有高下之分,却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仍然是个英雄:“有首《西江月》词单道石秀的好处:身似山中猛虎,性如火上浇油,心雄胆大有机谋,到处逢人搭救。全仗一条杆棒,只凭两个拳头。掀天声价满皇州,拼命三郎石秀。”(第四十四回)
《水浒传》第四十四回末尾还说:“那老子言无数语,话不一席,有分教:报恩壮士提三尺,破戒沙门丧九泉。”很明显,作者是把石秀当作“报恩壮士”的;他认为石秀的行为也是一种“忠义”的行为。明人余象斗体会到了作者的用心,或者说他也这样去理解石秀,故说“石秀将潘氏之事告知杨雄,乃义气丈夫。”又说:“石秀被杨雄如此不以自己,后以计杀头陀报知杨雄,越见石秀胆勇智足,仁义两全,古之罕矣。”(《水浒传会评本》第四十四回夹批)
容与堂本在“杨雄与我结交,我若不明白得此事,枉送了他性命”之下,也评说:“真忠义。”(第四十四回)
当然,作者的同情和赞扬之所以倒向石秀一边,更主要的还在石秀所杀的潘巧云、裴如海一个是****,一个是奸夫。特别是这对奸夫****之中,奸夫还是个“破戒沙门”。前面提到“万恶淫为首”,这是对西门庆、潘金莲这样的普通人而言的;和尚裴如海当尤甚,因为他的身份与普通人不同,应该戒绝所有的欲望,而他却坠入欲海,无异犯下双重的罪孽,儒理和佛教都不能容,这就是金圣叹所说的“破坏佛法,破坏世法”(《水浒传会评本》第四十四回眉评)。故和尚犯淫戒,得进十八层地狱。容与堂本《水浒传》第四十五回开头诗后接下来有一段话:“话说这一篇言语,古人留下,单说善恶报应,如影随形。既修二祖四缘,当守三归五戒。叵耐缁流之辈,专为狗彘之行,辱没前修,遗臭后世,庸深可恶!”是作者和世人痛恨犯了淫戒和尚的明证。正是这种儒家伦理和佛教戒律的双重作用,决定了作者在律令与伦理面前的价值取向,使得他要在石秀的“知法”“犯法”的冲突中,将一个明明违法的罪犯转化成了一个壮士。而且自己出面充当法官,“枉法”地对石秀进行赞扬。与塑造武松的形象相比,对石秀形象的塑造便难说十分成功了。人们对石秀行为认识的严重分歧便是证明。当然,对于石秀的赞扬,作者还是比较谨慎的,决不像对于武松那样毫无保留,所以金圣叹能够从里面看出来他的可怕可恶,我们更可将他阐释成一个颇为残忍的罪犯。
上面分析的,虽只是《水浒传》中的两个个案,但却绝不是两个特例,整部《水浒传》都贯穿着这样一种文化现象——在遇到执法与护理发生冲突、矛盾时,作者情感的天平,都是自觉不自觉地向着护理一方倾斜。比如说,为了义,“美髯公”可以“智稳插翅虎”、“宋公明”可以“私放晁盖”(第十八回)、“朱仝”可以“义释宋江”(第二十二回);为了义,武松可以帮着一个恶霸施恩,去打另一个恶霸蒋门神(第二十八回到第二十九回);因了义,宋江杀阎婆惜犯法亡命,横海郡柴进、孔家庄孔明孔亮兄弟、清风寨花荣等都不顾律令将他窝藏,并把他当作上宾款待(第二十三回、第三十二回、三十三回);因了义,朱仝将犯下死罪的雷横私自放走(第五十回)……作家也正是借用法与义的冲突,去完成一个又一个重义气的“好汉”的形象。
可注意的是,执行法制与维护伦理构成矛盾冲突时,作者的情感天平向伦理一方倾斜,绝不仅仅存在于《水浒传》一书之中,而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一个颇为普遍的文化现象。这里取这类小说中几个影响较大,较能说明本文上面论点的故事作点阐释:
(一) 唐李公佐《谢小娥传》。小说叙谢小娥一家俱为盗所杀,小娥逃得性命。李公佐为其解梦,说仇人是申兰、申春。小娥于是男装于江湖间寻觅,终于找到了申兰,佣工于其家,伺机先杀了申兰,余党亦一一就擒。小说说:“时浔阳太守张公,善娥节行,为具其事上旌表,乃得免死。”作者评曰:“誓志不舍,复父夫之仇,节也;佣保杂处,不知女人,贞也。女子之行,惟贞与节能始终全之而已。如小娥,足以警天下逆道乱常之心,足以观天下贞夫孝妇之节。”看得出,执法者及作者李公佐正是因为小娥的节孝,不仅赦免了她不通过官府而手刃仇人的罪行,而且给予高度评价的。《谢小娥传》中谢小娥杀人报仇与《水浒传》里的武松杀人报仇虽有不同,但本质却是一致的:复仇者都越过官府私自将仇家杀死;本该受到法律的惩处,却因了复仇者的道德魅力而免受法律的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