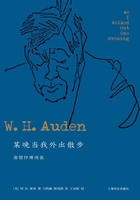(一)豪侠·绿林豪侠集团·侠文化
——《水浒传》的根本性质
《水浒传》由于其题材的政治敏感性,成书历史和成书过程的漫长、复杂性,内容和信息含量的丰富、博大性,艺术手法和艺术形式的精湛、多样性,自其大量流行以来,就成了人们热烈评论、反复研究的对象。许多问题是人言人殊,聚讼纷纭,直到今天仍然争论不已,悬案很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水浒传》研究中关于其思想内容的主要观点是,《水浒传》反映了“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的斗争”。但那是当时的主流意识和主流媒体反复宣传影响的结果,是在一种特殊的环境中形成的,当今的读者是否会对这一观点产生共鸣,就不一定了。而我们研究者自己,怕也到了自我反省的时候了。
说《水浒传》写的是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的斗争实在是缺乏根据。这一论点的逻辑依据主要是:封建社会里的阶级矛盾,主要是农民和地主的矛盾;《水浒传》写宋江造反的故事,反映的是封建社会里的矛盾和斗争,所以它反映的当然是农民对地主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固然认为,封建社会里的阶级矛盾,主要是农民和地主的矛盾。但主要矛盾并不就是唯一矛盾,《水浒传》反映的是封建社会里的矛盾和斗争,也不一定就非反映这主要矛盾。根据“封建社会里的阶级矛盾,主要是农民和地主的矛盾”,“《水浒传》反映的是封建社会里的矛盾和斗争”,而且借了个宋江起义的外壳,就断定其性质属农民反抗地主阶级封建统治的斗争,首先从逻辑上就说不通。
而且,从历史的角度看,宋江能不能算是农民起义领袖还很难确定。《宋史》说他的这支队伍一共只有三十六人,辗转于河北、山东、淮南一带。史书没有说他有什么纲领,也未说他有志于图王。这支队伍若不是支流寇,就只是一群绿林豪侠。史书也只称宋江们为“盗”,而不称其为“贼”——在封建社会中,“盗”是一般的强人,“贼”则是叛逆,是妄图窃国的人。“盗”这样的队伍,民国期间也有很多,七十岁以上的人都清楚,这样的队伍并不都是“革命军”。而在历史上,这样的队伍更不知有多少。所谓官军“莫敢撄其锋”不过是夸张之词。宋江的名声这么大,完全是水浒戏曲和小说《水浒传》造出来的。
即使历史上的宋江队伍是一支农民起义军,由原型到典型,人物形象、队伍的性质也会发生根本变化。从《水浒传》的文本分析,最后汇集到水泊梁山的这一批水浒英雄,怎么说也不能算是一支农民起义军。因为凡称得上文学形象的水浒英雄,几乎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农民。李逵是农民出身,“祖贯是沂州沂水县百丈村人氏。……因为打死了人,逃走出来,虽遇赦宥,流落在此江州,不曾还乡”,作了个狱卒。阮氏三兄弟是渔民,应该说贫苦的渔民和农民是同一个阶层的人,但“三阮”虽“日常只打鱼为生”,却“亦曾在泊子里做私商勾当”。有人说,梁山英雄的头领虽然几乎没有农民,水泊中的大众,却应该是农民组成。但文学作品的思想是靠形象来传达的,形象以外的“人物”表现不出思想。特别是,梁山的这支队伍自建立以来,便没有作过多少对农民有益的事情,梁山发动的战争也不是为了农民。可以说全书中没有一点农情农趣。
那么《水浒传》到底主要写了什么呢?我以为《水浒传》写的大多是豪侠,在水泊梁山聚义的乃是一个绿林豪侠集团,《水浒传》体现出来的则是一种浓浓的侠文化。
翻一下孙楷第先生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我们会发现,《水浒传》是放在“侠义公案类”的,这说明,孙先生也认为,水浒英雄主要是侠义英雄。鲁迅先生虽没明确讲过水浒英雄是侠,但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七篇《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中,却指出:“《三侠五义》为市井细民写心,乃似较有《水浒》余韵,然亦仅其外貌而非精神。”则又明显认为《水浒传》与《三侠五义》有某些相类的地方。孙先生的将《水浒传》放在“侠义公案类”中是否也受有鲁迅的影响?倒不是我想拿大旗作虎皮,我这样解读鲁迅、孙楷第的论点相信不会是曲解。
说水浒英雄主要是一批豪侠得先从“侠”的内涵讲起。
司马迁说过:一个侠一定是“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史记·游侠传》)
也就是说,侠的特点主要是讲究信义,舍生忘死,扶助弱小,而不图报。
按照司马迁对侠的定义,看一看《水浒传》里的鲁智深,他不就是个典型的“侠”吗?他帮助金老父女脱离困厄、拳打镇关西,自己被逼得四处逃亡、做了和尚;他助林冲对抗高俅、高衙内,在野猪林内用禅杖架住了将要落到林冲头上的水火棍,又被逼得逃离东京相国寺;为了救出陷落在大牢中的史进,只身前往华州,以至自己也身陷囹圄。鲁智深这一系列的行为,岂不正是侠“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的注脚?再看一看武松,不也是个典型的“侠”?为了替哥哥报仇、为了替施恩夺回快活林,沦为囚徒、几至于死,也在所不顾,他的行为不也正是侠“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的注脚?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所有侠的本色,也是水浒英雄的本色。华州太守强抢王义的女儿玉娇枝为妾,又把王义刺配远恶军州,途经少华山,正撞见史进,告知这事。史进将王义救在山上,将两个防送公人杀了,又直去府里要刺贺太守。石秀见杨雄被张保及病关索一批帮闲逼住,“动弹不得”,“便放下柴担,分开众人……将张保劈头只一提,一跤颠翻在地。……一拳一个,都打的东倒西歪”。戴宗、杨林看了,暗暗地喝采道:“端的是好汉,此乃‘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真壮士也!”史进、石秀的行为,不正是一个侠客的行为?他们岂不就是豪侠?电视连续剧《水浒》的主题歌“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算是抓住了这批豪侠的本质特征。
《水浒传》里的英雄特别重义,这义是侠的“信义”之义、“侠义”之义,是一种江湖义气,而不是儒家的“义”者“仪”也之“义”。“义”在《水浒》中是英雄们追求的一种完美品格,也是对人品的极高评价和期许。
侠客们首先须尊重友朋间的情义。为了朋友,他们可以两肋插刀。水浒中的英雄也是如此。史进捉了陈达,朱武、杨春自知武功不敌史进,只好自投史家庄,以实现三人“不求同日生,只愿同日死”的誓愿。虽说这是朱武的苦肉计,但要冒极大的风险,却是肯定无疑。而史进也因他们“如此义气深重”,放过了他们,并和他们结为兄弟。有诗赞道:“姓名各异死生同,慷慨偏多计较空。只为衣冠无义侠,遂令草泽见奇雄。”晁盖犯案,朱仝、雷横都有心将他放了,故而捉拿时或有意大呼小叫、虚张声势,或有意放开道路,指示逃亡去处;捉拿宋江时,两人更是有意卖放,朱仝还进入宋江藏身的地窖,告诉他赶快逃往柴进庄上;雷横枷打白秀英,犯下死罪,押解路上,朱仝“开了枷,放了雷横”,道:“贤弟自回,快去家里取了老母,星夜去别处逃难,这里我自替你吃官司。”“我须不该死罪。况兼我又无父母挂念,家私尽可赔偿。你顾前程万里自去。”李逵为了宋江,更是性命不顾,只身劫牢;石秀虽因为杨雄误信了妇人之言,蒙受了不白之冤,想着的还是:“‘杨雄与我结义,我若不明白得此事,枉送了他的性命。’”自己冒着生命危险,到底用计除了与潘巧云通奸的和尚海阇黎。为了朋友,水浒英雄可以说是荣辱死生,都在所不计。
我们常常发问:宋江“面黑身矮”,武功很差,又无甚计谋,他怎么就能统领一伙天不怕地不怕的梁山英雄?为什么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一听到宋江的名字就会五体投地?宋江的魅力在哪里?分析起来,其实就在他的“于家大孝,为人仗义疏财”,“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赒全人性命。如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赒人之急,扶人之困”,也就是说,他的魅力,就在他的“行侠仗义”。是他冒死给劫了生辰纲的晁盖送信;是他周济素不相识的阎婆母女十两银子,让她给死去的丈夫买了副棺材;武松落难,流落在柴进庄上,正是贫病交加,宋江不但不嫌弃,问寒嘘暖,临别依依,又送给十两银子;刚与李逵见面,李逵正为银钱短缺而与人争吵,宋江马上送上十两银子为他解困等等,都是宋江“赒人之急,扶人之困”侠行的表现。小旋风柴进也有侠风,“专一招接天下往来的好汉,三五十个养在家中”。他曾帮助过流放的林冲,避难的武松、宋江,而且“他是大周柴世宗子孙。自陈桥让位,太祖武德皇帝敕赐与他誓书铁券在家中”,为什么他不能像宋江那样统领群雄?武松的几句话说出了个中的原由。武松曾对柴进说:“却才说不了,他便是真大丈夫,有头有尾,有始有终,我如今只等病好时,便去投奔他。”说宋江“是真大丈夫,有头有尾,有始有终”,话含讽意,实际上是在说柴进不如宋江,对自己有始无终。
“仗义疏财”、“打抱不平”不仅是《水浒传》英雄的本色,也是古今侠义小说中侠客必须遵守的游戏规则,否则,他就不能算是侠。古龙的新武侠小说《楚留香传奇》写楚留香在京城盗得白玉美人后,躺在一艘豪华海船的甲板上,左右温香软玉,悠闲自得,接下去,作者也不忘写李红袖“吟道:‘上次你从济南取来的一批货,已卖了三十万两,除了救济龙虎镖局王镖头的遗孀一万两,趟子手张、赵两人家眷各五千两,还替黄秀才付了一千两丧葬费……’”金庸的武侠小说《笑傲江湖》写令狐冲不论“正道”“魔教”,遇见不平,就拔刀相助。他从田伯平的手中救下了衡山派的小尼仪琳,在衡山派掌门临终时受命接掌衡山,成了纯女性教派中的唯一男性。他身为华山派的弟子,却与“魔教”中人结交,还帮任我行重夺了明教教主的大位。他的原则只有一个:主持正义。
“义”这个词,大约是所有侠义小说使用频率最高的词之一。“义”也是《水浒》中评论英雄时用得最多的一个词。看一看《水浒传》的标题,便有“晁天王议义东溪村”、“公孙胜应七星聚义”、“梁山泊义士尊晁盖”、“朱仝义释宋公明”、“施恩义夺快活林”、“锦毛虎义释宋公明”、“白龙庙英雄小聚义”、“三山聚义打青州”、“宋公明义释双抢将”、“混江龙太湖小结义”等等。林冲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义举,作者也赞他“仗义是林冲,为人最朴忠”。小说称晁盖“平生仗义疏财,专爱结识天下好汉”;说三阮兄弟“与人结交真有义气,是个好男子”;说卢俊义“慷慨疏财仗义”,李应“疏财仗义结英豪”,戴宗“十分仗义疏财”;称关胜是“蒲东郡内产豪英,义勇大刀关胜”。解珍、解宝被诬入狱,乐和为他通风报信,对他的姐姐说:“小人路见不平,独力难救。只想一者沾亲,二乃义气为重,特地与他通个消息。”就连那个菜园子张青和他的妻子孙二娘也都有点侠气,是两个有道的强盗。他们开黑店不也有原则:“‘三等人不可坏他。第一,是云游僧道,他又不曾受用过分了,又是出家的人。”“第二等是江湖上行院妓女之人,他们是冲州撞府,逢场作戏,陪了多少小心得来的钱物,若还结果了他,那厮们你我相传,去戏台上说得我等江湖上好汉不英雄。”“第三等是各处犯罪流配的人,中间多有好汉在里头,切不可坏他。”鲁智深在诉说他“来到孟州十字坡过,险些儿被……害了性命”时,还说“那人夫妻两个,亦是江湖上好汉有名的,都叫他做菜园子张青,其妻母夜叉孙二娘,甚是好义气”。
“义”既是梁山好汉的理想目标,“义”也是维系他们团结的一根纽带,所以豪侠总称他们的结合为“聚义”。不义的行为蔓延滋长,不仅弱者遭殃,他们自己也将无力与强权对抗,于是铲除不义便是他们的义务和责任。
梁山英雄口中常讲的一句话是“四海之内皆兄弟”。“四海之内皆兄弟”一语本出自《论语》,从孔子的弟子子夏的口中说出,是地道的儒家思想。到了侠客们那里,重心也有点偏移,他们强调的是其中的哥们“义气”。
《水浒传》第四十三回,写杨雄因为没有防备,被张保等一班无赖困住了手脚,抢走了花红包袱。石秀“路见不平”,抡起扁担,打散了一批无赖。戴宗、杨林见了,“暗暗地喝彩道:‘端的是好汉!真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于是要请石秀喝酒,并要结为兄弟。石秀说是不敢当。杨林就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怎如此说?”张保一班无赖强抢杨雄财物的行为是不义,在石秀、戴宗、杨林眼中这就是不平之事,石秀帮杨雄打散众无赖是“打抱不平”,是在行“道”,尽管此时杨雄、石秀、戴宗、杨林并不相识,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信条将他们联在了一起,一个“义”字将他们联在了一起。这是说明“替天行道”和“四海之内皆兄弟”两个口号内涵的一个例子。而这样的例子在《水浒传》中很不少。石秀等的行为思想,岂不也很有点侠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