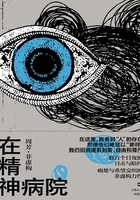这时我正在绘图室一位青年工人的帮助下(所谓帮助,就是用他的名义把书借来)通读二十四史(场部有一个职工图书室,不仅有新书,也有一些不知从哪里弄来的旧书)。读史增强了我对历史的责任感和信心。我深信,把无罪者当作罪人的悲剧总有一天要结束。但是,自己已经四十多岁了,身体早已被折磨得虚弱不堪,颈椎病、腰劳损、气管炎……我还能不能活到那一天呢?
“你还年轻。”当晚躺在监房的黑暗中,这句轻轻的、平淡无奇的话仍然萦绕在我的耳际和心头。在我听来,它蕴藏着关怀和鼓励。“你还年轻。”这就是说,你还应该有坚持下去的力量,你还可以看到该倒的倒下去,该站的站起来。
不错,我还年轻,我不怕,我得坚持下去。
一九七六年,黑夜终于开始破晓。劳改队高高的围墙,也遮不住破晓的曙色。这年十一月间,我又交出了重新写过的一份申诉书,申诉书的最后一句是:
我要求的并不是怜悯,我要求的不过是(而且仅仅是)公正。
渐渐绘图室里的紧张气氛也有所缓和,谈话的内容多起来了。就业人员先是摘了帽子,接着又转成了工人。工人师傅和几位干部,对我的态度也不同了一些。关于潘汉年和董慧的情况,我又陆续地听到了许多。
潘汉年是一九七五年七月从北京送来洣江茶场的,董慧比他早两月到来,他们原来并没有关在一块。听说,老夫妻在见面的时候,都流了泪。
他们夫妇俩带来的东西很多。董慧的身份据说“不是犯人”,带来了电视机。潘汉年则带有很多书,还有一副钓鱼竿,大概他在原来被“优待”的地方是可以钓鱼的。至于是一些什么书,我确实想打听打听,可是看到的人弄不清楚,只说“有好多鲁迅的书”。(顺便说一句,干部和工人也是被告诫了的,不允许和潘氏夫妇接触。)
他们夫妇俩同住在由浴室改成的小平房里,被允许在茶场范围内“自由活动”。初来的头一年,潘汉年总是每天五点多钟就起床打太极拳,接着就打扫屋子周围的卫生。到木工间买柴火,到邮电所取报纸,都是这一年里的事情。可是,贾谊所谓“居此寿不得长”的这块卑湿之地,对老人的健康太不适宜了。尽管他恬静、安详,尽管他天天打太极拳,尽管他已经等到了“******”的完蛋,到一九七六年冬天,潘汉年就开始生病,出来行动的时候也少了。
大约是一九七六年底一九七七年初的一个大晴天,我被叫到场部去“搞宣传”,有意从潘汉年夫妇的住房前经过,看见潘汉年穿着棉衣,戴着冬帽,坐在屋外晒太阳。他的面孔向着一大片菜园,替场部干部种菜的犯人正在菜园里劳动,我只看到他的背部。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一九七七年二月,听说潘汉年病重,在场部医院治疗。场部医院的医疗水平,大概等于长沙市的街道卫生院吧。三月间,又听说上头叫把潘汉年送到长沙去抢救。不知道是出于什么考虑,反正人是用汽车送走了。送走的消息我是事后才知道的,接着就听到了他的死讯。据说,他的病是肝癌,送到湖南医学院附属医院去时,用的名字是化名。
老实说,潘汉年的死并没有使我特别悲哀,我的情感早已钝化和麻木了。那么些年,死人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我曾亲眼看见一个犯人用菜刀把自己颈项拉开一个大口子,还用手从口子里往外拉气管(或者是食管)。我还曾亲眼看到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婆,因为“为刘少奇翻案”而被判处死刑,当场枪毙示众。用一根裤带或绳索悬梁自尽的尸首,少说也目睹过三五回。像这样“寿终正寝”,而且被送到“大医院”去抢救,要算是绝无仅有的了。我只有一种烦躁的感觉,为什么“******”已经倒台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还做得这么迟缓。我当然无法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得到承认还得经过那么复杂、那么曲折的斗争,真是“************”啊!
潘汉年死后,董慧也因高血压住进了场部医院。关于她,听到的新闻也有一些,大都是当作笑话讲的。比如说,买了个鸡不会杀,不会脱毛,不会开膛剖肚。她没有小孩,就买了个毛长长的哈巴狗玩具,连住医院也要带着放在床头。茶场为了“照顾”她,轮流派一些干部家属去帮她料理生活,由她从每月一百元生活费里拿出几十元作为这些家属的报酬,她却连自己的手表被一位家属换走了也不知道……
我是在原判刑期还差一年的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六日离开第三劳动改造管教队即洣江茶场的,董慧在我离开之前二十来天死于茶场医院,病名是高血压。
我一次也没有在近处见到过董慧,没有和她讲过一句话。
(一九九二年十月《书前书后》初版)
钟叔河诉说潘汉年最后的日子
阿丙 晓梅
我国著名出版家钟叔河曾“有幸”与潘汉年一起关在湖南茶陵洣江茶场(劳改农场)。中央电视台播放二十八集电视连续剧《潘汉年》,却不料他并未一集接一集地追看。“我看了前面一两集,出来的人物有******、汪精卫,我觉得人物被漫画化了。将政治、历史人物浅层次地图解,这就不可信了。”钟先生说他的“文学时代”早已过去,所以他一般不看文学作品,只看历史资料。他把电视剧《潘汉年》归入到他不喜欢看的“文学作品类”。他更愿意选择原始、客观的历史事实,凭自己的头脑去得出结论。
钟先生曾在《潘汉年在洣江》一文中,抱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严谨态度,写了潘汉年跟他讲过的仅有的两句话:一是“相信人民”,二是“你还年轻”。文章用的是平实沉郁的笔调,但灰色的“****”加“劳改”岁月和对潘汉年的敬仰之情却在行文间凸现。钟先生回忆起他所了解的潘汉年在洣江茶场度过的最后岁月——
一九七五年七月,潘汉年和他的爱人董慧被从北京某关押处送来茶场。他们带来了一卡车书、钓鱼竿和电视机;他们一个月有两百元生活费,可以买鱼和蛋吃,抽的是好的香烟。一九七六年冬季以前,潘汉年的身体还比较好,经常到木工车间捡木块来生火。但湖南这块“寿不得长”的“卑湿”之地,对老人的健康非常不利。尽管等到了“******”完蛋,但一九七六年冬天潘汉年终于病倒,翌年二月病情加重,三月间被送往长沙湖南医学院附属医院,用的是化名,诊断是肝癌,不久就死了……“我当时四十五岁,与潘汉年年龄不同、层次不同,虽然心中敬仰他,想与他攀谈,但他长期从事革命秘密活动,有地下工作经验,是不可能跟陌生人乱讲话的。他对我说‘相信人民’,这句话在什么时候都能讲。但是,我能感受当时的气氛,他心情不好,******不相信他。******死后八年——一九八四年,潘汉年才获平反。”
钟先生还提到其文章以外的唯一一个情节,是关于潘汉年的爱人董慧的。董慧的父亲是新加坡富商。董慧在国内读书时与潘汉年相识相爱。潘汉年死后,因为没有子女,董慧更加凄凉。有一次,她哥哥从新加坡回国来看望她。“上级”安排董慧在长沙的湖南宾馆与哥哥见面,并派了几个人假装服务员进行监视。蒙在鼓里的哥哥压根儿不知道妹妹正在受难!潘汉年死后仅两年,董慧就因脑溢血而病故于洣江茶场。
听钟先生诉说过去那个年代发生的真实事件,再看看电视中所见的风流儒雅、气度不凡的“潘汉年”(潘自一九五五年被捕后的镜头一个没有!),两者相距是何等遥远!读钟先生文中所记见潘汉年最后一面之情境,痛惜长久阻塞于心——
“于是我便有意从潘汉年居住的平房前经过,看见他穿着棉衣,戴着冬帽,坐在屋外晒太阳,他的面孔向着一片菜园。替场部干部种菜的犯人正在菜园里劳动。我只看到他的背部。
“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
(一九九八年二月一日《湖南日报》)
《钟叔河诉说潘汉年最后的日子》读后
维中(黄道奇)
看了《湖南日报》二月一日第三版所载的这篇“诉说”的文章,很是诧异。它介绍钟叔河先生在“****”中曾“有幸”与潘汉年同志一起关在茶陵洣江茶场,不久前还写过一篇回忆文章,文章我没看过,但这篇“诉说”转述钟叔河的话就确实没有怀念的意思了。简直是说潘汉年不过如此,没有值得怀念的了。
“诉说”转述钟先生对潘汉年同志的“敬仰”很特别,他只“选择原始、客观的历史事实,凭自己的头脑去得出结论”,他对电视剧《潘汉年》看了一二集,就断定这不过是件文学作品,大学者那当然是不屑于看的,说:因为“出来的人物有******、汪精卫”,觉得“人物被漫画化了,将政治、历史人物浅层次图解,这就不可信了”。这意思不难明白,把******、汪精卫这些大人物扯到潘汉年这个浅层次人物一起,太不应该,潘汉年哪有资格高攀?不配、不配。
原始、客观的历史究竟怎样?潘汉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与国民党的代表陈立夫等的谈判是事实吧,潘的背后是******、******,陈的背后是******,潘与陈的对话,实质上就是毛与蒋的对话,这个“图解”辱没了******吗?!至于潘汉年与汪精卫的一次直接接触,人们现在谈论起来,心里还很难过。据史料披露,这次不愉快的接触,不是潘汉年高攀汪精卫,而是汪精卫为了一个可耻的政治目的,妄想利用共产党而设置的圈套。然而潘并未就范,相反,以他的机智勇敢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可惜的正是由于在敌人的心脏里的这场搏斗,竟不幸被造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第一个大冤案。人们还在深思这血的教训的时候,而钟先生却在旁讥笑被“漫画化”了,变成了“浅层次的图解”。而电视剧关于堂堂正正的共产党的谈判代表的历史叙述中,本来就扯在一起的******、汪精卫出现一下都不允许,未免把共产党的谈判代表太轻看了吧。如果钟叔河不知道这些原始、客观的历史事实,那又写什么回忆文章?还装作“名士”派头,搞什么“诉说”,岂不是沽名钓誉吗?我想,简直是的。
钟叔河在洣江茶场所了解的潘汉年,据他说只是看到潘夫妇“从北京某关押处送来茶场,带了一卡车书,钓鱼竿和电视机,一个月有两百元生活费,可买鱼和蛋吃,抽的是好烟”,“穿着棉衣,戴着冬帽,坐在屋外晒太阳”,看别人劳动等等。这对一个犯人唠叨这些是什么用意?是羡慕,还是妒忌?为什么不叙述一下,潘的活动范围仅限于住所附近的“米筛坪”,电视机运来时已碰坏,钓鱼竿从未用过,钟叔河觉得加上这些就不原始不客观了么?这种说法会把人们的认识引入误区的。难怪“诉说”的作者听了钟叔河的话,“再看电视剧中的潘汉年风流儒雅、气度不凡的形象,两者相距何等遥远”!那么电视太不真实了。大概作者年轻,不懂得特殊任务必须采用特殊的手段才可完成这一简单明白的道理。至于电视剧为什么不表现蒙冤后的形象,这大概是剧作者别有一番深意吧,不必深究。
我很久就想过文艺界应多拍几部以潘汉年同志的英勇机智的事迹为题材的影片,用以教育后人。今日看到成果,虽然仍然悲哀,但仍是高兴的,潘汉年同志是一位为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生入死二十多年,建立了种种奇勋伟绩的伟大革命家,却又蒙受了奇冤的历史人物。人们刚喘口气开始怀念,流言蜚语就出现了,我们有责任再还其本来面貌。我们有责任。
(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日《湘声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