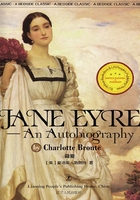非现场经济是创新的产物,非现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创新的土壤,改善和建立创新机制成为重中之重。
笔者认为:非现场经济创新的土壤主要是营养供给,这是市场机制和激励机制所应解决的利益获取和再分配,我们可以用智慧共享体系和“按行动力分配”制度的建立来逐步完善性地去解决这个问题。然而,我们的创新之树还需要空气的养分,需要适宜生长的温度和湿度的空气环境。这犹如一棵巨大茂盛的榕树,不仅靠土壤的养分,更需要“气根效应”一起来支撑起这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
这个适宜的温度和湿度的空气环境就是我们抚育创新的社会环境氛围,我们的智慧劳动一天都离不开这个创新氛围,离开一天就将因窒息而亡。
因此,这一切就是要求我们的创新机制首先需要的有一个能“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社会氛围”,一个能生长创新之树的最基本的空气环境,整个社会氛围必须是与创新土壤相匹配的要求。
中国智慧经济和公平社会实现的保障将首先取决于中国创新氛围的优劣,优质的创新氛围才是中国智慧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招商局董事长秦晓于2010年5月9日在剑桥大学中国同学会论坛上的演讲提到:“对‘经济增长模式’的判定,即优与劣、好与坏不是经济增长的速度,而是经济增长的效率和质量、财富分配的公平与公正、对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选择权利的保护。只有具备了这些特征,这种模式(制度)才能充满活力、才可持续、才具有竞争性、才真正反映了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
笔者个人认为:“中国模式”能否成为“反映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首先要看它是否具有时代特征,是否始终与时代同步。
在智慧经济已经到来的今天,“中国制造”模式(制度)是否还将是“充满活力、可持续、具有竞争性、真正反映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
这种由初级制造业支撑起的改革开放前30年带来的“中国模式”是否就能代表********的“中国创造”模式?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在由移动互联和智能移动终端支撑下的非现场经济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内容,再也不是简单初级的“中国制造”所能全部包含的。
而是直接涉及社会财富再创造与再分配规则改变的经济模式。
总结和探讨中国经验、中国模式是必要的,学术的百家争鸣同样也是必要的。
但在探讨“中国模式”时,我们必须注意实际可能造成的社会氛围效果,必须清楚地认识到:
(1)学术层面探讨不等于成熟理论的大众传播,特别是在公众传播平台上我们需要慎重。
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学术层面探讨的百花齐放是各种思维的碰撞,属于只对学说负责的探讨层面;而大众传播层面不仅是对学说负责,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向社会负责的义务。
(2)我们为什么要探讨“中国模式”。是为了夜郎自大?还是真正为了探询中国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如果我们的社会各界不充分认识、并时刻审慎地注意到以上这两点,那么就是对中国创新氛围培育的破坏。
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提示着我们:这种中国模式的探讨行为,首先将会涉及国人的某些文化意识和经济观念的调整。
这一点,笔者个人非常赞赏成忠英、阎雨两位教授所倡导的:用“东方的软智慧与西方的硬技术”的结合起步,来探询现今的中国经济和中国管理新模式,及其未来的发展方向。
这里,我们必须提出:现今的中国模式谈论出现了一些探讨令人担忧的倾向,有些人在我国整体经济取得了一些初步成绩就沾沾自喜,甚至还出现了个别的纯粹的民族主义和夜郎自大,误导国人。
一些专家学者在各种公开场合上探讨中国模式话题时,不时地表现出了浓重的“民族主义倾向”和“排斥西方文明和西方硬技术”的情绪,甚至个别还出现了借小题而嘲讽打压向外学习或“海归”的不良现象。
中国经济还刚起步,虽然GDP总量已经超日本,但人均GDP还十分低,很多核心科技、创新应用、管理体制等还远远落后于一些发达国家,特别是我们的信息经济的基础领域的核心技术和产品几乎是被人掌控着。
如果我们再不注重这些,不注意紧盯世界先进并自主创新的话,那么我们在智慧经济阶段里能跟得上别人的脚步就不错了。
笔者不仅要问:难道我们这些“儒生”们忘记我们的先知孔圣人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教诲了吗?!
哪怕是在非洲的某个部落中,也总有一点点是值得我们中国人学习的。
更何况时代是进步的,全世界都在变化运动之中,我们必须保持时刻清醒的头脑,谦逊并与时俱进,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所在。
古训:君子慎言。在此,笔者呼吁名人、专家学者们“慎言”,特别是在公开课堂或公众媒体上“慎言”。
一年内发生的方舟子与唐骏、方舟子与肖传国的事件给了我们怎样的启示?原本是关于诚信监督和一个真伪学术的学术界的争论的好事,可是实际的演变结果呢?
一个演变成了虚伪的正统论,试问:唐骏以自己的学习方式和实践成绩难道还够不到一个普通博士的水准?我们反对的是虚假文凭,而不是反对自觉的继续教育学习者。难道我们的现代中国人还是在膜拜鲁迅笔下“不肯脱长衫的孔乙己”?
我们是鼓励创新的学习型人才?还是鼓励“穿着长袍的废物”?
另一个更糟糕,一个学术与伪学术的争论演变成了凶杀案。
这两个个案,充分暴露了我国知识界、学术界普遍存在着封建残余意识,严重破坏了我国创新力培养氛围的营造。
2010年11月24日《重庆晚报》:“在全球21个受调查国家中,中国孩子的计算能力排名第一,想象力排名倒数第一,创造力排名倒数第五。”
这是2009年教育进展国际评估组织对全球21个国家进行的调查结果。
此外,在中国的中小学生中,认为自己有好奇心和想象力的只占4.7%,而希望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只占14.9%。
著名教育家、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此前曾表示,中国孩子的想象力状况令科学界忧虑,他拿世界上两个最重视家庭教育的国家——中国和以色列做比较。以色列家长教育奉行狮子育儿法:母狮让小狮子离开独自学会生存。中国的家庭教育则走向两个极端:要么娇宠,要么棒喝。结果是,以色列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有近10位,而中国却一个人也没有。
这个痛苦的事实固然是我国教育界和教育制度的耻辱,可是游历世界的感受让笔者深深体会到:这绝不是单单一个教育改革就能完成的了的,而是包含教育界在内的整体社会氛围决定了的,这是一个需要我们全体社会共同承担的责任。
我们的大众名人、媒体,不论出于何种目的,也不论谁对谁错,别忘了在公众面前实际可能产生的社会责任,我们共同在给我们的普通国人和我们的下一代传输的是什么信息?
名人、权威人士不经意的信息传导将会对社会产生什么的实际精神结果?
千万不要所谓的“好心”却造成了“破坏社会创新力氛围培育”的实际恶果!
事实上我们实际营造了是怎样的一个“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社会氛围”呢?!这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特别是名人、公众媒体和我们的权威人士值得深思的问题。
这里我不得不提到一个让我钦佩的人物——陈光标。我钦佩他的不单是他捐出的真金白银,而是他勇于脱掉破旧的长衫,反传统的高调行善思维。
其看似莽撞的行为将在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甚至两岸三地的后代中产生极及地持续影响,其反思维惯性的深远意义不尽在一时片刻的言语之中。
因此,中国的希望在于智慧劳动,智慧劳动的希望则在于社会的创新氛围营造,而创新氛围的营造则在于我们敢不敢脱掉那件鲁迅笔下的破长衫!
只要我们团结一致,抛开封建残余思维的束缚,以老一辈开创的“两弹一星”精神为支柱。共同致力于中国的“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社会氛围”营造。
那么,在中国已经取得的经济成就基础和创新机制深化的共同作用下,我们坚信:勤劳智慧的中国人通过创新氛围的培养和智慧劳动的推动,终将用自己的双手托起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智能移动终端支撑下的非现场经济”,进而构建起真正和谐幸福的社会典范形象。
不论是为了振兴我国的ICT产业,还是为企业单位的创利;不论是为了引入教育事业的新内容,还是创新人才的自我培育;不论是为了平民的共同致富,还是成就个人事业的成功。就让我们一起参与到“非现场经济”实践和探索的行动之中吧。
第三节 致谢
由于笔者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ITC的专业人才,笔者的经济学素养存在缺陷和不足,同时也缺乏信息技术研究的深度,加之系业余时间的观察和匆忙写作。因此,本书存在着许多不当之处,特别是关于“非现场经济”的内容分析工具的设计仅仅是个开头,缺乏时间性和各种状况的比对分析,笔者在后续的研究活动中加以改正,也将继续完成海量比对和调整工具和公式,以便持续地完善此工具,为经济学分析增添一个可选择的辅助分析工具。
笔者希望得到是:首先提出非现场经济学概念和揭示智慧劳动与资本共同主导经济的发展趋势;其次是本书出版后能得到更多的社会力量扶持,能继续深入研究智能移动终端支撑的非现场经济现象,意图得出:非现场经济指数每提升1个百分点能带来多少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占比;非现场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每提升一个百分点能给社会贡献什么(GDP提升的贡献和其他经济指标的提升贡献);如何完善非现场经济学科和非现场安全经济学等等。
在此,笔者由衷地感谢所有在我编写本书时曾给的帮助、支持鼓励和启发的人,非常感激我的家人和同学们对我的体贴、支持和理解,特别感谢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发展个改革研究院的邹东涛院长、曹元副院长、北大的阎雨、成中英老师,中国工程院潘云鹤常务副院长,浙江大学褚建副校长,浙江大学圆正控股公司胡征宇总裁、杨其和书记,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的汪炜副院长、浙江大学出版社傅强社长。国信证券的廖亚滨总工程师,中国电信浙江公司的张新建总裁、寿永飞经理、张信阳经理、江军经理以及中国电信的其他领导和各位专家。
本书只是笔者先行抛出“非现场经济学”这个新学科研究的概念性话题,仅仅是为后续的正式研究起个头。
该书出版后,欢迎广大读者提出批评和建议,并关注后续《非现场经济系列丛书》的出版,更希望能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各专家学者,参与后续专著的编写,特别是《非现场经济导论》一书,更是期盼专家的联合完成,希望我们一起再来完善和补充这个新的学科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