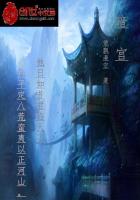那风那雨那世界
那是在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盛开的季节,空气中回荡着阵阵清香,滋润着人的心田,仿佛杂草丛生的井底的一滴清水,流淌着纯净……
——此文献给那些风雨同舟情深不渝的人们
于帆静静的捧着手中的小船,那心中最爱的一叶小舟,就这样的远离了自己的世界吗,还有那风雨同舟的话语,也随那风那雨消逝了吗?
于帆是属于那种比较浪漫的人,她个子不高,但长得漂亮,有一种大家闺秀的气质,还有最好看的就是那水汪汪的大眼睛。
在读高中的时候很多男孩追求她,但她那时只顾学习并没有把那些男孩放在心上。那时她家住在县城里,没有在学校住宿,来回上学她都是骑着自行车,虽然她骑自行车的技术水平一般。
一次放学后她仍然骑自行车回家,刚出校门口不远就被一个愣小子给撞了,那小子也骑着自行车。幸亏她被撞得不严重,只是腿擦破了点皮,稍稍有点血。可她还是气愤极了,圆目立瞪着那男孩,男孩慌张之余才想起说声对不起。男孩要带她到附近诊所涂点药,她看自己并无大碍就说不用了。
之后他们就都走了,过两天在于帆放学的时候,又碰到了那个男生,他问她的伤怎样了,这两天他一直在找她,但不知她在哪班,也不知她叫什么名字。于帆看他诚挚的样子,心中的怒气也消了,便说没事了。那个男生说他叫文强,在高三(二)班。于帆感觉他的名字可笑,还许文强呢。他似乎看出她的想法,没有说什么。于帆告诉了她的名字,但没有告诉她的班级。
因为于帆觉得这个男孩是出于自责的心态,所以也没有过多的想什么。那以后的时间里,于帆在放学的路上经常会看见文强,时间久了,她知道是那个男孩在等他,因为他们不是一班,不是一起出校门,要想相遇只是偶尔,这么经常的相遇就是他刻意在等她的。
每次相遇都没有说话,只是那个男生远远地向她微笑着点头,于帆对他不讨厌但也没有过多的好感。就这样很快到了高三下学期了,学习的紧张和忙碌也冲淡了一切,可那男生始终都会看着她骑着自行车远去的背影。有一天男生终于给女生一封信:“美丽的于帆,你已经走入了我的心里,快毕业了,我不想把遗憾留给自己,我要向你诉说……”
于帆看后觉得并没什么,虽然男生表白得很清楚,但对于她来说好象已经麻木了,况且她并不喜欢那个男孩。从那以后,于帆就故意躲着文强,即使碰见也装作没看见,这使文强很难过。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高考了,他们都考上了大学,而且碰巧还都在同一个城市。
到大学后于帆也是很优秀的,她喜欢文艺,每天同学们都能听到她悦耳的歌声。没过多久文强就找到了她,继续追求着她,她也不理睬。同寝的姐妹都劝她,都说现在这年头象他这样专情的男孩已经太少了,珍惜吧。
经过大家的努力,于帆终于接受了文强。他们刚开始相处的时候很快乐,时间久了,文强就感觉不开心了,因为他一直都觉得于帆不够关心他,只是他自己一头热。可是他是喜欢她,心里放不下。文强当初觉得只要她和他在一起就够了,都说爱到深处只要看到她就够了,只愿付出而没有任何要求,可真正在一起时却还会有这么多的不如意。
他把自己的想法写了一封长长的信,他对女孩说,她把他当做什么呢,还不如一个要饭花子,给要饭花子一个馒头还很温暖呢,可是他对她这一点施舍也没有。女孩看完信后哭了,是呀,从他们相识到现在,男孩一直都是在给予她全部的爱,而她并没有在意,她感觉自己确实应该好好地用心去爱他,毕竟现在他们已经是一对恋人了。
从那以后于帆将感情渐渐地投入了,她才感觉到爱一个人会这么辛苦,每天她都会想念他,特别看到文强写给她的那些信件,而且她永远都不会忘记文强送给她的生日礼物--一只小船的音乐盒,那只小船代表着帆,文强说与帆风雨同舟。于帆在心中默默地行驶着她的小船,她感觉前行的路上有了方向。
就在他们都沉浸在幸福的甜蜜之中,文强的父母却在暗地里给文强办好了出国留学的手续,这都是在临近毕业时告诉文强的。文强并没有打算要出国,他想和于帆一起在国内读研后再找工作。当他得知这个消息时,他不知怎样对于帆说,要于帆也同他一起去吗,还是让她等他两年呢?
文强见到于帆告诉了他的情况,于帆沉默了许久,最后她说她等他,因为于帆知道她的父母不会让她出国的。那是雨季,也是在那个夜晚,雨下得特别大,他们依偎在一起,任凭那风雨淋湿他们的衣襟。那风雨冲刷不掉他们四年的情感,可是面对即将的分别他们都是那么不舍。
后来文强出国了,于帆在国内读研,他们鸿雁传书,网上见面,偶尔打过洋电话,虽然相隔遥远,于帆始终感觉文强就在她身边,她感觉自己才真正地爱上了虽不浪漫但很有内在的文强。回想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文强总是那么呵护着她,尽管有时她还孩子气,她还总是不在乎的样子。
而现在,于帆常常在梦中,静静的捧着手中的小船,那心中最爱的一叶小舟,就这样的远离了自己的世界吗,还有那风雨同舟的话语,也随那风那雨消逝了吗……每一次,于帆都在噩梦中惊醒,然后她难以入眠。
那又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也是前年的那一天,于帆走在回家的街路上,路两边的灯光闪烁,她不想坐车,只是走着,她不怕淋雨,她也是想念文强吧。她一直向前走着,忽然一把雨伞打在了她的头上,她抬起湿漉漉的脸望去,是文强,她以为她在做梦,她又眨了眨眼睛,真的是文强。
他们什么也没说,相拥在风雨中,伞落在了地上……
……
一只柳树下的故事
矿区确实有这样一种住了大楼的半城半乡的妇人,她们都是跟随在煤矿工作(井下一线的)多年的丈夫办的农转非户口,才加入了矿区家属的行列。她们穿的衣服还没有完全脱掉乡下人的粗俗习气,走起路来很不协调,不是崛起屁股身体前倾,就是左右摇晃,像跳迪斯科的演员,说话总是半土半洋,常常犯连音错误,很简单的一句话,让人听起来很吃力。还特意装出一幅倨傲的神气,在打扮得花里胡哨的外表下隐藏着一个自命不凡的粗鄙的灵魂。正如她们用光亮的皮鞋装着一双又粗又臭的脚。李青艾就是这样一个妇人。
她的丈夫常山是在井下一次跑车的事故中致残的,后来发生病变,下肢瘫痪,生活不能自理,光天化日之下一幅可怜巴巴的样子。他流泪、愧疚、悔恨自己不该冒险违章;她在无奈中感到对生活的失望和痛苦,感到命运在无形中捉弄她。眼前,她的壮实的要终生相伴的汉子——因违章而造成的瘫痪者的活生生的事实,把她倨傲的神气突然降到了冰点,像一个瞎子掉进了永难自拔的万丈深渊。她非常的痛心,难过——默默地忍受着——在懊丧的生活中挣扎。
只有他坐着的可怜的身影在风雨中、在雪路旁像一座会移动的雕塑,双手向前用力拉动两条没有任何知觉的腿,然后,双手托地,用力撑起,屁股在腰部的努力下往前一送,就这样艰难地“走”,简直像一条泥鳅,身后留下一条弯弯曲曲的土印和泥迹。他每完成这样一个前进过程都需要付出最大的气力。嗯!这才是活糟践人,因为没有办法,时常行进在多少个夜晚归家的路上,在雪中,在雨里。
其实,单位已经给他最大的帮助和救济,为他家修起一个做生意的店铺。可她并不满足店铺的生意,趁着丈夫的残瘫,一门心思地想找份“正式”工作,以后的生活也好过一点。于是她喋喋不休地使唤着他,为她的工作,丈夫拖着残瘫的身躯多次出走。
她的工作还没有着落。丈夫已经死了。
她,在大多数同龄人中是不幸的,是很倒霉的。也许是命运的安排。但她有自己独特的先天资本,认识不认识的人都这么说。她不像一个已婚的女人,特别的年轻,像一朵水灵灵的刚出头的含苞待放的荷花。她身材苗条,娇艳灵活,比刚进矿区那阵子简直换了个人儿。
她走路说话洒脱大方恰到好处,笑意中带着两个浅显的酒窝,她使来往行人的目光灼灼,流连忘返。她完全成了矿区一个耀眼的招人喜爱的亮点。
就这样一个她,竟落到如此不幸的地步。
那时候,随丈夫到矿上,她很高兴,也很满足,没有任何不切实际的想法。然而,就在办户口的时候,常山在一次运输中违章操作,双腿被翻倒的矿车轧骨折。在事故分析会上,她痛哭流涕,表露出乡下女人的粗俗和无知;对丈夫的残瘫不知道怎样面对,怎么讲条件与自己有利,胡搅蛮缠,只是表示出怨恨和悲哀;又怨自己没有做好丈夫枕边的安全教育工作,所造成对家境的不幸感到惶恐不安。单位领导针对她家的实际情况,照顾着随前一批给她办了户口,职工自愿捐款献爱心。这对她来说是个很大的精神安慰。在常山出院后,不长时间,他双腿发生病变,没有知觉。夫妻痛哭不已,大夫尽最大努力,医治无效,——他下肢瘫痪。
他每次出门,都是她支使,并把他连背带拖(腿在地上)弄出门外,放到路面上,看着他说:“去吧,去给我找回个‘正式’工作,咱以后的生活还好过些。否则……这可怎么呐?”
于是,他就像个屎虼螂滚粪蛋似地、艰难地、慢慢地在路面上往前蹭。
天气没有变化,太阳撂在煤山尖上,粉红色的阳光非常宜人。在他又完成一个前进过程时,煤山尖上的太阳不见了,出现了一片升腾的黑云,忽闪闪挂在天边,很吓人的。他心里有些焦急,前进的动作加快了。
雨,下来了,来往车辆和行人似乎根本没有人看见路旁的他。
李青艾从家里送出一位矮个子男人,说:
“你的狗,带走吧。”
“就是给你的,我——现在照顾不了它,因为……”他苦涩地笑笑,给她一个无奈的回眸,便匆匆走在雨中。
他是谁?他是一位房管干部。前半年妻子离婚,丢下这条白毛金丝狗,挺好看的一条狗,就受到吃不上食物,有时一天都吃不上一顿,还不时地遭到他的打骂,才变成瘦骨嶙峋的脏兮兮的可怜虫。他想把它扔掉或者给人。李青艾跟他来往是想弄套房子,他答应她,她也答应他,这狗自然也跟她留了下来。她给它舀些剩饭,一块馒头,把丈夫喝的牛奶也给狗倒了半碗,它吃得很香,两人话语投机,配合默契。
李青艾给狗洗澡说:“可怜虫,被遗弃的东西……”
然而,常山在雨幕中,双手向前用力拉动两条无知觉的腿,义无反顾地往前蹭。雨水从他头上浇下来,衣服湿透了,浑身是泥,他什么也不在乎,一心一意想给老婆找份“正式”工作,说真的。
李青艾忧心忡忡地把矮个子送出门,转身对狗说:“宝贝听话,在家看门,我一会儿就回来。”她惦记着雨中的男人,从门后拿块塑料布蒙在头上,把门锁了,正出门时,天空一个炸雷滚过,雨点更密,像银线一样射将下来。雨幕中,她跑着,拐弯,在太平房后边看见前边路旁的丈夫用力往前蛹动。
“常山,常山。”
他没有听见,继续一拖一擦地往前蹭,头顶上又一个连头雷轰隆隆滚过。
“常山,常山”她心疼地跑过去。
“你,你来干什么?让我去吧。”
“来,咱回去,好天再说。”她说着背起丈夫就往回跑。常山在妻子的背上伤心地掉泪了,说:“放下我吧,放下我吧!艾,我——简直——屙裤里了。”便呜呜地哭。
“不怕,屙就屙吧,下这大的雨还怕洗不了。”
回到家里,白毛金丝狗发出叫声,汪!汪!
“这是哪来的狗?”他问。
“矮个子送来的。”她说着给他换了衣裤,把臭气熏熏的屎裤顺手扔在雨中,用暖水瓶里的热水给他擦身上,说:“你成这个样子,到何年何月才能好起来。”
常山非常无奈,面对着妻子对他的照顾和关爱,他没有办法,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好起来。他愧疚地哭了,她给他擦着身上也哭了。
白毛金丝狗仰着头,瞪着黑里见红的眼睛看,又在他身上嗅,他伸过手,“来,你是谁家的?”它舔他的手,还摆着卷起来的尾巴,表示亲热。
她给他舀来饭,常山在被窝里吃:“来,你也吃。”他给狗面条和豆腐,狗吃着,不时地抬头看看,意思是说:“你这么可怜,还喂我东西吃,你真好!
“来,接住。”他又扔给它一块豆腐,它跃起一口接住:“行,真乖。”
它跃上了床,在他的被头卧下,他用手抚摸着它的洁白的光滑明亮的皮毛,一会儿,它微微地闭上眼。
“这狗叫什么名字?”常山问。
“叫宝贝。你说行不行?”
李青艾擦着眼泪说,头上蒙了块白色塑料布,坐在雨中的石头上给丈夫洗那臭气熏天的、使人恶心、呕吐的屎裤;她心里一时有说不出的难受,委屈;她似乎就不该是这样子的。雨水从她头发上,脸上和着眼泪滚下来。她抬起头用湿手把遮了眼睛的头发捋一边,叹气。双眼望穿雨幕,无论怎么她现在都没有办法。已经写信告诉了儿子,说他父亲的病情——下肢瘫痪。
儿子没有复信。
当妈的不放心,又寄出一封,说:“儿啊,妈知道你忙,要十分顾不上就不要写信回来了。你爸——我伺候。”
常山坐在房间的地上:“宝贝,过来。”小狗跑过来,他用木棍从方便面箱上边捅下一根香肠,宝贝摇着尾巴,仰脸,他剥香肠,一节一节地喂它,它吃得津津有味。
矮个子从李青艾店铺出来,乐滋滋,转身对她说:
“没事,明天就给你搬。”
中午回家,李青艾对丈夫说,明天搬家,你早些下去看门。常山应着扭头看看矮个子,笑着说:“辛苦你了。”心想:小子唉,给我受吧,我的老婆不能就那么容易——混蛋!
满天星斗闪烁。
李青艾把丈夫唤醒,帮他穿衣服,裤上的尿迹和泥土脏兮兮的,抖一抖,脏穿上,长事了,无需要天天洗。无意也弄醒了睡意浓浓的宝贝。她把丈夫背出路上说:“去吧,搬家的事你就放心。”宝贝也跟了出来。
“宝贝,回来。”她叫狗。
宝贝在常山身边站着,看着空旷朦胧的夜色,它有些恐惧。
“回吧,你回吧!叫它。”
“不回来,就叫它跟你去吧。”
常山在路上吃力地往前蹭,它警惕地慢慢地跟着,东张西望。
矮个子找来车,还叫了两个人帮忙,很快就给她把家搬完了。
他们没有喝她的酒,也没有吃她的饭,抽烟倒是——阿诗玛。
“辛苦你们了,快坐下抽烟,一会儿喝酒吃饭。”常山感激的心情而又无奈地笑着说。
住了大楼两个月以后,李青艾多次埋怨丈夫说:“你什么时候能好呢?我的命苦,跟上你活受罪,要不是——鬼才住这又脏又臭的一层呢。”因为矮个子说过几次,要住,就住个好层次,钱不够他给填上。需不知,她现在住的一层也是领导特意照顾常山残疾出入方便,如果说常山不是在井下受伤残瘫,凭他的工龄是不该住上大楼的,而今住一层到现歪了。
常山自从出事到现在,妻子不管怎么着,和矮个子在家也好,在店铺也罢,他都说不出口,看见的当没看见,忍着痛,忍着恨,抚慰着受伤的心灵——宽恕吧,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个废人。有时候他也烦恼,忏悔,愤怒,眼巴巴看着那深恶痛绝。之后似乎又觉得是理所当然——他什么都不能做了。而她要求的“正式”工作,还没有个结果,仿佛又有愧对老婆的关心和体贴的感觉。然而他心烦意乱,坐立不安,于是就出门频繁,有时候宝贝跟着,有时候他一个人,领导太忙了——难找。他能理解,因为自己的儿子也是个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