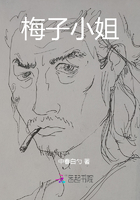又是来年夏季,天气炎热。
莫夫人病重,洛萧澈不待我开口便道:“你且回去尽些孝道。”我自是感激,便连夜动身去了。
莫夫人已是极其严重,我心内疼痛,泪眼模糊。莫老爷叹了口气,道:“原本不予告知你,怕你担心,如今,看是越发严重,这才通知了你。”我转过身去,掩了掩泪痕,极力掩饰着自己的悲痛:“父亲怎的这般糊涂,这岂是可以瞒的事么?若是母亲有了好歹,女儿这一辈子都不会安生。”
莫老爷几日不见也是因的莫夫人的病头发白了不少。我从宫里带了最好的太医为她诊治,道:“怎么突然得了病,还这般严重。”太医开了方子,悄声道:“娘娘,令尊怕是……娘娘节哀。”
我心情复杂,嘱咐道:“你且先留在这里照顾莫夫人的病,什么情况与我禀报,先不要告知莫老爷。”太医点头称是。我吩咐妥当,这才心事重重在床边坐下,莫夫人双眼紧闭,我看着又要难过,袭月道:“娘娘先去休息吧,连夜来,总该累了。”
一夜无眠。
莫夫人悠悠转醒过一次,复有昏睡过去,只费力道:“怎么青果没来……”我这才想起自我昨夜出宫到现在并未见到她,平常时间她早该到了。心下想着,便服侍莫夫人用了药之后动身去了宫文琦的住处。
开门的倒是个眼生的小厮,那小厮并不识得我,我又只带了袭月,他以为是哪家的夫人,道:“我家夫人不在。”我心生疑虑:“可否留了话去哪了?”小厮道:“夫人去给一位故人祭拜,怕是晚间才能回来。”袭月看了看我的脸色,我疑窦顿生:“故人?”我与青果也算是坦诚相对,她何时有这样一位故人得以让她舍了莫夫人先去祭拜?
我循循诱导:“可说这位故人葬在何处?”小厮道:“这就不清楚了,我也是刚来的。”袭月塞了碎银,道:“麻烦小哥了,你家夫人回来还请麻烦相告一声。”小厮笑道:“那是自然,夫人要么进来先等等,小的这就去请人去请夫人早些回来?”我摇了摇头,心中疑乱不堪。
袭月追过来,道:“娘娘……”我看着她,道:“或许,他们都骗了我。”袭月不语,只道:“便是如此,怕也是好意。”我苦笑,道:“我们先回去吧。”
莫夫人一直昏睡不醒,莫老爷放了一切生意,每日守在床前,在古代,像莫老爷这般钟情之人,倒也少之又少了。
晚时青果姗姗来迟。见我面色古怪的行了礼,我淡淡道:“宫夫人今儿去祭拜故人?”青果低头不敢看我,未待我在说话,宫文琦便跟了来。
“娘娘。”他恭敬行了礼。我不语,场面一时寂静。
“娘娘,这是欧阳公子要臣给娘娘的东西。”宫文琦抬手,是一管玉箫。袭月接过来递给我,我苦笑,这是欧阳宇鸿贴身的玉箫,虽然他甚少拿出来,我却记忆犹新。
“他说了什么。”宫文琦道:“他道自己无碍,怕娘娘疑心,便留了这玉箫作为纪念。”“无碍?”我笑得凄然:“他总是这般的性子,便是自己死了,也要活着的人好受些。”青果道:“小姐……”宫文琦见我如此,有些薄怒:“我们便是如此,也是为了娘娘,青果那日小产,也是乍然听闻心急娘娘。”我迷茫的看着他,只剩下苦笑:“罢了,本宫也没有怨你们,你们都是为了本宫好。”
莫夫人奇迹般的好起来,精神抖擞,与我们说了许多话,便是:“我”小时间的事情也连回说了几遍。我心内欢喜,忙唤了太医,太医道:“这是回光返照,大限已近了。”顿时一惊,心内像是生生捥去了一块。
次日,莫夫人便没了。
按照大晋国例,除非是先皇与太后,再是皇上,不然皇后是禁止参加一切丧祭的。
我被莫老爷强行送进了宫,第一次我终是忍不住,痛哭失声:“女儿一直未曾尽孝道,如今母亲病逝女儿竟不能送她一程,女儿心里何安?”莫老爷亦流了泪:“若是为了此事惹恼了皇上,迁怒于你,你母亲又如何能安心的上路?”
终还是妥协了,我心如死灰,先是得知欧阳宇鸿的死讯,如今莫夫人也没了,我突然一阵悲凉袭上心头。
回宫之后我一直提不起精神,不出半月整个人便瘦了一圈。
与青果也甚少联络,洛萧澈素来平淡无波的眸子如今看我也夹杂了许多柔情。“娘娘,宫夫人求见。”我懒懒的抬头:“她如何来了?”袭月道:“说是皇上特意宣进宫来陪娘娘的。”我轻轻摇了摇头:“让她回去吧,我谁都不想见。”袭月顿了顿,终是出去回了话。
一别几日,青果因了洛萧澈的允许得以经常入宫,我便是从未见过。
袭月道:“娘娘,你若不见,宫夫人怕是心里难安。”我冷漠不语,如今,我自有自己的打算。
我与洛萧澈仍维持着表面的平静,只是心里越发不能接受他,接受不得他残忍的心,肮脏的手。
泽儿很少来了,偶尔我远远惆怅的看着他,心里一直自责,我的孩子,娘亲对不起你。
青果还是固执的来,我仍是固执的不肯见她。
袭月有些不忍,好言相劝:“我家娘娘近日心里难安,夫人也不必非要急于一时,时日久了,该好的自然都会好起来。”
青果只是感激一笑,掩不去浓浓的倦色:“多谢袭月姑姑的好意,只是我心里实在觉得对不住小姐。”袭月惶恐:“夫人言重了。”
我心无所动,洛萧澈挑眉看我,半响道:“你果真不若以前。”我淡漠的看向他,心碎一地,断然拼凑不起来了。
他开始注意起我的变化,仔细看我:“是哪里出了变故?”我看着他,眼神没有聚焦。他有着让女人为之疯狂的地位权势与这张迷惑众生的脸,而我看来,一切都是讽刺罢了。
“皇上觉得臣妾哪里不妥么?”我淡然问他。他寒着一张脸,冷着一颗心。“竟是孤又太过纵容你,以致你竟敢这般对孤言谈。”我苦笑:“臣妾该哪般对待皇上?抑或说,皇上需要臣妾装成哪般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