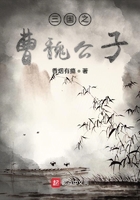另外一个男人是本市最大一家报纸的理论部主任,开着白色本田来参加聚会的他告诉素问,经常作为党的喉舌写评论文章的他,私下里研究乔治·巴塔耶已经很久了。男人说他的理想,其实是躲进小楼做学问。他说他发现人类的终极问题,其实就是色情的问题。色情里面,才有真正的生和死。而素问的研究对象卡夫卡,简直充满了孩子气。
男人还说,人最大的痛苦,是不能做回自己。
聚会散了的时候,大家都起哄似的,撺掇第一次来的男人做护花使者,送素问回家。男人就笑着说太好了,当仁不让的样子。两个人把车驶进深夜的大街时,后面还有人追着汽车,玩笑似的喊着,一定要擦出火花啊,没有火花就对不起大家啊!素问和那男人都假装大大咧咧地,没有理会。连头都没有回一下。车窗的外面有了驰骋的风声时,两个人却一前一后,突然沉默了起来。好一会儿,前面攥着方向盘的男人才说,我们找个咖啡馆坐坐。素问完全没有考虑,就说了好。
在咖啡馆里,男人再次拣起了色情的话题。他喝着拿铁,用那样干净,圣洁的语气,再次提到了乔治·巴塔耶,提到了亨利·米勒,提到了很多外国人,甚至维多利亚时期的地下小说。男人说我们这个国家,这座城市,永远视色情为洪水猛兽,我们都太落后了。男人还说,文化人最高的追求,是应该走过文化,站在一切文化的对立面。
女人忙不迭地点着头,在暧昧的灯光中,通红着脸颊,目光流转着,把身边的男人,惊为天人。趁对方呷咖啡的时候,她暗暗掐灭了包包中的手机,抵死不愿意对方晓得,几公里远的某间屋子里,有个嗷嗷待哺的鹅黄小儿,而且很可能,他的屁股上,正糊了一滩稀屎。
当天用很激昂的情绪,理直气壮地探讨了若干关于色情的理论知识,两个人才感觉到有点累了。时间接近凌晨一点的时候,双方突然有了落寞和惭愧交织的感觉。落寞是夜晚的安静和寒气带来的,而惭愧,是彼此发现彼此,说的全是变巴变巴过来,别人的话。
男人和女人都有了一瞬间的气虚,不晓得自己在干着什么,或者想要干着什么。
沉默了上十分钟,男人把自己的脸刻意躲进了灯光的阴影中,半天,才幽幽传过来一句话,你晓得,我今天晚上,好想要你……
素问没有做声,眼泪却突然迸溅了出来。她想他迂回了大半个晚上,终于说了句人话。呵,见******鬼吧,乔治·巴塔耶。滚回姥姥家去吧,亨利·米勒。
当然,还包括维多利亚时期的地下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