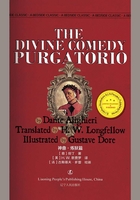印象中的妹,是孱弱的,苍白的女孩儿,永远跟在我身后。捉蜻蜓时,她只是充当发现者的角色,真正去摇蜻蜓网的,自然是我。
那时的妹清秀得很,细细的眉眼极像画中的古装人儿,稍稍着红戴绿,便立即灿烂起来。难怪祖母每每为其擦洗面颊时都要唱一首自己编的歌儿:好白呦,好俊呦,好一个小妮子呦……那时节,妹就羞涩涩地扭过脸去,要不干脆扎到祖母的怀中,无声地乐着,很斯文的样子。
连父母都奇怪,怎么天不怕地不怕、男孩儿般的我,竟会有这么一个怯怯的妹。想来,一件件地让人觉得有趣。
比如那年月唱火了样板戏,小小的我因唱李铁梅而红遍了小学校。于是父亲母亲的同事一见我面便搂将过去不由分说逼迫唱上一段。于是,我的开头语大概永远是那句:“我给叔叔阿姨唱支歌儿。”遂摆出刘长瑜的样子,捏着衣襟唱起那段《都有一颗红亮的心》。
掌声永远是热烈的,众人投向我的也是热烈的注视。于是便洋洋得意起来,不顾了身边的妹。偶尔地稍稍留神,发现妹紧缩在母亲的棉袄里,不敢看我,细眯的眼,露着钦羡和自豪来。
我知道,那一刻妹把我当成了偶像。
然而,妹也是倔的。
在玩猪蹄或羊脚上那块骨头的年纪,她整日地蹲在自己划定的一爿小地方,专心致志地玩。圆圆的皮球或沉沉的布口袋往天上拋时,她那专注的表情十分可爱,充满了让人爱怜的成分。
我们比她大一点儿的女孩儿常常自充大人,绝不将妹一般年纪的人夹杂在内玩耍。妹也极有志气,不央求,一人闷着头玩给你看,而且玩的技艺也高超得很,遇到我或者别的同伴发现,便伯乐一样地推荐到自己一组里来,于是我们的队伍便立即因有了她这个新鲜血液而显得强大起来。
但她却不自满,摆出无所谓的样子,很超脱。别人不再带她一起玩,她也无怨言。转过身,又默默地玩开去,有时入了迷,甚至忘了吃饭和睡觉。
母亲常为此而有些恼。自然是担心女儿小小年纪过分贪玩而误了身体的发育。更重要的,也是母亲希望妹能像我一样合群,不那么总是形只影单地自己做游戏。
“该睡了。”母亲有好几次冲着黑夜路灯下的妹说。那时,孩子们大都被家长叫走了。只有妹一人,跑到我们大孩子刚刚玩过的路灯下放松地、如入无人之境似的玩着。
妹不理会母亲的叫喊。低着头仍看着那些排着队的猪蹄骨和羊脚骨。母亲后来明白,如果妹没玩够,是不会轻易收那些“兵”的。
常常是大睡着的我不知何时妹回来了。她不开灯吵我,静悄悄地睡下,第二天也不再念及前晚的玩兴。
妹是属于那种天生艺术气质的人。手细细的,长长的,教文艺课的老师总是看着那双手感叹:这该是弹钢琴、拉小提琴的手!只因那年月家境不好无法觅得一架大乐器,爸托人从上海给她买了一把小提琴,她爱死了那把琴,每天放学疯了似地跑回家对着镜子练。记忆中她还被一个教芭蕾的老师找去训练过。那老师不知什么时候无意中发现了亭亭玉立的她的学生。那几日,妹每天喜气洋洋地离开家,又兴高采烈地回来,很幸福很快乐的样子。吃饭时,急不可耐地讲着老师教的基本动作。只是这种情形持续不长,不久妹重又闲暇下来,便又闷头读书了。
妹读书不像我这般马虎而无心,也不像我这样遇到喜欢的书就不撒手,不爱看的连碰都不去碰,妹极听父亲的话。那时父亲还是个业余作家,借着他年轻时代的梦想,一直在当工程师之余偷偷地写作。偶尔他也推荐书给我和妹看。那时我多半像完成任务似的只记大概内容和几个书中人物,不像妹,能将某些精彩段落倒背如流,并且活用得也极准确和自如。尤其是那些唐诗宋词,我常常在背着思想就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从不用心。被父亲叫了去,站在他面前那一刻是记得的,转过头去玩了,便忘得一干二净。我总是能给自己找些非常合理的借口,比如记忆力不好等等,父亲也没办法。
妹不是这样的。她在儿时对诗词的感觉和理解就已达到了一个与她幼小年龄不相符的层次,因而至今她的美妙散文无不受其影响和熏陶,并使她的文学潜质在一个极其优雅的格调上得到了尽情的发挥,这是我一直都暗暗钦佩的。只是出于年长于她,难免被自尊心所驱使而不情愿放下架子来承认罢了。
妹读《红楼梦》时很小,还没到当时被允许的年龄。始作俑者是我,我偷着从父亲高高书柜的最上端翻腾出来,然后捂住被子打着手电筒看。到宝黛读《西厢》时,不免也心中“嗵嗵”作响,“葬花”一处更是跟着黛玉落泪。妹总是要接着我看下去的,她不如我那样大张旗鼓地读。她不声不响地看,很用心。除了情节她还会把那些绝妙语言在心中默背。往往一本书看下来许多有代表性的警句就留在她小小的脑袋里了。譬如“亭亭玉树迎风立,婉婉香菊带露开”等等,甚是能代表她的欣赏力。
不过,读书入了迷,妹也是很固执的,甚至到了倔的地步。倘若她正在读着一本书,她是不会受别人支配的。我记得有一回她发誓用一整晚读完一本书,于是就躲在被子里看,一直到深夜。不知怎么被母亲发现了,于是妹就被告知眼睛如此下去会坏的,而且将头缩在被子里不卫生等等。妹哪里听得进这些,她只想让母亲快快走开,好让她重新自由自在地读下去。
母亲没容许她那样。妹反抗了。她从床上起来,穿了衣服,抱着大书拿了小凳到走廊里去了。
母亲更恼了。说妹这样会弄坏本来就弱的身体,而且夜深有凉风吹到骨头缝里就会有炎症产生。妹偏不听从。母亲哄劝加严厉的家长命令,妹岿然不动,眼神没有一点儿离开那书的意思。
就那样,妹和母亲僵持着,一个站着,一个坐着,站着的人看着坐着的人而坐着的只看膝头的书。
最终是母亲屈服,她抱了一件大衣给妹披上,然后再找双厚鞋子让妹穿。见妹不再理会,母亲便回屋去了。久了,妹以为自己的行为得到默认,便也名正言顺了似的不再征得父母同意,径自搬起小凳子到走廊里去看一通宵。第二日我醒来时发现她已不知何时回来睡了,脸上还留着读过书的满足。我一直以为妹的心事重重和她的多愁善感是从母腹中带来的。据父亲说,母亲在怀着妹时常到医院去看些不大不小的病。那些都是挺折磨人的症状,让医生总是费很大的心神方能看出一些眉目。于是,那些磨难也就留在了妹的身上,致使她从母体分离出来的那日起就敏感而瘦弱,脸也是苍白的。可是我以为她的强悍的,彪形男人也比不了。
有一年,我们还住在东北的黑龙江,在那个工业重镇,我们以烧煤取暖。那儿的煤质极好,黑黑的,有棱有角的煤块如水晶一样透亮。孩子们常常在没有玩具时找几块来当棋子儿,摆摆也极像回事儿的。我们那俄式的红砖楼房外面总有一个多宝格儿式的煤池子,每家的煤按住房顺序盛在里面。玩累了孩子就会无所事事地坐在水泥砌的煤池子上,把脚搭在煤堆上,那是刚刚卸下的煤,散发着特有的味道,孩子们就像坐在小河边那般用脚试探着煤的结实与松软,全然不顾母亲新给洗的鞋子是否会脏得不成样。有时妹也夹杂其中,并快乐不已地“嘎嘎”笑着,声音极大。煤往往是马车运来的,车老板儿脸上凹下去的地方像夹了根根白线一样,有趣得很。车老板儿把车停在楼门口后,便一手举着马鞭一手拿着煤场开出的小票,大声唤着订煤户主的名儿。这时就有孩子欢天喜地地涌过去,围着马车一本正经地品评着煤的好坏。煤好时,块儿是很大的,极少有粉末儿,这说明买煤的那家是有权有势或有路子的。我们家那时也只有望“煤”兴叹了。我们没亲戚在东北,父亲是1957年因右派言论不得已而到这个地方来的,一点儿靠山也没有。所以,尽管每次车老板儿在叫我父亲的名儿时,我们都还抱有幻想地冲出去,妹那时就小兔子一般跑到马车旁,大人似的看看车厢内的煤,然后大声喊着:“咱家来好煤喽!”遂跑回屋向父母报信。
余下的时间里,父母换上旧衣裤,我和妹一人一个簸箕,很雄赳赳地来到煤堆旁,于是,一下午或一上午的艰苦卓绝的劳动便开始了。妹轻捷地跑来跑去,用细嫩的手指牢牢地抓着簸箕的两侧,似乎孩子无法承受的重量都集中在她的手上了。
大人干得多,一会儿便累了。孩子则不然,只觉兴奋得很,而且认为显示自己价值的时候到了。待煤池子装满,剩下一小山丘般大小的煤堆时,我和妹便抢着一簸箕一簸箕地往家里运。祖母那时正在厨房,她已打开了盛煤的煤箱。那煤箱像养动物的小窝,最上面搭着一个厚厚的木板,可掀起盖上,往里加煤时就从那儿倒进去。之后,上面便蒙上一块好看的塑料布,以后就可以在上面摆切菜板和面板等烹饪的家什,到过年时,上面便是摆饺子的地方了。煤箱下面是一个动物出口一样的小方孔。祖母就一煤铲一煤铲地从那儿往炉膛里添煤,于是火一下子就旺起来。所以每当我们家来煤时,祖母必等在楼上,打开煤箱上的盖儿,我和妹就一趟趟地走到煤箱前,由祖母接过簸箕,呼啦啦地将煤倒进煤箱里。如恰巧里面的煤用光了,那倒进去的少许煤落地的声音就像小孩儿抓了一把沙子撒向风中一样,没有什么大的动静。每每这时,妹和我都很不满足自己那样小,并且不是个有气力的男子汉。有时,妹跟在我身后,亦步亦趋地踩着楼梯往上走,我就只听得见她气喘吁吁的声音从她那单薄的身子里发出,十分的让我怜惜。有时,她冲到了我的前头,我看她小小的背影在与沉重那么不协调地抗争着,便又生出无限的敬佩来。时至今日,我总为她现在的弱不禁风而抱怨自己当年没多干一些活儿。
妹虽不是家中长女,但却以她的细心博得了每一位家庭成员的信任。祖母给家乡亲戚们准备的衣裳包裹放在哪里,父亲顶顶重要的文件存在了哪个抽屉中,母亲常常忘记的瓷器装在了哪只箱子,即使那时妹在自己的家中,打电话过去问她,她会一一地告知。甚至父母为什么事有了争执,只要她出面,便会由急风暴雨变成风和日丽了。所以父母总要说一句:二女儿真是个懂事的孩子!祖母说,她的二孙女是最会疼人的孩子。每每这时,祖母就会哼歌儿似的念起父亲早年写的一首应该叫顺口溜的小诗:“太阳落到屋角下,二丫放学回到家。进得门来咧嘴笑,小脸红得像早霞。叫过爷爷叫奶奶,叫过爸爸叫妈妈。用手紧紧红领巾,想要说话羞答答:爸爸妈妈听我说,爷爷奶奶别打岔儿,今天少先队开了会,俺想入队批准了。辅导员给俺系上了红领巾,队员们都和俺把手拉。说俺学习好爱劳动,人人都把俺夸。爸爸妈妈抿嘴乐,爷爷胡子笑开了花。奶奶不知说啥好,硬把二丫怀里拉:哎呀呀,我的心肝小二丫,真是顶呱呱,明儿奶奶去上街,给你扯布做花褂儿。”
祖母这么背诵着,眼里流露出她对妹常有的喜爱。并且她就认定这首诗中的二丫是我妹无疑,并且她就果真把妹拉到怀里:“哎呀呀,我的心肝小二丫,真呱呱!”一到高兴时,祖母就会创造性地改词儿。
久了,只要祖母又念叨这些字眼儿,我就知道妹必定是又做了什么好事情让她老人家高兴了。当然,多半祖母是忧愁的,她担心妹的身体怎么可以承担那么耗神的写作。我自然是不会对她提及妹是如何住在四周白色的医院里忍受着病的煎熬和治疗的缓慢过程,也不会向她描述妹曾怎样地坐在轮椅里被我和她的丈夫不停地推往按摩室,因为支撑她腰的那根骨头需要接受十分冷酷的医治。不过,当祖母看到她的二丫必须躺在硬硬的床板上才能矫正她的腰椎并且还要捧一块木板去写她的文章时,祖母就会躲到一旁悄悄流泪,继而又笑眯眯地去夸妹的坚强。
现在,我就坐在汉堡温暖的家中,从德国去想象妹在做着什么。窗外的一棵叫不出名字的树正在慢慢地变绿。几日前才露出的豆粒儿般大小的芽儿,已经现出茸茸的叶子了。远处,尖顶教堂传出了“当当”的钟声。我想,妹如在这样的气氛里必是又会做她的文章了。
那必定是一篇极妙的美文,像我以往读过的每一篇。
1995年于汉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