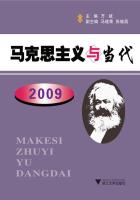必须要记住的是,基本动机提供了一套现成的价值层次,这些价值是以较高的和较低的需求、较强的和较弱的、较重要的和较无所谓的关系,彼此相互依存的。
这些需求是按照整合的层次,而非按照二分对立的方式来加以排比的。也就是说,它们彼此一一相连、相互依赖。为了实现某种特殊才能的较高层次的需求,可以说有赖于安全需求的连续获得满足;而安全的需求,则可以说即便在静伏无为的状况下,也是不会消失的(我所谓的静伏不动,是指饱食一顿之后仍会再饥饿的状况。)。
这点意谓着,退向较低层需求的退化过程永远可能存在,而且在此层次脉络中,不仅要将此退化过程视为病理的或病态的,而且更应该将之视为对整个有机体的整合是绝对必要的,同时亦应视之为“较高层需求”之存在与作用的先决条件。安全是爱的先决必要条件,而爱又是自我实现的必要条件。
因此,这些健康性退化的价值选择,也应该被看做是正常的、自然的、健康的、发乎本能的等,看作是所谓的“较高层次的价值”。显然,这些价值亦处于一种彼此相互辩证与相互律动的状态中(或者,正如我常喜欢说的,他们是有层次的整合,而不是二分的对立。)。最后,我必须要处理的是清楚、且具描述性的事实,亦即大部分人在大部分时间里的情形是,较低的需求与价值比较高的需求与价值占优势。也就是说,一般人常会受到退化拉力的影响。惟有最健康的、最成熟的、最发展完全的个人(并且也惟有处在良好的,或相当良好的生活环境下),才比较会选择,和偏爱较高层次的价值。之所以如此,很可能主要是因为获得满足之较低需求的基础稳固,而且较低需求一旦获得满足,便会呈现静止与休眠状态,因而不再受到退化拉力的影响。(同时之所以能假定需求获得满足,显然也假定了一个相当美好的世界。)
以上论点可以用一个陈旧的方式概略言之,亦即人类较高层次的本性建基于人类较低层次的本性,较高层次的本性需要以较低层次本性为基础,并且如果缺少了这个基础,较高层次的本性就会崩溃瓦解。换言之,对大多数人而言,如果缺少了一个已获得满足之较低层次的本性作基础,则人类较高层次的本性便难以想像了。而发展此一较高本性的最佳方式,就是先去实现较低之本性,并使之获得满足;此外,人类较高层次之本性亦建基于目前或先前便已存在的良好,或相当良好的环境中。
言外之意便是,人类较高层次的本性、理想、抱负和能力的基础并不在于舍弃本能,而在于满足本能。(当然,我前面所说的“基本需求”并不等同于古典弗洛伊德所说的“本能”。)即使如此,我的解说方式也已指出有必要重新检验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他的论点过时已久了。另一方面,此一说法与弗洛伊德把生命与死亡的本能以隐喻方式加以对立二分的看法,具有某种同质性。也许我们可以利用弗洛伊德的基本隐喻以修正具体的叙说方式。在进步与退化,较高与较低之间所呈现出的这种辩证关系,目前已被存在主义的学者用另一种方式说了出来。除了我尝试尽量使我的说法较接近于经验上与临床上较可辩证,或较不可辨认的素材外,我看不出这些说法彼此之间有多大的差别。
即使是我们之中最完美的人,也不能免除人类基本的困境:既是纯粹的受造物同时又肖似于神,既强且弱,既有限又无限,既是纯粹的动物同时又可超越于动物之上,既是成人又是孩子,既怀有恐惧同时又充满勇气,既会进步也会退化,既渴望完美又害怕完美,既为蚂蚁亦是英雄。这也就是存在主义所一直努力要告诉我们的人类困境。我觉得,根据我们目前已有之证据为基础,我们必须同意他们的看法:此种二分对立的困境及其辩证的关系,是精神动力学和心理治疗之任何终极系统的基础所在。此外,我认为它也是自然主义之价值理论的基础所在。
三千年来我们习惯于根据亚里斯多德的逻辑方式(A或非A二者彼此全然不同,且互相排斥。你可以选择其中之一,非此即彼,但是你不可以二者同时皆选),来作二分对立、区别与划分;然而放弃此一习惯却是相当重要的事,甚至是关键之所在。尽管很难,但是我们仍必须学习以整体的方式,而不要以原子论的方式来思考。因为所有这些“对立的”情形,其实都以有层次的方式被整合了,尤其是在健康人身上更是如此。而且,治疗的根本目标之一,就是要改变二分对立与分裂的情形,把看似水火不相容之对立物加以整合。我们肖似于神明的特性就是建基于我们的动物性之上,同时也需要我们的动物性。我们的成熟性不只是由于放弃了孩童的天真,而是因为含摄了儿童善良的价值,并且是将之筑基于其上的建设。各种较高的价值都是以有层次的方式整合了较低层次的价值。总的说来,二分对立形成了病理学,而病理学使用的正是二分对立的方法(请与高斯坦所论之有效的隔离概念加以比较)。
正如前述,价值的一部分是在我们之内被发现的,但是,价值还有一部分则是由每个人自己本身所创造或所选择而出的。“发现”并不是把我们所赖以生存之价值导引出来的惟一方式。自我研究发现,严格单义的东西,只指一个方向的手指,只用一种方式便可满足的需求,是很稀有的事。几乎所有的需求、能力和才干都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予以满足。虽然这种不同的变化有限,但它仍是一种多样的变化。天生的运动员有许多不同的运动任其选择,任何个人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去满足爱的需求。音乐之才无论吹笛子或吹黑管都一样可以得到快乐。大智之士不论成为生物学家、化学家,还是心理学家都同样会感到快乐。任何怀有善意的人都会认为世界上充满了各种不同的事由与责任,等着他以同样满意的心情去奉献。也许有人会说,人性的内在结构是软骨质的。它就像树篱笆一样,可以修剪,亦可以导向,或甚至就像一棵水果树,可以修整成一面树墙。
选取和放弃的问题,始终一直存在着。即使是一个试测老手或一位优秀的心理治疗医生,很快便能概略看出一个人的才干、能力、需求和人品,很快就能为当事人提出相当妥贴的职业忠告,仍遭遇到同样的问题。
此外,当一个人正在成长,模模糊糊地看到命运的行列,他可以在其中作选择,并配合机运,配合文化上的赞成与责难……当他渐渐决定献身于(是选择?还是被选择?)例如作个医生,于是如何自我造就、自我创造的难题,很快就浮显出来了。遵守纪律、工作努力、延缓享乐、强迫自己努力、塑造并训练自己,这一切,即使对天生的医学人才而言,都是必要的。不管他多么热爱他的工作,为了整体之故,他仍然必须吞下许许多多的琐碎杂事。
或者换个方式来说,以成为医生来实现自我,意思是要作个优秀的医生,而不要变成一个庸劣的医生。这样的理想,当然一部分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一部分是文化教给他的,还有一部分是从他的内在流露而出的。他所认为之良医应该具有之一切,与他的才干、能力和需求同样都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
在《心理分析与道德价值》一书中,哈特曼否定了道德命令可以从心理分析的研究结果中导引而出。此处“导引而出”的意思究竟是什么?我认为,心理分析和其他揭发式的心理治疗只不过是把人性内在的、较生物性的、较属本能的核心予以显露或铺陈。此一核心的部分,当然就是某种偏好与渴望,而这些偏好与渴望,即使很微弱,但亦可视之为以生物性为基础的内在价值。所有的基本需求均属于此一范畴之中,而个人所具有之天生才干与能力亦复如此。我并没有说这些都是“应该”或“道德命令”,至少不是就其古老与外在的意义而说的。我只是说它们内在于人性,此外如果否定它们、挫折它们,便会造成心理疾病,并因此造成罪恶,造成罪恶与疾病的重叠,虽然两者并非同义。
同样,雷德利也说道:“一是对治疗的探讨变成一种意识形态的探讨,那么一定会大感失望。就像惠利士所明白表示过的,因为心理分析无法提供一种意识形态。”当然,如果我们采取“意识形态”的字面意义,的确如此。
不过,还有一些十分重要的事被忽略了。虽然这些揭发式的心理治疗并不提供一种意识形态,不过它们的确有助于“揭发”和至少显露出内在价值的基本原理。
这也就是说,揭发式的、深度的心理治疗医生可以帮助病人发现他(病人)一直朦胧地追求、向往与需求的一些最深刻、最内在的价值。因此我主张这种治疗与价值的探索息息相关,而不是像惠利士所说的毫无关系。事实上,我认为我们可能很快就可以把心理治疗定义为价值的探索。因为终究说来,自我身份的探索就其本质而言,就是探索一个人自己内在的真正价值。尤其是当我们回想起自我认知的增长(和自我价值的澄清),其实是与对别人和对一般现实之认知的增长(和对他们价值的澄清)相互一致的,这时就更能了然于怀了。
最后我认为,时下流行强调自我知识与伦理行为(价值实践)之间有一个(假想的)大鸿沟,很可能其本身就是一种病症,代表思想与行为之间根深蒂固的裂缝——虽然此裂缝就其他性格形式而言并不如此普遍。这一点,很可以归结于哲学界向来对“是”与“应该”和“事实”与“规范”之间所作的二分对立。据我观察,较健康的人,高峰经验中的人和努力设法将固有之良好特质与良性的歇斯底里特质予以整合的人,普遍都没有这种无法跨越的鸿沟或裂缝。在他们身上,清晰的知识立即流露为自动自发的行动,或是伦理的实践。也就是说,只要他们知道什么是该作的,他们便会去做。那么在较健康的人身上,这个知与行之间的鸿沟还留有什么样的障碍呢?只有现实和存在中所固有的问题,即只有真正的问题,而没有虚假的问题。
只要这个论点正确无误,那么深度的、揭发式的心理治疗,就不仅具有祛除疾病的功效,还可以是合理的、发现价值的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