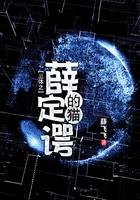(一)
下班前,苏以真接到钱文薏的电话,说晚上大学同学聚会。在来福士广场的港丽餐厅。“听说杜原会携眷出席。打扮得漂亮点,把那小女人比下去,让杜原后悔——”
隔着电话,苏以真恨不得一手捂住那个大嘴巴,再三关照:
“这件事只有你一个人晓得,要是告诉别人,我是肯定肯定会生气的。”
钱文薏让她放心,“我这人最有分寸了,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心里清清楚楚。”
晚饭时,杜原果然带来了女朋友,长相甜美,娇小玲珑,说话嗲得像湖州粽子。一众男生私底下都夸杜原眼光不错。钱文薏却不以为然,说杜原是乡下人的品味,一点儿也不大气。
“现在的女人,不到一米六根本就谈不上有身材,脸一看就是化妆出来的,老粉涂得比一块钱硬币还要厚,又不是上舞台,居然还戴假睫毛,口红艳得像要吃人,哪里比得上我们苏——”苏以真不待她说完,挟起一块虾胶鸡翅塞到她嘴里,加重语气:“多吃菜,少说话。”
钱文薏并不罢休,两杯酒下肚,居然又劝苏以真想开些,放开怀抱,“天涯何处无芳草——”弄得几个同学都问苏以真是不是失恋了。苏以真只好瞎编,说前阵子搞办公室恋情,被甩了。同学都表示愤慨,说那男人一定是近视眼,眼光绝对有问题。
钱文薏在一旁咯咯直笑,“巧的很,这男人也姓杜——”
苏以真笑咪咪地把她拉过来,在她耳边道:“再敢多说半个字,以后就不是朋友了。”
散席后,大家说去泡吧。苏以真要回家,被钱文薏硬拉去了。喝了好几轮,每轮走几个老的,又来几个新的,手机一圈圈地打,到最后,原先的同学已所剩无几,都是同学的同学,朋友的朋友。没几个认识的。名片雪花似的散。苏以真手里抓着一把,大多是些会计事务所、银行的白领。彼此说些不着边际的话,你好我好大家好。苏以真几次要走,都被钱文薏留住。
“我是要喝到high的,你走了,谁送我回家?”
苏以真只有留下来。钱文薏劝她打起精神,“你看,这里坐着的全都是精英、青年才俊,你伸手一捞就是一把。哪个不比杜原强?你对他们笑一笑,他们骨头就要轻三两——”
苏以真恨恨地道,“看着吧,下次我要是再把心里话告诉你,就从东方明珠跳下去。”
钱文薏打个酒嗝,说,其实暗恋也没什么,不丢人。苏以真道,是不丢人,但也不必整天挂在嘴上。钱文薏道,是杜原那小子没眼光,等我给你找个比他好几万倍的男人,活活气死他。
苏以真叹了口气,幽幽地说了句:“他又不晓得,怎么气得死?”
钱文薏说她,“所以说呀,现代女性哪有你这样犯傻的。都六、七年了,要是早点说出来,现在小孩都读幼儿园大班了——你就憋着吧,憋到人家结婚,还要倒贴一封红包。人财两失。”
苏以真不说话,陡的拿起旁边一瓶酒,往嘴里灌去。
这一晚过得混乱无比。苏以真记不清自己到底喝了多少酒。一杯接一杯,没停过。眼前人影晃动,有劝酒的,唱歌的,还有说黄段子的。嘈杂得一塌糊涂。后来,也不晓得过了多久,有人扶起她往外走。她眼前发黑,脚下软绵绵的,像踩在棉花上。没有一丁点力气,整个身子都靠着这人。迷糊中,听见旁边一人问:
“刘言,你一个人行不行啊?”
苏以真听了哈哈大笑,手指一下下地点着那人的鼻子,“流言,怎么叫这个名——”话没说完,便被这人架着往外走。到了外面,风一吹,苏以真“啊”的一声,张口便吐个唏里哗啦。这人“哎哟”一声,“怎么说吐就吐——”手依然是牢牢地扶住她。一会儿,又给她披上外套。轻轻把她垂到面前的刘海往后捋去。
“好了好了,吐出来就好了——”一双手在苏以真背上拍了拍。隔着衣服,还能感到几分暖意。苏以真没来由的一阵心酸,眼泪不觉便流了出来。“难受是吧,一会儿就好了——”他哄小孩的口气。苏以真想说“谢谢”,嘴巴张了半天,却一个字也发不出来。这人叫了辆出租车,问她:
“你家住哪儿?”
苏以真比划了半天,好不容易把地址说清了。司机回头关照那人:
“哎,别让她吐,我刚换的车垫。”
苏以真倚着车窗。人感觉好些了。脑子也清醒了些。她朝那人看去——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男人,留着李小龙似的头发,圆脸,两颊有好多青春痘。很深的双眼皮。
“谢谢啊——”苏以真大着舌头,“呃,我朋友呢?就那个穿花裙子的女人。”
“醉的比你还厉害呢——放心,有人送她回去。”
“谁啊?可不可靠的?”她问。
年轻男人笑笑,“不错啊,喝醉了还这么忧国忧民——放心,绝对可靠,比我还可靠。”
苏以真嗯了一声,想这人挺有意思。一会儿到了家,男人扶她下车,问,“一个人上楼没问题吧?”她使劲点头。男人又跑到门卫那儿打招呼:
“这女的喝醉了,麻烦关照一下——这个,我不方便上去。谢谢啊。”
苏以真摇摇晃晃地走上台阶,朝他挥手,“走吧,再见。”
回到家,倒头便睡。睡得昏天黑地。次日早上醒来,瞥见身上的外套,一愣,忘记还给人家了。平生第一次喝醉酒,还当着陌生人的面,实在是狼狈。苏以真回忆了半天,隐约记得那人叫“流言”,好像在会计事务所里工作。把包里乱七八糟的名片翻了个遍,都没找到这人。只得给钱文薏打电话。钱文薏也说不认识。“我帮你问问,肯定有人知道。”
干洗好的外套挂在衣架上。苏以真懊悔得要命。人家还是个小阿弟呢。真是有些不成体统了。又觉得自己傻到了极点。那晚杜原早就走了,根本看不见她一反常态的疯样。就算见了,也不会有一丁点的怜惜。她是个彻头彻尾的傻子。钱文薏说得没错。从大二起到现在,整整七年,两千多个日夜,她把那三个字藏在舌头底下,小心翼翼地,加了盖、上了锁。好东西放久了会变成垃圾,好话也是如此,过了保鲜期,就烂在嘴里了。说出来就是一团浊气,夹杂着陈年的腐味。只好没头没脑地咽下去,烂在肚子里。难受是难受,但好在别人并不知情,总算是少了些难堪。
公司附近新开了家川菜馆。同事们说要尝鲜,午饭便订了这家的工作套餐。苏以真不吃辣,照例是去马路对面的日本料理。秋刀鱼、茶碗蒸、味噌汤。味道谈不上十分好,但原料新鲜,服务也不错。吃完慢慢踱到公司,电梯来了,她走进去,正要关门,忽的一只手从外面扶住了电梯门。随即一个男人挤了进来。
“不好意思哦——”
苏以真转过身,对着镜子整理头发。见那人戴顶棒球帽,手里拎着几个饭盒,衣服背后印着“××川菜馆”,牛仔裤洗得发白,都破出洞了。电梯快到的时候,这人一回头,忽的瞥见镜子里的苏以真。两人目光相对,都是一怔。
李小龙似的发型,满脸青春痘。这人赫然便是那晚的年轻男人。
苏以真惊讶极了,“咦,你怎么——”总算是反应快,生生地把后面半截话缩了回去。这副模样,自然是来送外卖。衣服上都印着LOGO呢。他不可能在会计事务所上班。那天晚上是胡诌。怪不得找不到他的名片。苏以真没有让错愕在脸上停留太久,很快露出微笑,“你好呀,真巧。”
男人也说了声“你好”,换个手拿饭盒。有些尴尬。
“你的外套还在我那儿呢。总算找到你了——你在这家饭馆上班对不对?明天我把衣服拿过来给你。”苏以真客气地向他道谢,“那天晚上真是麻烦你了,很不好意思的。”
电梯门打开,两人一前一后地走进办公室。男人放下饭盒,收了钱,临走时朝苏以真瞥了一眼。苏以真坐在靠窗的位置,埋着头,很认真地看报纸。小小年纪就不学好,泡吧也就算了,还豁胖充大。苏以真挺看不惯他。等他走出去,又想,人家到底帮过自己,豁胖不豁胖,是人家的自由。便有些后悔,该表现得热情些才是。失礼了。见一帮同事在一旁吃得津津有味,直说这家店味道不错,又实惠,明天还订他家的。苏以真一想也好,明天又能见到他。也省得亲自把外套送过去了。
年轻男人叫刘言。是川菜馆的小工,青浦人。连着几天,办公室都订川菜馆的午餐。大家很快便与他混熟了,开口闭口“小阿弟”,还撺掇他去问老板要打折卡。他真的要来了一张,堂吃八折,外卖打九折,说一次性满两百元也可以打八折。大家算来算去,两百元实在是凑不满,便建议苏以真也订他家的,多一个人就差不多了。苏以真不肯,说吃辣过敏。
刘言一旁听了,忽道:“我们家的川菜保证不过敏。”
苏以真好笑:“你怎么晓得?要是过敏了,怎么办?”
“要是过敏了,”他道,“这顿饭我来买单——不光你那份,大家的都我来买单。”
大家跟着起哄,说小阿弟为了拉生意,豁出去了。老板请了这样的伙计真是有福气。又说苏以真再不吃就不够朋友了。刘言一本正经地朝苏以真看,很有信心的模样。苏以真想这人真是多管闲事,吃不吃辣与他什么相干了。转念又想,若不是多管闲事,那晚也不会送她回家,素昧平生叨扰人家。说到底还是个热心人。心一软,“好吧好吧,吃就吃。”
第二天午餐送来。水煮鱼、铁板牛肉、手撕包菜、酸辣汤。刘言单独替苏以真包了一份,菜和汤分开,配了湿纸巾和水果,很干净的样子。“做你生意不容易,给你搞点特殊化。”刘言说这话时,并不看她,而是朝着旁边,漫不经心似的。苏以真嘿的一声,心里竟不自禁地暖了暖。
水煮鱼红艳艳的,色泽很好。她挟了筷放进嘴里,顿时便朝刘言看去。刘言问,好吃吧?她不答,又挟了筷牛肉。吃一口,朝他看一眼。刘言说,专心些,才品得出味道。
大家问她感觉如何。她道,谁晓得呢,就算过敏也不会这么快。快下班时,收到一条短信:“没过敏吧?刘言。”她奇怪他怎么会晓得自己的手机号码。再一想,那晚应该给过他名片。想不理会,又觉得不好,隔了半晌,回了条:
“忘记告诉你了,我吃番茄酱也会过敏。”
第二天,刘言送午餐过来时,依然给她单独装一份。
趁别人不注意,她问他,为什么要拿蕃茄酱冒充辣油,“不怕我说出来吗?”刘言说不会。“你一看就不是那种咋咋乎乎的女人——再说了,与其吃那种小日本的淡不拉叽的东西,还不如吃我们的。生鱼片哪有水煮鱼好吃啊。你实惠了,我们也实惠。这叫两全其美。”
他说川菜馆是他一个远亲开的,请了个正宗的川菜师傅,几十年的老手艺,比“俏江南”、“川国演义”还要好。他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索性不读了,在外面打零工。洗过碗、搬过砖,发过传单,还给死人化过妆。“不是人人都能穿西装戴领带在办公室吹冷气,我没那个命,拿家里的钱去读个夜大什么的,没意思,还不如早点出来干活。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他说话时,语气透着些许不羁。说完还吹了记口哨。
苏以真朝他看。心想这人年纪轻轻,想法倒挺成熟。
“你几岁,”她逗他,“是九零后吧?”
“比九零后大三岁,跟你一样,都是八零后。”他道。
苏以真嘿的一声,瞥见他脸上密密麻麻的青春痘,想,小朋友一个,还吃大姐豆腐。“八零后也分好几代呢。你穿开裆裤的时候,姐姐我已经在学校里当升旗手了。”
“在我们学校,都是读书最差的学生当升旗手。” 他故意气她。
她哧的一声,问他:“那晚为什么说谎——明明在川菜馆上班,干嘛说在会计事务所?”
他道,“不是我说谎,是一个朋友替我吹的牛,说反正是来凑数的,将来也不会见面,就算吹自己是副市长也没关系。谁认识谁啊。”
苏以真又问:“那干嘛送我回家?谁认识谁啊。”
“你以为我想啊——谁让你坐的离我最近?旁边几个男的都醉得不成样子了,我要是不送你,你肯定在酒吧待上一通宵,上海治安又没那么好——总之是看不下去,心想就做一记好人吧,好心有好报。”
苏以真笑笑。“这话对,否则我也不会订你家的午饭——我没骗你,我是真的不能吃辣,以前有一次跟同学去吃香辣蟹,结果大腿肿得跟猪腿似的,在医院吊了一夜盐水。”
“啊?”他很惊讶。
“所以啊——我是冒着生命危险,订你家的川菜。”苏以真笑。
后来,苏以真每次想起这层,便觉得诧异——又何必理会他呢,照旧吃自己的日本料理不是挺好?清爽又健康。没来由地给他一激,竟真的订起了川菜——虽说是番茄酱版的川菜,但总归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多了人家的功夫,也添了自己的麻烦。搞得每次吃饭都跟做贼似的,生怕被同事察觉,远看是没啥,走近了一眼便能看出端睨,明明红得吓人,却是一股甜香,辣椒籽也没半颗。再说又是单独包装。有多嘴的同事已经嘀咕了,“怎么天天开小灶——”
她把这层顾虑跟他一说,他脑筋转得倒快,送餐的时候,给她一小包辣油打开放在旁边,“这样别人就闻不出来了——”她不便说,其实不光是这个,总觉得哪里不妥。有些那个了。讲不清。她好奇他是怎么把番茄酱放进菜里的,又不是掌勺的师傅,怎么做的手脚。味道倒也不难吃。川菜做成淮扬菜,是另一种风格。应该费了不少心思。再说了,他不嫌麻烦么,赚的钱又不是他的。
苏以真想,还是吃回日本料理算了。可一来同事那边不好交待,二来总觉得欠了刘言的情,那天晚上送她回家是一桩,天天往菜里加番茄酱又是一桩。苏以真觉得自己做事拖泥带水已经到了一种境界了。七年都不敢对杜原表白,现在连订个工作午餐也是牵丝绊藤。
星期五那天,换了个女孩送外卖。女孩说刘言家里有事,请了假。没有小灶,苏以真头一次吃起了大锅饭。同事们开她玩笑——小阿弟一请假,大阿姐待遇就直线下降了。苏以真被正版水煮鱼辣得舌头发麻,索性也不辩解,笑咪咪地由大家说去。一副身正不怕影子斜的态势。
下午接到刘言的电话,第一句话便是“没过敏吧?”
苏以真吓他:“脸上都起红疹了。”
“啊!?”他紧张起来,“要不要紧——真是对不起,我今天有点事,忘记关照他们了——你怎么还在上班啊,快去医院看看,免得又要吊盐水——”
“请病假要扣工资的,”她道,“我这月公休全用掉了。”
“那也要去医院啊,你这个人真是——中午吃份日本料理就要花掉六、七十块钱的人,还计较这些小钞票,你是不是脑子不好使啊,”他居然骂起她来,“快去请假,就算不去医院,回家睡一觉也好啊。黄梅天,正常人也觉得皮肤发痒呢,更何况你这种容易过敏的——”
苏以真挂掉电话,便有些后悔。好端端的去招惹人家。听他的语气,应该是真的急了。拿过手机,在屏幕上打道:“我挺好的,跟你开玩笑呢”,想想不妥,又删了。心里觉得挺不好意思,一把年纪了还寻小弟弟开心。
一会儿,收到刘言的短信:去医院了吗?她回道:去了,在排队。
下班出来,远远的瞥见刘言站在门口,双手抱胸,一副似笑非笑的表情。苏以真吃了一惊,脸都有些红了。几个同事走过,跟他打招呼。她便也没事人似的,上前道了声“你好”。转身便走。他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到了路口。她停下来,回头朝他笑。
“不好意思哦。”她觉得自己像个做错事的小孩。
“红疹消得蛮快嘛。”他走到她面前,“一点印子也不留。”
“开个玩笑,别生气。”她道。
“有啥好气的,”他嘿的一声,把手插进裤袋,耸着肩膀对她笑,“我良心没那么坏——我宁可被你骗,也不希望你真的皮肤过敏。”
苏以真听了,忍不住朝他看去。见他也在看她。忙把目光移开。那一瞬,心头好像被什么轻轻拨了一下。都听到“吧嗒”一声了。忙不迭地转过身,继续往前走。
他跟上两步,走在她前面。两人一前一后地走着。他一米七出头,而她是一米六九,穿上高跟鞋还比他还高了半个头。好在他肩膀宽,走路胸挺得很直,看着还不算太矮。况且她也不是那种高高瘦瘦的竹竿身材,所以落差并不十分大。苏以真想,要命,居然研究起这些来了。
她对他说,还是不习惯川菜,“也省得天天麻烦你了。我照旧吃我的日本料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