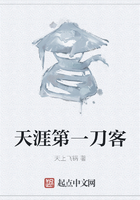一早,暗白的天光映入珍芙宫寝殿的霞影纱窗,不等到早朝的时辰,拓跋晗便已经睁开眼睛,无声地从床上坐起,活像是悄然获取美色急于逃走的采花大盗,手忙脚乱地穿靴,洁白的寝衣照在壮美的身体上,却找不到自己的龙袍。
他找了找床下,又看了看床上,却崩溃地发现,他尊贵无匹的龙袍不但被叠成了一个“小枕头”,还被仍在酣睡的严薇舒舒服服地枕在了螓首下。
这女人实在过分,昨儿死抱着他不放,还敢枕着他的龙袍睡觉?!
他握了握拳头,眼睛却贪恋着她的睡容,咬牙切齿地天人交战——算她狠!不过,他堂堂一国之君,总不能穿着寝衣去上朝,而且他实在不想惊动太监送了朝服到珍芙宫来。
他凑上前,轻轻地抬起严薇的头,把黑色的龙袍抽出来,又轻轻移了枕头在她的颈下……
失败的是,龙袍成功取走,他的手臂却被严薇习惯性的翻身抱住,绝美的睡容娇憨甜美,口中还呓语唤着他的名字,“晗……”
汉哀帝为董贤断袖,难道他要为美人断臂?!
心头掠过这个想法,他温柔的眸光又变得清冷,不禁恨透了自己。她是杀了母后和师父的凶手呀,为何他对她的爱恋却仍是未曾减少一分?
他无奈地抽了抽手臂,没有抽动,而且手臂正碰到她胸前敏感的柔软,反惹得她娇媚地动了一下,越是往他近前移动。
若在平时,他一定毫不犹豫地躺回去把她吻醒,可现在……
他注意到她手臂上用白色布条包扎的伤,眸光顿时一暗,难怪她最近总是穿着袍子,就算两人亲热,她也绝不会露出手臂。
就在他要碰到她的伤口时,严薇已经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晗,怎么醒这么早?要去早朝了吗?”注意到他的眼神,她怔了一下,忙松开他的手臂,拉住被子遮挡起手臂上的伤口,“你……你快去上朝吧,别误了时辰。”
这个伤口倒是让他不再觉得尴尬,心底的关切没来由地涌上来,他强硬握住她的手臂,拆开布条,看到没有结痂的伤口。
看样子已经有多日,伤口极深,从伤口周围残留的药渣可以看出她对自己的身体有多草率。
“这伤该不会是你刺杀师父时留下的吧?很像是师父用冰锥伤人之后造成的……”不,如果她中了冰锥,这整条手臂早就废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告诉我!”
“你捏疼我了。”
“为什么不回答?你还想回夙清宫里呆着吗?”
回夙清宫?这么说,昨日是她曲解了他的关心?他一次次地要她,歇斯底里地纵情,在她耳边呢喃着与以前并无差别的连绵情话,并非已经打消了对她的怀疑?
满身吻痕成了莫大的讽刺,一夜欢愉带来的悸动还残存体内,凌迟了她的自尊。
她强忍着泪,揪紧胸前的被子,“你何时杀我?”
杀?她就这么巴不得死?巴不得离开他?“好好在这儿呆着,别妄想逃走。”
他穿上龙袍,头也不回地出了宫殿。
早朝,坐在龙椅上,他满脑子都是她手臂上的伤,她竟带着那样深重的伤口整天跑得不见踪影?
她平日总怕痛,哪怕一点点划伤都忍不了。就算她非要杀母后,非要杀师父,她也可以找他发泄,打他,骂他,杀了他都可以,为什么她要做傻事?
“陛下,太后母仪天下,又是陛下的生母,太后薨,举国哀悼,请陛下务必严惩皇后!天山老人是陛下的恩师,陛下更不能罔顾师徒情分,让皇后逍遥法外!”
拓跋晗这才注意到,众臣已经对这件事议论了许久,若非他们齐声高呼,他也不知自己还要坐在龙椅上发呆到几时。
严惩凶手?他要如何严惩凶手?要他把他五个孩子的娘亲斩首示众?让他亲手杀了自己心爱的女人?
他们真是大义凛然,一张张老脸上都是志得意满,仿佛杀了严薇就是他们此生最大的梦想。
见他沉默,与几个王爷一起立在阶下的拓跋远鸿突然开口,冷斥众臣,“诸位大人,你们这是做什么?事情还没有查清楚,你们怎么能断定皇后就是凶手?”
“大街上早已沸沸扬扬地传开了,王爷就不必再替陛下隐瞒了,我们也已经知晓陛下就将皇后娘娘关在珍芙宫内……”说这话的正是阮立言。
他的话还没有出口,就被拓跋晗怒斥,“阮爱卿,你怎么对朕的一举一动如此清楚?”
皇宫大内,至尊举动,岂是他一个臣子能窥伺的?纵然他是元老,在朝野上下能呼风唤雨,也容不得他如此放肆!
阮立言自知说得过了头,慌忙跪下,“陛下息怒,老臣并无逾矩,只是……只是听说。”
“听说?原来阮大人是单凭片面之词帮朕定夺天下大事的?!”
“陛下,臣不是这个意思……”阮立言只觉得有口难言。
拓跋晗无声冷笑,“这么说,你不是听说,你们口口声声说皇后是凶手,在皇后杀太后时,阮爱卿大概就从旁看着呢!你们个个都知道天山老人天下无敌,武功更在皇后之上。难道阮爱卿亲眼目睹了皇后刺杀天山老人,还从旁协助?”
“这……老臣冤枉!”
“你冤枉?皇后就不冤枉?”
“可……这……”阮立言疑惑看向拓跋远鸿,却又无法把自己获悉整件事的始末说出来。不过,拓跋远鸿明明已经抓了辛文将军的贴身侍从严刑拷打,证明了皇后就是凶手呀。
“谁能说出个所以然,朕马上把皇后带过来质问。”
大殿内一片死寂,众臣都交头接耳,拓跋晗紧握着拳头,愤恨冷视着他们。
阮立言不甘心的把视线转向静默不语的辛文,“辛文将军,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老臣想听你一句实在话,太后与天山老人,是不是皇后所杀?老臣希望你对先帝的在天之灵发誓,你说得每一句话都一定是实话。”
辛文腮骨动了两下,看了眼拓跋晗,又面对阮立言,迟迟无法开口。
他若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严薇是凶手,这辈子他就再也别想见素纹了,素纹定会憎恨他一辈子。
“末将……”
“没想到,朝堂之上竟也如此境况?阮老头儿,你是看晗儿年轻好欺负?还是看辛文将军为人忠厚蓄意欺压?”
拓跋晗听到这浑厚苍老的声音,不可置信地看向殿门口。
初升的朝阳映入大殿,自后打在入殿来的白衣白发的老者身上,他眉毛胡子全白的脸掩在阴影里,叫人无法分辨他的神情,但他威严狂冷仙风道骨的气韵却已震慑整个大殿。
众人皆朝他看过去,面容惊愕,如见了恶鬼来索命。拓跋远鸿双腿摇晃了一下,险些踉跄跌倒。
天山老人身后,还有一个挺拔俊朗的墨青身影,正是其嫡传大弟子莫卿贤。
拓跋晗忙从龙椅上起身,疾步迎下来,“徒儿不知师父回宫,未曾远迎,还请师父见谅。”
“你就是这样当皇帝的吗?别人口出恶言诅咒你的师父母后驾鹤西去,你竟然还能稳坐在那把硬邦邦的龙椅上?”天山老人怒不可遏,“若非你的皇后严薇先一步通知老夫,有人预谋刺杀老夫,老夫恐怕也没命在此训斥你了。”
“薇儿通知了师父?”
莫卿贤解释道,“皇后并不知师父的行踪,命人把消息传给了我,又让我去寻师父。”
拓跋晗顿觉心口钝痛,仿佛被狠狠地刺了一刀,既然师父活着,母后也定然活着。
他怎么会如此混账,竟怀疑薇儿会对师父和母后下毒手?
“辛文,记下所有在早朝上跪求严惩皇后的人,罚俸三年!”
“遵旨。”
“阮立言身为朝廷重臣,信口雌黄,多次以下犯上,罪无可恕,朕本念其劳苦功高,多次忍让,可他不但不知悔改,反变本加厉,朕无法再容其恶行。”说着,他佯装无意地冷瞥了眼拓跋远鸿,又对阮立言说道,“阮爱卿,朕不想再见到你,你若还想为自己多留点颜面,就返乡养老吧!”
大殿尽头的高阶下,传来阮立言经典绝伦、夹杂着三分感恩的哭腔,“谢主隆恩!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退朝!”
拓跋晗匆匆说完,直奔珍芙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