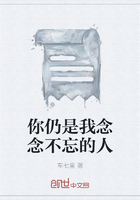黄仁宇原计划的课题包括整个明朝,上自洪武永乐下迄天启崇祯,注意由盛而衰的原因,也注重税收演变过程中,以征银代替实物的影响。但费正清先生严格指出,那样牵涉的东西过多,内容必然会泛滥无际。经过黄仁宇的一再辩论,最后才折衷地将时间定在16世纪。
黄仁宇写的第一章可谓一帆风顺。费正清先生看了稿本后说,“你写得很好,既正确又明了。”可是另一方面,他也提出历史研究的重点是在于“分析”而不是“描写”。这一点埋下了两人日后关系隔膜的种子。到第二章写完时,两人的观点发生严重冲突,费正清先生甚至说,“我已经用尽了所能‘给你的’劝告了。”
8月份,黄仁宇开始陷入生活的危机中。纽普兹大学听说他得到研究经费,“不久即有专书在哈佛大学出版”,已提议给他升为正教授,而东亚研究所提供的1万元经费已用去一半,9个月的时间也已耗掉二分之一,但拟定的稿子仍然没有头绪。同时,他在哈佛所租的房子已经到期,学校即将开学,再租下去就会很贵。于是,征得费正清先生的同意,黄仁宇用一半的时间在纽普兹,一半时间在哈佛,继续他的研究。
1970年的秋季和冬季,黄仁宇夜以继日,平均每天工作12小时,每周7天,除了来去剑桥之外,毫无间断。《16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全文交稿后,他写信给费正清先生说,如果哈佛东亚研究所对文稿有疑问,他可以在接到通知后的24小时内来剑桥当面答复。
由于得不到任何音讯,1971年夏季,黄仁宇将复本寄给英国剑桥大学的崔瑞德教授,问他是否可以询问在剑桥出版的可能性。崔教授表示,“虽说我不能替剑桥大学出版社发言,可是我想你把引用书目和注释整个寄来,他们会高兴接受的。”不料,这时费正清先生回信表示对文稿仍感兴趣,说哈佛至少可以抽出文稿中的一部分出版,或者题为《明代财政论文集》。但黄仁宇认为,他无法对文稿进行分割,所以拒绝了费正清先生的建议。最后,《16世纪明代之财政与税收》一书,于1974年底在英国出版。
荣誉与耻辱
早在1967年7月,黄仁宇就接到李约瑟博士邀请他参加《中国科学与文明》课题的计划。当时黄仁宇新婚未满一年,儿子杰夫也只有两星期大。李约瑟的信装在不起眼的信封内,没有注明寄信人的地址,凯思学院淡红色的邮戳也不明显,乍看之下还以为是广告信函,但等看到第二页寄信人的签名时,黄仁宇非常兴奋,不禁大声对妻子说:“有人邀请我们去剑桥!”
“现在?”格尔问。
“不是,是三五年后。”
在这封信中,英国皇家学院院士、英国学士院院士、凯思学院院长李约瑟博士说,在今后的几年中,自己会从事《中国科学与文明》最后一卷的工作,他问:“在进行最后一卷时,不知你有无可能来这里加入合作?”
黄仁宇当然很高兴有这个机会,也很乐意成为被考察的对象。在以后的几年中,双方保持着密切的通信联系,对于彼此的学术观点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1972年8月,黄仁宇携夫人和孩子抵达剑桥。考虑到计划合作一年,黄仁宇担心找不到愿意提供财政资助的机构,所以用措辞略微不同的两份申请书,分别送到华盛顿的全美学术团体联谊会和国家科学基金会。为了将申请金额降到最低限度,他自动删除了在英国的额外花费,只申请相当于薪水的数目。在申请书中,黄仁宇还说,他和家人的来回机票将由李约瑟博士的研究基金来支付,但事实上是他自己掏的腰包。不过,后来黄仁宇发现,他的胆怯毫无必要,两个机构都全数批准了他的申请,以致于他还必须通知国家科学基金会,将重复的部分删除。
与李约瑟博士的合作相当愉快,并成为黄仁宇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他说,“能亲近如此杰出的人物,真是一项殊荣。”这一年,他与李约瑟博士、李约瑟博士的助手鲁桂珍博士讨论学术问题的照片,被刊登在影响很大的《观察家》杂志封面,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纽普兹大学的校长还特意写信给李约瑟博士,说自己的教员能在海外参与如此重大的研究计划,实在是荣幸之至。
经过认真的讨论和研究之后,黄仁宇写出了200多页的草稿,准备放入《中国科学与文明》第四十八节。他又从其中摘出1万字的文章,由两人共同署名发表,刊登在香港、罗马和旧金山的期刊上。
黄仁宇在英国呆了363天,差2天满一年。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在回美国前,黄仁宇决定加入美国国籍。但如果在剑桥呆一年,则会破坏在美国居住的连续性,必须从头开始算,住满5年后才能再次提出申请。因此黄仁宇向美国环球航空公司订票时,特意预留了48小时的时间,以备班机延误时有缓冲的时间,不致于破坏申请计划。
回到美国后,黄仁宇的学术影响进一步扩大,他曾受邀到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瓦萨学院及麻省理工学院演讲,还曾获得密歇根大学和古根汉基金会的研究资助。1979年春,他已经在纽普兹大学连续任教10年,也就是说,成为一般意义上的“终身”教职,同时,他还获得了参加在普林斯顿《剑桥中国史》明代部分撰写工作的莫大荣誉。
但就在这时,他被纽普兹大学解聘了。
解聘发生在1979年3月27日。这一天,他接到校长室的电话,由校长考夫曼及教务副校长、文理学院院长通知他:“我们有不好的消息……”解聘于第二年8月31日生效,当时黄仁宇刚刚过完62岁的生日。
当时,黄仁宇是纽普兹大学惟一教授中国历史和日本历史的老师。和他同期被解聘的还包括教授拉丁美洲历史、俄罗斯历史和中东历史的教师。而教授非洲史、印度史以及另一位教日本史的老师,则在1976年就被解聘了。留在纽普兹大学的,是13位全职的历史系教师,全都是教美国史、加拿大史和西欧史的。他们之中当然也有值得尊敬的学者,但也有人一直叫嚣:“我们独特的西方文明!”所以黄仁宇觉得,自己的被解聘,实际上是出自于政治阴谋。
不管怎么说,被解聘一事,对黄仁宇的身心都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他说,“这个事实会永远削弱我的尊严。”有人主张黄仁宇应该忘掉这件事,全身心地投入到创作中去,但黄仁宇却认为,说这话的人从来不曾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考虑,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忘记这样的事。他觉得无论走到哪里,似乎都被贴着不名誉的标签。很多人试着帮黄仁宇,想为他重新找到一份工作,但没有人会雇用一个刚被解聘的60多岁的老人。
他们到当地的社会福利局去咨询,数周后接到通知,说如果是在62岁退休,每月可以领到400美元的社会福利金,加上其他收入,共有600美元。但这些加起来也不到他们每月最低生活标准的一半,更不要说还有房租和其他杂项开支了。
黄仁宇也研究过领取失业津贴的可能性,结果得到一张申请表,上面有两栏,询问申请人是否领取了社会福利金和退休金,也就是说,黄仁宇必须等到真正失业时,才能领取失业津贴。与此同时,他还必须定期证明他没有办法找到别的工作,而解聘他的原单位也可以质疑他的申请。黄仁宇把手册一丢,扭头就走了。
格尔曾陪着黄仁宇去找律师,希望能揭穿被解聘背后的政治阴谋。但律师告诉他,必须找同事当证人,结果有3名同事非常愿意替黄仁宇作证,第四位则犹豫不决。深思熟虑后,黄仁宇不得不放弃了打官司的念头。
从此,黄仁宇再也没有过其他固定的工作,写作成为他获取收入的惟一来源。
在失掉工作的同时,黄仁宇的代表作《万历十五年》在出版方面也遇到了困难。这本书的英文名字是《1587年,无关紧要的一年》,他曾将此书影印发给《剑桥中国史》的作者群。著名学者牟复礼逐字看过两次原稿,甚至替黄仁宇改正注释中的错误。他还说,“这本书愈早出版愈好”,又说,“我非常遗憾学生在今年秋季看不到这本书。”好友崔瑞德也努力帮黄仁宇在英国找出版社。不过,英国的出版商并不热心,因为他们要求与美国的书商共同出版,不愿独自担风险,但由于在美国找不到愿意合作的出版商,英国的书商也就不轻易松口。
黄仁宇亲自跑过三个出版社,每次也都是被退回。商业性的书商认为,这本书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应该交由大学的出版社出版;而大学的出版社则认为,这本书太过于通俗,应该交由商业性的出版社出版。
应该说,根据牟复礼和崔瑞德两人在学术界的地位与影响,《万历十五年》的学术性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当这份书稿获得了该领域最称职学者的强力推荐的时候,为什么却始终得不到学术出版社的认同呢?原来,依美国出版界的惯例,有学术内容的著作,必须经由不署名的审稿人进行公正的评价。审稿人不只是建议该不该出版,而且一旦决定出版,还必须提出改进的建议。而牟复礼和崔瑞德对书稿赞誉有加,无意间就排除了自己成为公正审稿人的资格。同时,《万历十五年》的稿子也不是以学术论文的传统形式写成,而当时的审稿人又无法从论文的规范模式中解脱出来,因此极力反对这种通俗的写法。
黄仁宇也做了两手准备。由于无法以英文出版,所以他努力工作,迅速将其译成中文。1978年夏天,他的一位朋友余哈维前往中国,黄仁宇就托他设法帮忙在中国找出版社。
认识余哈维,也算是一种机缘。早在40多年前的1937年,当黄仁宇还是长沙临大的学生时,他们就住在同一栋宿舍,但彼此并不认识。1946年,他们都在沈阳的国民党东北总部,还是不认识。只是等黄仁宇到了纽普兹,才通过朋友的介绍相识了,从此两家经常往来。
当年秋天,余哈维回到美国,打电话告诉黄仁宇,说该书的出版前景相当“看好”,因为他的妹夫黄苗子(作家和艺术家),愿意将书稿推荐到北京的出版社。黄苗子还曾拜访过黄仁宇以前的好友廖沫沙,请他写中文版的序,当时廖沫沙正在北京朝阳医院养病,廖沫沙表示很乐意。由于廖沫沙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特殊地位,如果借用他的名字,相信这本书在中国大陆出版,应该问题不大。另外,由于当时的中国尚未完全从“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中走出来,所以这个消息也让黄仁宇极为兴奋。
到10月份,余哈维催促黄仁宇将书稿再邮寄一份给黄苗子。信虽然寄到了,但这本超过5斤重的手稿,却不知去向。1979年1月,黄苗子建议黄仁宇再寄一份过去。不过,这次黄仁宇选择了让人亲自带过去的办法。这个人名叫卡尔·华特,是余哈维的女婿。
华特把书稿亲自交给黄苗子,经过黄苗子的热心推荐,被中国最大的历史书籍出版社中华书局看中,同意出版。不过,碰巧的是,华特将这个消息告诉黄仁宇的那天,正好是1979年3月27日,也就是黄仁宇得知自己将要被解聘的时候,所以黄仁宇对于这个“好消息”表现得极为冷淡,让华特感到非常委屈。
几经周折,于1980年,中国大陆的中华书局终于将历经苦难的《万历十五年》一书出版,廖沫沙在序言中也对该书做了高度评价。此书一炮打响,立即成为当时学术界最畅销的图书,人们纷纷从内容、理论及写作方法等等多方面对该书进行探讨,一场“万历十五年热”席卷大陆。
苦尽甘来,《万历十五年》的英文版在美国出版后,也迅速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好评,该书还曾获得美国书卷奖1982年和1983年两次提名。此后,中国台北的中文繁体版、德文、法文和日文版也相继问世。
尾声
此后,黄仁宇周游世界,多次往返于大陆和台湾等地,并孜孜不倦地撰写有关历史论文和随笔,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大部分著作,如《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天南地北叙古今》、《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等等重要著作,都是这时的产物。藉着《万历十五年》的成功,黄仁宇的系列专著,也纷纷在大陆和台湾出版。他作为著名中国史学家和海外著名汉学家的地位,在读者和学者中间,逐渐确立。
2000年元月8日,黄仁宇走完了传奇般的一生,于纽普兹的家中去世,享年83岁。同年11月20日,陪伴他近半个世纪的妻子格尔女士也随他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