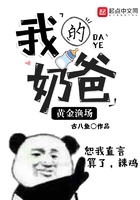申夫人茫茫然瘫坐在地,怔怔望着太后,口中喃喃道:“求太后开恩,求太后开恩!”
“阿萝啊阿萝,自从你救过哀家的命以来,你从来没有求过一件事情,这一件,恕哀家不能答应。豹儿是哀家侄儿,是大哥唯一的血脉,哀家心中伤痛,不亚于你。”太后缓缓睁开双眼,目内露出精光,“谋杀太后而能苟存性命,此例一开,日后多少刀剑向宫内飞来!莫说太后皇后,就是皇上也一刀杀了!”
太后所言,于理于法,无可挑剔。
可是,那个是豹儿,她辛辛苦苦养了十七年的豹儿啊!叫申夫人如何舍得!
她咬咬牙,举起握了许久的金牌,道:“太后娘娘,先帝免死金牌在此,奴婢斗胆,求饶了豹儿这一遭!”
太后纹丝不动,恍若未闻。
佛堂内寂静无声。
忽然,连绵不断的雷声轰隆隆从屋顶滚过,雨声沙沙地落在瓦面上。
刺目的闪电,照见了太后神像般凝重的脸。
“太后娘娘,先帝免死金牌,只是一场笑话吗?”申夫人问,她的声音已经完全颤抖成一条细细的线,似乎随时可断。
“阿萝,先帝有言在先,赦免的重罪不包括谋反大罪!豹儿灭绝人性,肆意妄为,他向哀家刺出那一刀时,可曾想过哀家是他姑母,是当朝太后?”太后的声音在沙沙雨声中,显得空洞而虚幻。
“太后娘娘--”
“阿萝!”太后猛然打断了她的话语,“国法重于亲情,二十一年,你已经懂得这个道理,当时的你,不是大义灭亲了吗?如今,为什么忘记了?”
怎能忘记?
二十一年前。
刀光剑影,血肉横飞,哀嚎惨叫。
“阿萝,你必遭报应!”养父养母凄厉的诅咒,如绳索,紧紧缠绕着她的心脏,让她喘不过气来。
当时的她,不过是太后身边一名小宫女,镇日洒水扫地。一次外放回家,在水榭台底的一只小船上睡着了,竟听到养父养母在水榭中商量何时发兵杀进宫内,杀太后,废新帝。她自幼与养父养母不谐,饱受虐待,回宫后毫不犹豫将此事汇报给了太后。
养父得知她匆忙离去,觉得事情败露,仓惶起兵,掌控京城。申钺与申铖两兄弟死不投降,率领兵士固守皇宫,哪怕养父杀尽他们申家大小人口五百八十三人,一直浴血奋战,坚持到蓝大将军领兵靖难解围。
养父养母行刑前,仰天大笑,又厉声呼唤她的名字:“阿萝,阿萝,你必遭报应!”
那时候,观刑的她,只是冷笑,觉得深埋心底已久的一股怨气随他们的鲜血冲天而起,无比畅快。神?鬼?如果真有神鬼,为何她幼年时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太后念她大功,将她许配给申钺。
申钺心中只有无辜枉死的妻女,纵然是太后赐婚,也不曾有过半点和颜悦色,常常握着挂在胸前的一只绿花锦囊,整夜无语。
那时候,她曾经感叹,是报应吗?
接二连三都是女儿,她也曾怀疑,真是报应吗?
直到豹儿出生,她觉得对得住申家枉死的五百八十三人,总算对得住申家列祖列宗,总算对得住自己的夫君。
二十一年弹指过,当年宫廷内浓重的血腥味早已经被檀香的味道所代替。
二十一年,不容易。
她望着太后,太后的头发已经几乎全白了。
二十一年,对于太后,也同样不容易--为了唯一的儿子,她使出浑身解数,经过多少腥风血雨,才能够安安稳稳地坐在皇宫内的佛堂拜佛念经。别说侄儿,就算亲大哥,只要威胁到她,也毫不留情吧。
申夫人将那块天下人梦寐以求的金牌用力一抛,远远抛到角落里。她恭恭谨谨再磕了一个头,站起来,脸上已经一片肃然。
“太后娘娘,愿太后娘娘福寿绵延,努力加餐,奴婢阿萝告退。”她低下头,如同二十多年前常做的那样,往门后退去,直到低斜的目光看见门槛,微微提起裙子,退出去,才抬起头。
太后依旧双目微闭,持着念珠,口唇微动,仿佛与一切尘事无关。
雨水打湿了申夫人的头发与衣裙,她毫不在意,只静静立着,坚毅地望着佛堂里面。
守门的宫女不敢做声,也不敢为她递过一把伞。谁都知道,这是当今老宰相的夫人,是太后的亲大嫂,也是谋害太后重犯申豹的娘亲。
“阿萝,你去吧,天牢里,自有人照应。”太后平稳的声音从阴暗的佛堂中传来,“记住,一个半月。”
“谢太后娘娘隆恩!”她跪倒在雨水里。
“阿萝,不要太贪心。留下你们性命,已经是格外开恩。”
是的,她贪心,如果可以一命换一命,她宁可用自己去换回豹儿一个,不,哪怕是加上女儿的命也在所不惜!
只是,如今她的命,价值几何?如何能够抵得过豹儿的如山重罪?连先帝的免死金牌,也不过是一块废铁而已。
申夫人浑身湿漉漉地乘马车回家。
申钺在府门前持着青油布伞,翘首而望,一见马车,立刻快步向前:“阿萝,怎样?怎样?”
他曾亲自前往天牢,问过儿子,儿子亲口承认是他酒醉后掷刀差点刺中太后,他已经知道,儿子的性命无法挽回。
虽然他不许夫人进宫向太后求情,到底心头存了一点点微弱的希望,说不定太后看在申家香火上,留豹儿一条狗命呢。
一见夫人面容惨淡,他再也问不下去了,颤抖着手,将青油布伞往她头上罩去。意料之中的结局,为何是依旧不能承受的沉重?
“太后开恩,许我一个半月,马上派管家他们到乡下去,找四十五个健壮年轻的姑娘!”申夫人厉声说道,身形一晃,晕倒在地。
年过六旬的老宰相,竟来不及伸手去扶住,眼睁睁看着她跌在雨水中。丫头门子们惊叫着,涌上来。
“阿萝!阿萝!”申钺扔下伞,跪倒在地,一脸湿漉漉的,也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
残灯如豆。
细雨敲窗。
老宰相握住妻子凉浸浸的手,坐在床前,不知已经多久。他太困了,不禁打起盹来,忽然觉得手中一动,马上惊醒,道:“阿萝!”
申夫人见到微弱的灯光,大吃一惊,推开被子就要下床:“老爷,我要去天牢!太后开恩,为申家留一点香火!”
“阿萝,你别急,刘管家已经带着姑娘们去了。希望上天保佑,上天保佑。”短短数日,老宰相显得越发苍老了。
申夫人颓然倒回枕上。
相比宰相府内的愁云惨雾,无双王府内又是另一番景象。
申冉冉醒过来,望着迷茫的灯光,慢慢回想起所发生的一切,心头的愤恨与悲哀如浪涌来。
在和夏欣喜地揭开帐子的同一时刻,她敏捷地拔了一支簪子压在脖子上,凛然道:“送我回去!”
簪子尖尖地压着脖子,冰凉而锐利,如她内心深处的疼痛。
他满脸的欣喜凝在脸上,长而浓密的眼睫毛遮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