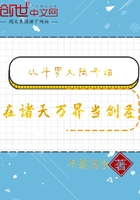尤其是读书人是根本瞧不起商人的,他们自认清高,都认为商人是逐利之徒,铜臭之人,是让人看不起的鄙俗的。
这是当时社会的风气,是很难在短时间内能扭转的,这我们都是知道的,但汪老爷此时是相当的失面子的,因为他是中途弃文经商的,在这些人的眼里就更多了一重罪了。
那个严兄在我们身后长声而笑说:“原来是我忘了,你是上不去的了,真是鄙俗,扰了我们读书人的好兴致,状元楼居然让这样的人都上来了,不就是有俩臭钱嘛,真是污了状元楼的名声。”
此人这话说得极是大声,旁边所有的人都向着我们这一边看过来,我看到汪老爷脸色铁青,只气得身子打颤却说不出一句有力量的话来。
我天性中那种打抱不平的因子在这样的情况下,突然的就冒了出来,我走到那个姓严的面前问:“敢问兄台,你们在这里准备畅谈的是什么诗词呀?”
姓严的知道我与汪永翔是一道的,因此很不屑地对着我一副教训的口气说:“我们今天谈的是观画,你这样的粗人懂吗?”
原来就是看画论诗嗦,我也有几首,我冷笑着说:“在下,这粗人也有一首观画的诗,倒要请兄台指证。”“那就说出来吧,我是最喜欢提携好学的人的了。”这人摆出一副好为人师的样子,骨子里不过还是想借机讪笑我一番借此讥讽汪永翔而已。
我曼声念道:“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那个姓严的当时就呆在那里了,开玩笑王右丞的绝句,量你这酸腐肚里能有多少墨水,未必你还真能予以指证点评吗?
我冷冷地看着他说:“还请兄台,多作指点。”“这、这、”他在这里嗫嚅着涨红了脸说不出话来,汪永翔则是惊喜得话都说不完全了:“秦兄弟,想不到你有这样好的文采。”
有人站在三楼的楼梯上鼓掌,“好一个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真是好诗。”
我抬起头来,看到一张脸,一张温润的脸,我愣住,从来没见过如此象玉的男子,他站在那里穿一身白衣,当真的白衣如雪,谦谦温诺,一脸柔和的笑,如春风扑面,温暖却给人一种有距离的亲和的感觉。
这实在是有些矛盾。
我并不是说他长得有好帅好酷很有气势或压迫感这些,他并没有,他的五官很平常,他的眼没有特别的深遂,他的眉毛没有特别的黑挺,他的鼻梁也不是特别的高耸,只是让人看得顺眼而已。
但他的身上有一种气度,一种包容一切,淡定从容的舒缓,他缓缓地走到我面前站住。他的无侵略性和温和让我感到很舒服,就象大冬天浸在满满一缸子热水里的感觉一样。
听得他说:“小兄弟,好诗,能否请你们一行人上楼品画?”我也喜欢他的声音,温雅而醇厚,象一坛子上好的美酒一样,听在耳里,让耳朵极是受用。
我知道我有些受到了他的嗓音的蛊惑,但理智毕竟还是在起作用中,我知道上楼对于汪永翔来说,是一种殊荣,可是对我而言,不过也就是换个地方吃顿饭而已,现在就我的处境而言,能不引人注意就不应该引人注目,我刚才也是晕了头了,为争一口气管这闲事,看来聪明人也会做傻事是很正常的现象了。
不过清醒得也有些太迟了。
有人在楼上喊:“小兄弟您快请上楼来吧,有你这诗会就更热闹了。”看来听到王维的诗的人不只这么一个两个,现下我也有身份了?“快上去吧,是翰林院的李院士在请你了,这李院士可是七年前的状元公哦。”身边原本呆掉的严姓兄台现下回神了,还必恭必敬地说。
“对,秦兄弟上去吧,这李院士可是咱大槐国最有学问最聪明的人了。”汪老爷也在催促我了,看来这李院士好象是他的偶像似的。
不上去也不行了,只好上楼了,自己种的因自己受结的果吧,无论好坏。
上楼济济一堂的文人墨客,一双一双的眼睛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好象掂量着看我有多少本事似的,这让我浑身的不自在。
我自已知道自己的斤两,当然的我并不是什么文武双修的奇才,我只是有得闲的时候爱看看古诗词而已,那来什么也不得了的文采。
连稍有涉猎都说不上,也不过就是心里记得些名人的诗句而已,当此时刻我的脑海里翻来覆去搜刮着能用来搪塞的句子。
那个如玉似的男子跟在我的身后,这让我觉得心里有了一定的凭恃似的,这个感觉来得太无聊了,今天第一次见面,我就想依靠人家了吗?
但很奇怪的,我就是觉得这人有一些熟悉,这现象让我想起红楼梦里宝玉与黛玉初相见的情形,也就是似曾相识。
我还记得越剧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的歌词上有这么一句:眼前分明外来客,心底却是旧时友。这人有三十一、二岁的样子,前生今世我都没见过他,我很确定。
一个老者上前来对我说:“小兄弟,请留下你的墨宝。”“这可是李院士。”汪永翔在我耳边轻声说,我想他提点我的意思是我应该打点起浑身的精神来对付,于是我将我奇异的心事暂时丢开。
这个李院士个子高高的,人却很清减,留一把半黑半白的长须,浑身上下都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厚醇味道,他的那双眼睛里满是睿智的光芒和对文学的热爱。
我看到他示意的桌旁有文房四宝,连墨汁都是碾好了的,我走上前去提笔蘸墨将刚才我念的诗句写了下来,一边在心里暗暗庆幸,以前写标语和封条的功底还在,没让我丢脸。“请写下名讳。”有人提醒,我落的下款是秦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