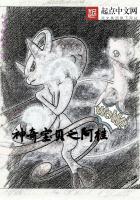段誉对萧峰的友情,带有崇拜的色彩。在段誉眼中,萧峰是类似于天神的人物,所谓“燕赵大汉”,他的雄健豪放,恰是四季如春的大理小国所缺乏的,萧峰的境界,段誉穷其一生,也不能抵达。所以,他们之间的友情,并非惺惺相惜的英雄情怀,而是一种个性对另一种个性的感知与认同。
其实,萧峰是一个不可无酒、不可无朋友的人,极不适合独处。可命运却偏偏夺去他所有朋友,仅留一个有点傻气的段誉。对此,他或许也有几分无奈吧。但他并未因此便轻看段誉,相反,更因这逆境中的萤萤之火,而为段誉孤身犯险,关山飞渡。那时,他的心境应是悲凉与豪气并存的。高山屈于流水,需低头弯腰的俯就,萧峰为全段誉一人之义,已慨然将生命置于对方掌中。
江湖男儿,须以身当剑。中原虎狼岂能阻我前行?燕云十八骑关山飞渡,只为一酬知己。二弟,千山万水我替你背负,你无须回护。前路茫茫,是非对错已成过往。那老者为渡我,甘愿受我一掌。而我乃凡人,参不透这重重禅机。我只知从此后,我萧峰无父无母,只有你!
在契丹国生活的那几年,是萧峰一生最为茫然的时刻。他是天生的领袖,在中原,他爱他的部众,在契丹,他爱他的族人。而这两种爱,绝无并存的可能。那一段坐拥暖帐、一呼百应的日子,萧峰将自己游离于既定的结局之外。其实,那时的他已深知,这两种敌对的爱,必定在某一天将他逼入死地。
萧峰的人格,从那时开始分裂。我们可以想象,酒醒后的他,必然面对苍茫夜空,慨然浩叹。他的心境其实是凄楚的。在汉人的世界,他被放逐,被辜负,被所有人抛弃。而在契丹的土地上,他始终都不能有归属感。汉地中土给了他最基本的人生观、价值观,契丹则是他血肉的赋予者,其时,这两个民族,正处于对峙的战争风云下,萧峰的痛苦与无所适从,无法避免。
杀开的血路,终究荆棘遍野,一路踉跄行来,便是萧峰这等英雄草莽,亦觉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在矛盾最激烈的时候,他被命运逼入不能挽回的境地。这一刻,他感到疲倦。毕竟,孤身一人,独自对抗着宿命的无涯与怆然,对抗着蛮汉两种文化的挤压与逼迫,任你是铁打男儿,亦觉不堪重负。他孤寂桀骜的一生,在此处与他既定的结局再次遇合,这一次,他已回天无力,他到底还是承受了这致命的一击,将这一再偏离的遇合,以完美终结。
我为天下苍生一死,苍生可愿为我一哭?箭簇冰冷,刺我胸膛,我以热血暖它。江湖来去,刀剑风雨,我有些倦了,且容我于此处作别。原谅我,这一生的不羁。若有来世,自当青蓑绿笠,垂钓于世间云水红尘,悠然于茫茫人海。而此生,我只有将生命置于命运掌中。万里风沙之上,任我一世苍茫,我无憾,无怨,亦无悔!
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袁承志
乱世出英雄,也出隐士,袁承志显然属于后者。战乱流年,需要的,是具济世之才的大英雄,而非像袁承志这样的个人英雄主义者,因而,袁承志的一身好拳脚,充其量不过为自己挣些功名,这在袁承志来说是不屑为之的,但除此,他的所学所会,基本无用武之地。
眼见复国无望,而李闯王谓之的太平天国,又着实令人齿冷,这时,袁承志能做的唯一选择,也只有飘然远遁,于海外觅一方浩渺天空,做一个逍逍遥遥的化外之民。
若以成败论英雄,袁承志显然不够成功。爱情上的所托非人,让他最后连面对阿九的勇气都没有;而在事业上,与其父袁崇焕比较,亦相去太远。几十年海外归隐,竟再未踏上中原一步,是惭愧,还是绝望?
所幸,《碧血剑》里,温袁两位看似主角,实则不过是背景,他们的起伏转折唯一的作用,便是从现实的角度,以现实的光彩,辉映死去的金蛇郎君,以及他与即将死去的温仪之间的爱情。从这一点来说,我们也不用为他们抱太多遗憾。
如果袁承志不会武功,并将公子长衫换成几片树叶,与人猿泰山基本无异。生活在人迹罕至的深山,整日与野兽为伍,交往对象除了古怪的师傅,也都是猩猩之流,这样的环境,培养武林高手或许可以,却造不出真正的大英雄。所以,袁一生平平,他的际遇,应与成长的环境有着密切关系,山野生活让他厌恶人际的束缚,而相对狭小的空间,又使他没有高阔的眼界。及至后来,两军交战时,袁跳出战壕,一派匹夫之勇的作为,更令身边家将惋叹,不及乃父多矣。
一代名将袁崇焕之子袁承志,依然矛盾地统一,聪明兼笨拙,被金庸牵着引着,走出了深山,来到了花花绿绿姹紫嫣红的大好中原,而之后,他几乎立刻就犯了一个错误,这种错误是十几年没见过女人的男人通常都会犯的:爱上了他见到的第一个女人。
温青青的不依不饶,袁承志的一再退让,给这段爱情蒙上了一层令人不快的阴影。书中后来出现的女性,除了特别丑的,无一例外地都遭到温的排斥,她不断地使着小性,不断地上演一些哭哭闹闹的小品。真实到了极致,丑陋便裸露无疑,这应是温始终不讨人喜欢的原因了。
好在袁承志师传正派,行为举止深受礼教约束,因此,即便对美丽的阿九公主动了心,也只是发乎情止乎礼,终究还是没能走到一起。最后,他的感情归属,仍旧波澜不惊地专事温青青一女。至于袁与阿九,虽郎情妾意,却一个情归海外,一个意在中原,两处相思,万种闲愁,一段偶遇幻作一朵绚丽的烟花,绽放于回忆的夜空,说起来,倒有些无奈的苍凉与凄清。
少时离家,青年成名,却在成名之后悄然去国,从此绝迹中土,袁承志这一走,可谓决绝。万里之遥的海外,每逢月华如水的夜,他的心里不知做何感想?故国在望,却也只是望一望罢了,终究是不能回去的了。
不过,他还是令人羡慕的。没有了继承父业的束缚与天下大计的重压,娇妻美徒,碧海蓝天,一生逍遥以终老,这是几世才能修来的福气。人生不过如此。
浮生若梦,寂寞沧海
——金庸小说中的绝顶高手
岁月是青衫上的仆仆风尘,经年历久地磨损着曾经的耀眼与辉煌,憔悴了红颜,苍老了英雄,转眼处,已是繁华尽逝。
而浮生,则是捉不牢的飘渺尘灰,宛若惊鸿一梦,梦醒后,留在人们记忆里的,往往是被推至台前盛妆倾情的那些演者,真正统领一代的绝世高手,却总是被掩埋于滚滚红尘中,在世人的薄情下,渐渐淡忘、湮没。
玉女峰顶,思过崖前,风清扬的青袍上,沾染了多少寂寞?十几年山来水往,风晨雨夕,华山派剑术最高的一代豪客,幽居于草木清华之间,独立于岩崖峭壁之上,剑之一道,于此浩浩然无所遁形的寂寞面前,又有何用?
令狐冲终究只是晚辈,虽有个性上的相同,却不能逾越年代上的相异,以及师门中的相悖乃至相斥,在风清扬与令狐冲之间,没有高手对奕的爽利洒脱,只有教与学的投缘机锋,而事实上,并世之间,放眼天下,谁又是他的敌手?他的倦怠与疲惫,是无可奈何地凌驾于江湖,又相忘于江湖。于是,他抬起头,眯起眼看着暌别已久的太阳,说:“日头好暖和啊,可有好久没晒太阳了。”
也许,高手总是寂寞的。孤绝的华山之巅,冥冥冷月下,风清扬袍袖飘拂,瘦削冷峭,这一次,他又将默然远行,行尽于被令狐冲笑傲的江湖里。他的出场与落幕,只在短短一个回目,寥寥几句言语,所谓寂寞如风,来了又去。没有人知道,下次重逢,要过多久,要有怎样的机缘,才能在阳光下,听他轻轻叹一口气……
而独孤求败,这个曾出现在两部书里的剑魔,比之风清扬,似是更加寂寞。《笑傲江湖》中,独孤九剑是剑术;《神雕侠侣》里,玄铁剑后又反璞归真于木剑,则是内力。剑术的张扬不羁,助令狐冲纵横江湖;内力的霸道雄浑,令杨过傲啸中原。不知这两位同名的剑客,是否真是同一人?从年代上考证,仿佛是不同的二人,但从名字及个性上看,似乎又是一体。
一个仅存在于传说中的人物,且知者甚少,在金庸笔下,他便有盖世武功,也只能独自寂寞着,如同绝情谷底的冰潭,忍受岁月风霜的遗忘与冷落。其实,寂寞之于独孤求败,自剑术练成之后,便早已如影随形。后人的敬仰膜拜,世间的淡然忘却,对他而言,恰如过眼云烟,不值一提。而他穷尽后半生所求的,唯一个“败”字而已。若得一败,死而无憾。
可叹江湖之中,举目四望,竟找不出一个对手,可将他败于剑下。沧海明月,青山无语,念天地之大,宇宙之广,唯独孤其人,独孤憔悴。无人对决,武功再高,又如何?
也只能是寂寞了。
然而,也有别样的高手与寂寞。一根银针若一缕相思,绣过滴血丹蔻的春葱十指,无限娇柔地洞穿了童百雄的咽喉。红衣拂动下,一颗在深闺中独守的女子芳心,为所爱,无悔一世,直至血流遍地,倒在众人脚底。能在有生之年,死于高手剑下,东方不败,何其幸运?
日月神教,光耀天地,东方教主,泽倍苍生。可是,东方不败不要这些,他,只要寂寞。
神殿后的秘道,是他寂寞的开始,他要用这寂寞将自己与世隔绝。这寂寞,不同于风清扬的黯淡,不同于独孤求败的惆怅,魔教教主的寂寞,是一朵夜色中的玫瑰,永远只为一个人绽放。
黑木崖一战,可谓惊艳,而金庸也只写了一个回目。数语之间,风起云涌,胜负定夺,东方不败翩若惊鸿,仅仅一个亮相,便已颠倒众生。轰轰烈烈的事业,终究是做给人看的,那不足为外人道的款款情深,才最是揪心。盛名之下,难负的不是武功,而是寂寞,秘道里的爱,也只能深藏于幽深的过往,留待岁月的风沙堆积成一座荒冢,遗忘了曾经的魔教与秘籍。
说到底,这世上,几曾有千秋万代的基业,哪里来千年万世的爱情?唯有寂寞,亘古不变。
华山皓月,南海涛声,绷架上织就的鸳鸯,任你青袍翩飞,红衣着尽,武功盖世又能怎样?独步江湖之后,冠绝武林之际,那些寂寞的高手们,也只有将无人能解的一怀愁绪,盈满胸襟,于千帆过尽的沉舟侧畔,拂一拂衣袖,转过身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