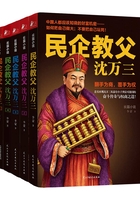梁裁缝出事以后,李兰珍像变了一个人。以前她从街上走过,人们老远就可以听见她“嘎嘎”的笑声,后来她成了一个安静的、有些羞怯的人。
人们偶尔问起她的那根手指,李兰珍就会把那根令人惊骇的手指伸给人看一阵,接着又有些不好意思地把它收回来藏到掌心里去,良久才迟疑地说:“我们裁缝么……”
说这话的时候她的目光就像被打了一样散开来,又空洞又迷茫。
她在孩子身上倒是比以前用心。梁小民在学校打了架,李兰珍关了大门,用竹扫把劈头盖脸地打他,边打边声泪俱下地骂:“我叫你不学好!”她的女儿小蚊很乖巧,虽说还小,但照样可以把一只脚尖绷直了站在窗前踩缝纫机,无师自通地轧鞋垫、补袜子、在棉布裤子上打很方正的补丁。
李兰珍坐在小竹椅上跟街坊们扯白话,人们冷不丁地问到一个老问题:裁缝干嘛承认自己是强奸呢?见李兰珍仿佛受到意外一击似的把头缩进肩膀里,窘惑地拿拳头在膝盖上擦来擦去,小蚊就隔窗一笑,脆生生地说:“糊涂东西,活腻了呗!”神情活脱是以前那个李兰珍——众人于是都笑了。
我外婆找李兰珍扯布做老衣,回来后对街坊说,兰珍这孩子,怕是毁了,三尺布扯出三尺半来,眼神比邓伯还差些。就有人说,兰珍要是机警点,裁缝也不得呷这么老大的亏。还有人说,裁缝这个人,还真是有情义,要不叶红梅怎么过得了这一关?
西街的福娘提起远走高飞的叶红梅,发狠地说:“未必她在大城市里就吃得下、睡得着?”
我家所在的小巷叫御銮巷,巷口有棵高大的泡桐树,我外婆她们说这番话时就坐在泡桐树底下。已是裁缝死后的第n个夏天了,蝉鸣声声、树影斑驳,一如从前。时间就是这样,总是快得超出我们的想象。
有一年春天,雨水特别多,涔水镇在整个三月都浸在濛濛细雨里。我家的后窗就对着涔水河,隔窗就可以看见河对岸大片的农田,还有农田尽头一抹黛青色的山。三月丰沛的雨水给人带来多少欢乐啊!我趴在窗台上,看着河边滩地上铅笔画一般纤细的柳枝在雨中一日日丰润起来,直至变成翠软的一团绿雾。时常有戴着斗笠、穿着蓑衣的农人牵了耕牛远远地从河岸上走过,牛偶尔的一声长哞听上去像句诗一样。稻田里的紫云英怯怯地开着紫红色的小花,雨雾中有着令人惊艳的干净的美。我哥哥和梁小民等一群半大男孩子日日不知疲倦地在河边和稻田的月口处梭巡,伺机捕捞逆水而行的肥美的鲫鱼。涔水镇家家户户的厨房里都充满了葱烧鲫鱼的香味。
我很享受在后窗看到的一切,美好寂寥的景致让我沉醉。那一年小镇上的女孩爱上了一种新的游戏,她们把含苞待放的野蔷薇和刚抽出嫩叶的竹枝摘下来,去掉竹枝的嫩叶,把蔷薇的花蕾插进去,做成奇怪而妖艳的花枝。有时她们人手一束,叽叽喳喳成群结队地从后窗经过,她们被细雨打湿的头发又黑又亮,像绸子一样。有一回,我看见叶红梅和梁裁缝相继经过后窗回到小镇,叶红梅撑着白色的自动伞,她过去后约有一炷香的功夫,梁裁缝也披着透明的塑料雨披从同一个方向过来,细雨汇集,刷洗着雨披上青草的汁液。尽管他们是在不同的时刻经过后窗,尽管梁裁缝手里还拎着一条串满了鲫鱼的柳枝,但他们同样轻快的脚步、干净的面容,使我把他们纳入到同一副画面里来,让那些拿着妖艳花枝的小女孩簇拥着他们,并把他们当做两个喜悦的人收藏在我的记忆里。
天快要黑下来的时候,后窗的世界更是神秘得令人心跳:夜在沙沙的雨声中漫步而来,它的黑纱似的翅膀慢慢掩盖了一切,被紫云英的花朵装点的稻田像盏渐渐熄灭的彩灯默默隐入黑暗……就是在这样一个黑夜驱赶白天的时刻,有一次我竟看见过死去多年、我从未谋面的外公在夜幕四合下的河岸上走过,他穿着藏青色的长衫,撑着桐油纸伞,神情寂寥、脚步茫然、踌躇。
那一年我已七岁,但我能说的话却很少。言语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谁能想到后来我会做了牙尖嘴利的律师?)。但我在看到外公的那个傍晚,破例在下楼吃晚饭的时候说起了我看到的这个穿长衫、脚步犹豫的男人。听完我的三言两语,我的外婆放下饭碗,泣不成声。当年外公被打成右派,外婆为不累及上卫校的母亲,果断地与外公划清界限——外婆的这一举动一直为涔水镇人们所称道。
是识大体的女人,人们说。
后来外公因病去世,死在异乡的破草房里,时间一晃又过去了好多年。对外婆来说,这段时间又未尝不是格外地漫长?漫长得足够她重新过上这样的几辈子呢?
偶尔有雨后短暂的晴天,雨声消退后的小镇,人声就像雨后春笋一样茂盛生长,街头巷尾到处是各种各样的人言,它们飞短流长,淹没了鸡鸣狗吠。
叶红梅的婆婆六婆在那个春天还能走动,雨停下来后,她扶着墙穿过一条无比喧闹的街道,从东街走到我家所在的御銮巷来。巷口的泡桐树一到三月就结满大而暗败的灰紫色花朵,花朵低垂,开起来老态龙钟的样子。人坐在树底下说着话,时不时有朵花“噗”一下掉下来,只是听这“噗”的一声响,你就知道这朵花不是落了,而是死了。
天一放晴,各式各样的老太太就齐聚到泡桐树下来。她们出门前一律用煤油篦过头上的虱子,脑后的发髻油亮亮的、一点就着的样子。她们的手指上都戴着铜顶针,手里拿着插着针线的鞋底。她们偶尔也看我一眼,对我外婆说,这丫头还是不说么?我的外婆有时答,可不!有时答,在家里也说。这要看我外婆的心情和她当时所处的境地。外婆如果碰巧手上没活干,看别人飞针走线,自己倒像个吃白饭的样子,外婆就会伸手把我搂过去,使劲晃一晃我说:“可是个没良心的,做给她吃,做给她穿,夜来给她盖被子,连一声儿外婆也听不到她的。”当然在大部分时候老太太们对我是熟视无睹的,她们要诉说的太多了,各家的生计,各家的媳妇,种种的不易与委屈。
六婆颤颤微微地过来了,扶着墙慢慢溜到马扎上去。她咳咳咳地喘上半天,蛇一样嘶嘶地说:“……偷人婆!回回到家,短裤子都是湿的呢。”
六婆说的是她的儿媳妇叶红梅。六婆一直到死,对叶红梅都充满了怨恨。镇上有个人是钻井队的,和赵大军差不多同时结的婚,人也不是经常在家的,可人家的爹妈孙子都抱在手上了。
听到六婆的话,我外婆等人就把嘴撇得扁扁的,以示对叶红梅的不屑。我不是第一次听六婆这样说叶红梅了,我不明白人怎么会被偷,叶红梅的短裤为什么会湿呢?大人的世界总是这样混沌、污浊、不明所以和暗藏敌意。六婆家的大门框上钉着“光荣军属”小木牌,过八一节的时候镇上的领导会提着麦乳精、红糖去看她。生着肺病的六婆是骄傲的,她的儿子是世界上少有的好儿子,儿媳妇是世上少有的坏儿媳。
“咳、咳咳、咳……昨儿给我吃春笋腊肉汤,发物么,盼着我早死呢。”六婆总是有得抱怨。
叶红梅下了班,有时会顺道过来搀护说了她一下午坏话的婆婆回家。人们看见她微蹙着眉,安静地若有所思地搀着六婆走远,总是难以把这样一个女人与卖肉的毛二、税务所的罗圈腿小江、镇医院的秃顶王大夫之类的男人联系起来——他们哪个也配不上她。再说了,这几个人有哪个是胆大的?军婚呢,不是开玩笑的。虽说是不信,但人们还是很乐意听到六婆这样的话,这些话真是让人想入非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