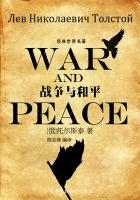梁裁缝这个人本没有什么好讲的,一个裁缝吗。在三十年前,这样的手艺人多了去了。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小镇上的手艺人,却在三十年前成了方圆几十里轰动一时的人物。人们后来谈起梁裁缝,人人脸上带了点微笑,想起他双手反剪,站在高台上示众时的样子,就有人忍不住感叹:“乡下人么……”
对那一天我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
那是阳光灿烂的一天。我乡下的爷爷碰巧来镇上买壮油菜苗的化肥,平常人声鼎沸的小镇安静得出奇,我坐在门槛上玩一方花手绢。见有人风一样从街道上跑过,爷爷就带着我跟了过去。我们走出小镇,发现出小镇的公路上到处是人。我们远远看见人们就像流水似地汇集到一个小山坡上,山坡下的公路边停靠着几辆草绿色的解放牌大卡车,半山腰已搭起了一个木台。爷爷把我举到一侧肩膀上努力往前挤,人真的是太多了,竟有人扛了甘蔗来卖,也有人推了装着香瓜、凉茶的小车在山脚下吆喝,女人们的手里往往还忙着针线活,人群里热烈的议论声使得现场就像一个市集。后来人群骚动起来,有几人被押到了木台上。我数了数,一共五个。梁裁缝就站在中间,他的左边是一个把继子淹死在水缸里的乡下女人,右边是一个打死自己工友的矿工。人们指点着他们,兴奋地议论说这是一准要枪打的了——还没等法官登台宣判呢,老百姓自己就把案子给断了。
台上五个人脖子上都挂了个划着红叉的白色木牌子,梁裁缝不像其他人那样垂着头,他把脸略微偏向一边,就好像他不好意思似的。
梁裁缝是有名有姓的,但平时他的姓名都用不上,大家只是叫他裁缝。要不是他有双叫梁小民、梁小蚊的儿女,谁又能知道他姓梁呢?晚上我外婆在昏暗的灯光下补我哥哥撕破的裤子,我的母亲总会说一句,值什么,拿给裁缝匝匝吧。梁裁缝的儿子在学校惹了事,老师这样让孩子捎信叫家长:让裁缝来一趟。就连他的老婆李兰珍,在外面提到丈夫,也是这样说:“哎呀我们裁缝……”所以那天,当我端坐在我爷爷一侧的肩膀上,越过无数攒动的大人的头顶,在一个白色木牌上读到梁裁缝的名字时,我吃一大惊也就不奇怪了。梁裁缝胸前的牌子上写着:“粱三来。”——原来梁裁缝叫粱三来。
观看完公捕公判大会,大家纷纷猜测,枪抵在后脑勺上,裁缝会不会尿裤子?五个人都是死刑,除了裁缝,其他人都有命案在身。人们就说,裁缝这下吃老大亏了,搞什么样的女人不好呢?搞个军属!
有的男人,主要是镇上那些在政府、学校、医院、工商税务等部门上班的男人,他们把一只手塞到裤兜里,一手捏着根卷烟,想起裁缝那些可能的暧昧场面,无不带了点艳羡、带了点轻蔑地摇着头笑着说,这狗日的裁缝!
我爷爷记挂着地里油菜苗,牵着我急急地往小镇赶。他从旧社会过来,属于那种见多识广的人。以前涔水镇的河滩里,哪一年不得杀几回人?土匪火拼、民间斗狠、衙门的法办,后来是打土豪劣绅、灭地富反坏,何曾消停过?所以我爷爷只嘟囔了一句:“划不来吗,少说也有二十年的好米没有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