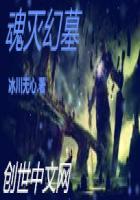在小兴安岭中心狩猎队各家各户的猎犬队伍中,那些年说起来,我们家的狗群算得上庞大和精英了。就数量而言,最多的时候有十七八条,是其他人家的三四倍呢!四奶奶就牢骚:“拿什么喂哟!就那点口粮!”注册的猎犬供应一份粮食。但是多数猎犬都没有户口,四爷还偏爱,所以说一日三餐就变成了问题。
“僧多粥少”,唯一的办法就是指望着狩猎,也许是饥饿或因为饥饿被逼上了“梁山”,遇上猪群必然一场恶战,刀光剑影,血肉横飞,地动山摇,喊杀声震天。所有的猎犬有收获,空手者四爷就狠狠地数落:“你以为是‘大跃进’吃食堂哪!干不干活都有你一份!饿着吧,看你以后还敢再偷懒!”四爷对“大跃进”非常熟悉,但是也痛恨,多劳多得,就变成了湛四爷一贯的政策。所以说,我家的狗群战斗力就特强,所向披靡,无坚不摧。大小动物一旦被围住,即便是插翅也休想逃走。当然了,猎犬中,最为出色的要算是老黑,它既是四爷的骄傲和自豪,也是同类们的楷模和榜样。
我到四爷家较晚,我还没来,听说老黑就早已经是“老大”了,声望极高,有一定的威信。但它是“招聘”的,始终没有“编制”。四奶奶就唠叨:“不许你霸道,没有户口,还豪横上了呢!”每次喂食,老黑的态度都非常恶劣,左一口,右一口,把同伙吓退了自个儿独食,惹起四奶奶的谴责和恼怒,用铁勺子狠狠敲着它的脑袋:“发扬点风格,再仗势欺人,我就让你饿着!怎么着,不服哪!敢跟我瞪眼!”“啪哧”又一铁勺子。动物抢食。互不相让,谁也不惯着谁。但猎犬不同,猎犬对主人绝对地服从,绝对地忠诚。这是习惯也是一种制度,否则它马上就会毙命。同病相怜吧。
我也没有户口,当然也没有供应粮的待遇,于是每次我都要替它申辩:“奶奶,两头野猪都是老黑逮的,对它不公,它能满意吗?”四奶奶轻轻哼了声鼻子,我立马就发现:大黑轻轻晃动着尾巴,看我的目光也流露出了感激。目光和表情仿佛在说:“够意思!小主人,到底是哥们啊!”老黑个儿大,毛长,垂耳朵,眉毛有黄点,外人都叫它四眼子狗,它不仅眉毛,四个爪也是黄的,像舞台上的花脸穿了一双黄靴,遇到猪群,它的两只粗腿就发挥出了优势。我多少次看到,猎场上它死盯着一头百十斤的野猪,开足了马力一头给撞倒,野猪爬起来它继续再撞,借助了惯力和地形上的优势,野猪每次都要翻个跟头,接二连三就彻底懵了,可怜巴巴,是那么无助。此刻老黑才把它按住,血盆大口对着野猪的脑袋,鬃毛倒戗,雪白的利牙像两排大刀子,抽着鼻子两眼喷出火来,炸雷一般猛地一声吼叫:“汪——”野猪伴随着一阵颤抖,精神上就彻底被解除了武装。
像猫抓耗子,仅靠威力和残忍的震慑,野猪爬起来也不敢再逃跑,而是乖乖的,服服帖帖任老黑摆布。弱肉强食,当时我就纳闷,野猪怎么变成了小绵羊了呢?除了跑起来四个蹄子生风,嘴巴子上的狠劲又哪去了呢?像缴了械的俘虏,被押回了屯子。老黑给解决了运输上的难题,它这一强项,是其它猎狗都无法能及的,这也就变成了它霸道的资本,没有户口,吃饭的时候对谁也不客气,也许老黑的心里头明白,猎杀容易,运输难啊!翻山越岭的步履艰难。别说五脏头蹄和下水了,狗吃饱了没有力量,有时候好肉也得白白地扔掉,老黑在狩猎队开了一条先河,自然也受到了众炮手的夸赞。
老黑仁义,对谁都宽容,不管对主人还是林场里的学生,踢它一脚它也不会反抗,厚道的性格甚是让人敬佩。马善人骑,能者多劳,久而久之,每次苦差,四奶奶就指定老黑去担当——除了它力大多拉跑得快,再就是场部人多淘气的孩子更多,不用担心猎狗会伤人。我去四奶奶家的第一个寒冬,四奶奶让我去林场场部领粮,人粮狗粮加在一起三四百斤呢!三十里地,场部坐落在大鹤立河下游,简易公路紧贴山根,连续降雪,被西林钢厂运煤汽车辗压得溜平,稍微不慎就可能摔倒,运输工具历来就是爬犁,狗拉雪橇,空爬犁飞起来子弹头一样。回来负重步步又是上坡,绳套上的猎狗那是真累啊!但空爬犁舒服,四五条猎狗蹦着高儿飞跑。乘坐爬犁危险性就特大。
三九天鬼龇牙,我全副武装,皮袄皮裤皮帽子,大头皮鞋手套,像只油桶,自己摔倒了爬起来都困难,五条猎狗大黑居中,中坚力量又能照顾左右。我坐上爬犁四奶奶才嘱咐:“去的时候下坡,别一个劲儿傻跑,摔了我孙子,我跟你们没完,听见了吗老黑?”见老黑轻轻晃动了尾巴,四奶奶才放心:“那就走吧,早点回来,到了林场别惹出来麻烦。”白雪皑皑山谷宁静,光滑的公路上不见一个人影,只有西北风在嗖嗖地刮着,视力模糊,眼睑上挂了冰霜,手脚像猫咬针扎般地生疼。五条猎狗可能为了取暖,拐上了公路就飞奔了起来,把四奶奶的嘱咐全忘在了脑后,爬犁磨冰,冰托着爬犁,人在爬犁上很快就僵了,我担心自己被甩落了下去,就换个姿势坐着更能稳些。但万没有想到前面是拐弯,拐弯的时候狗群也没减速,两手一松还没来得及调整,整个身子就飞旋了出去,“嗖,啪嚓!”旋出了公路实实在在砸落进雪沟。
安然无恙多亏了积雪,但爬起来一看,狗拉雪橇早就没影了。糟了,太麻痹大意耽误事啊!粮本和现金没有交给狗啊!不行,我得去追。但站起身来又改变了主意,因为在远处我清楚地看到:狗群回来了,发现我丢了又赶回来找呢!不行,得给点教训,不能这么便宜,看看它们怎么来收场?我扑通一声又卧进积雪里,耳朵尖尖听着动静。“汪汪汪!”狗鼻子特尖,老远就闻到了,可想而知是多么兴奋,爬犁很快就在我头顶上停住,肯定在观察我是否有危险。同时吼叫,不约而同的,叫声在山谷中沉闷而洪亮。
叫声刚停就疾奔了过来,一边吼叫一边用牙齿衔我的衣服。担心羊皮大衣被撕坏,我就闭着眼睛用两脚狠踢,背后上的牙齿被迫放松。见我置气,猎狗就哼哼,仿佛在告饶:“起来吧,俺们也不是故意的,以后小心还不行呀!”我犟劲上来了,死卧着不动,除了哼哼,除了叼衔。看它们还有什么章程?忠诚的猎狗不跟我较劲,急返回家中把四奶奶接来,让四奶奶出面协调这场矛盾。“栓子!爬起来吧,你也好意思的,让老黑它们为难。”见我爬起来,四奶奶转身又数落老黑:“记吃不记打的东西,反复嘱咐,你扭头还是忘啊!”老黑表情傻呆呆地愣着,虚心接受老主人的批评。再坐上爬犁我就内疚地看到老黑跑几步就扭头看看,目光神气仿佛在说,千万当心啊!没有摔坏,我就阿弥陀佛!
第二年冬天,老黑为救我葬送了性命。迎头不打猪,顺腚不打熊,迎头打猪是猎场上的大忌。那年特冷,也确实是累了,半水壶老白干几口我就吞了。林区男女都有饮酒的习惯,何况我们猎人,靠酒壮胆,靠酒解乏,靠酒才能进入梦乡。听见狗咬我才知道醉了,脑袋发晕两腿拌蒜,踉踉跄跄奔着叫声扑去。每次出猎,猎犬老黑都陪伴在我左右,履行头狗的责任和义务。没有命令它不会走开,尤其是主人是刚上阵的新手。离孤猪很远,蒙蒙撞撞我就开了一枪。这下糟了,孤猪这种猛兽最忌恨药味,尤其是枪口下逃走了的野猪,闻着药味就拼了命扑来。说时迟那时快,闪电一样。我匆忙焦虑地刚退出壳子,第二发子弹来不及填膛,疯狂的野猪就扑到了跟前,红着眼珠,晃动着獠牙,根根鬃毛铁丝般竖着。我手忙脚乱出了一身冷汗,伴随着冷汗醉酒也醒了。
千钧一发,就在我绝望悔恨的瞬间,老黑奋起急迎了上去。相比之下尽管它重量轻,体重还没有大孤猪的一半。但此刻的老黑像出了膛的炮弹,“噗”的一声急撞在了一起。野猪的速度受到了遏制,我乘机也闪身躲到了树后,来不及喘息就清楚地看到,老黑反弹滚出去数米,丧心病狂红了眼的孤猪,以它的残忍和十足的霸气,改变了方向扭头奔猎狗,獠牙冲老黑狠狠地刺去。随之又一挑,甩出去有丈远,“噗”的一声,恰恰又甩在我旁边的树上。老黑顿时就葬送了性命。
当其它猎犬急追了上来,发泄完的孤猪才大摇大摆隐匿进了林子。老黑死了,我的灵魂似乎也没了,那天我搂抱着老黑的尸体在猎场上一直蹲坐到了深夜,狗救主人,司空见惯,猎狗的行为更是屡见不鲜,可那天我是喝醉了酒啊!因为醉酒和思想上的麻痹,白白让老黑搭上了性命。我把老黑葬在房后,使它的灵魂永远不会离去,即便是我后来转去了林场,清明节的时候,也要到老黑的坟墓上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