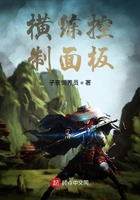抬眼看着流苏踏着一路晨光走来,一片逆光中,她的五官看得不太真切,柔和的旭日模糊了她的唇线,那身臃肿的黑袍被阳光剪辑得恰到好处,款款走来的流苏,脚步不轻盈,但是异常稳秀。乔一白站在路边单手插着口袋,没样子地倚在墙上,一条腿蹬着墙面,朝着早起浣衣买菜的美女吹口哨,活像个**。“哟,云流苏下士,昨天晚上你干什么去了?”乔一白是那种没事都要拨撩她一下,唯恐天下不乱的货色,在暖洋洋的日头里,彻夜通宵的乔一白不见丝毫困倦,反而神采奕奕。“野战。”心情恶劣的流苏口不择言。“啧啧,”乔小贱凑上来,贼眉鼠目上下打量了流苏一番,“那你怎么还是一副欲求不满的样子?”“住口吧,”流苏顺口回了他一句,“整条街的下限都被你拉低了!”白日的失落街道,褪去了夜晚的醉生梦死,抹去了月夜的血雨腥风,同时也抚平了涌动的暗流,宁静而祥和,像是江南行省的杏花疏雨般宁静的早晨,那个被誉为“人人都道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的江南道。会有走街串巷的手艺人兜售早点,会有妇人早起浣衣做饭,洗着尿布的年轻妈妈口中哼着不成调的小曲,吆喝声和喧哗声让流苏觉得,没有全息影像的世界也很美好。毕竟几千年前,我们的祖祖辈辈就是过着这样的生活。有米粒大小的花卉飞舞在空中,流苏眯着眼睛,在阳光下显得有些不真实,像是雪花又像是文明时代的白樱,这是末世以后可以在自然状态下生存的硕果仅存的几种植物之一,坊间将它称为米粒花。“失落街的米粒花很漂亮,尤其是在深冬落雪的时候,”乔一白用手拢了拢随风飞舞的米粒花,像是在驱逐讨人厌的蚊子——流苏敢打赌,这种生物的讨厌程度也绝不会超过乔一白本人。只听这货是这么破坏气氛的,“因为落雪时,一时之间分不清哪里是雪,哪里是花,就像这整个失落街,你分不清眼前的繁花似锦,有几分是真情实意,有几分是逢场作戏。”这个白天圣洁,夜晚堕落的街道!感谢玫林行省的军事独裁,才能维持如此的高效率。等两人走回飞行器失事的原点,救援部队早已赶到。如果换成我们“民主自由”为导向的联盟议会,估计光是扯皮推诿的功夫,两人就可以在失落街过新年了。那只保持人类理智的骸魔被装入特质的箱子内,他拼命拍打着玻璃笼子,可惜没有用,就像是一只被养在浴缸里的金鱼,总以为外面的世界触手可及,但是却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流苏就在下方目送着林卿鸢离开她的视线。忽然一架银灰色的战斗飞行器降落,由于他的型号和编号过于复杂,民间更喜欢将这种在国庆阅兵上出现率极高的战斗用机成为“银翼魔术师”,上面印着第二空域的新月标志。曾经有人吐槽过,第二空域有两大标志,一个是专属的新月徽章,另一个是他们傲慢而刻薄的作风。李非小金毛曾经这么嘲讽道,“云流苏下士,能不能拜托你不要这么刻薄,不然第二空域会觉得你是在侵犯他们的专利。”从战斗用机上走下来开道的人,身穿纯白的联盟空军制服,干净到纤尘不染,和总是满身泥浆的陆军作战和风吹日晒的海军部队不同,空军们总是能维持他们得体的衣着和翩翩风度,这并不意味着空军们安逸而不作为,他们的高强度表现在另一个方面,至少有恐高症的小金毛是不可能完成的。纯白的帽檐下打下一片阴影,刻薄到不近人情的薄唇更加突兀,那人目光似乎不经意间一扫,但却带着极强的观感,一下吸引了流苏的视线,她望了过去却瞬间僵硬。司曜,居然是他!司曜和另一空军作战员尽职尽责地站在两旁,他看上去比起在格桑学院时更瘦,穿着纯白制服的他身姿挺拔,像是直插入地面的白色尖刀,除了白珩以外,他是流苏认识地这么多人中,最能代表军人强硬而严明的形象的人。然而流苏只是将那句“我在玫林行省等你”在脑海中过了一遍,就将注意力从司曜身上转移。后下来的一个人,流苏更为熟悉也更有利害关系,陶桢穿着一身黑色的军装,黑色的帽檐下是一双海蓝色的双眸,他温润如玉的气质和刚硬的军装完美的融合,手上带着雪白的手套,脚上的军靴锃亮得晃眼,肩章上的金麦穗在阳光下熠熠闪光。理论上陶桢是军处研究所的人,而司曜隶属军部空军处,哪怕陶桢的军衔比司曜高,也没有权利干涉,但是司曜亲自护送陶桢至此,就表明了陶桢的身份和低位,也表明军部对他的重视。陶桢看上去像是在军部开会后直接过来的,军装都来不及换,但不可否认,他看上去更加有魅力。流苏第一次看他穿军装,他海蓝色的双眼比起以往多了几分凌厉,像是两道锋利的钩子,目光似乎要化为实质,在流苏身上挖出两块血肉来。“云流苏下士,”他踱到流苏面前,含着温和的笑容却让人笑不出来,“你来玫林行省不出一个月,就学到了偷袭长官这种需要极大天赋的技能,那如果让你呆上一年,你是不是连上将大人都会不放在眼里?”流苏低下头看自己的脚尖,头上毛茸茸的狐狸耳朵耷拉着,看上去在反省自己的错误,就像每次思修课翘课时的虚假忏悔一样,“我当时操作的时候,手‘一不小心’滑了一下。”“是吗?”陶桢轻描淡写地说,“我会向机械总部的人反映下士你的情况,并且敦促他们尽快研发出不会让下士你‘手滑’的飞行器。”说到这里,陶桢眼底的笑意振翅欲飞,“不过也许下士你需要重新考取飞行器驾照,会来得实际一些。”乔一白那个没心没肺的死小孩差点笑倒在沙地上,他甚至瘪起嘴巴,学着机械总部那只青蛙部长的口吻说道,“下士,你居然质疑我这半辈子最得意的杰作,这和质疑我的生活作风一样让我不能忍受,这么完美的手杆和操作台,居然也会让下士你手滑?那一定是你的手有问题,你确定你操作之前洗手了吗?呱。”谁能来告诉她,最后那个诡异的呱是怎么回事?现在是隆冬,谁会和你“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啊?陶桢不是那种刻板到上纲上线的人,他身边的这位第二空域队长才是,如果是司曜的下属在他和别人交谈时插话,司曜绝对做得出登时一脚把他踹翻的举动。陶桢对乔一白可谓是纵容,而且他平日里不拘小节,由着乔一白看热闹不嫌事大,非原则问起上对这位出身“黑印”的投诚分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这次,陶桢对流苏真的有些光火,他还是眯了眯眼睛,朝着乔一白随意一瞥,带着威胁的神色,乔一白在他手上出乎意料得乖巧,马上闭嘴收声。接着,陶桢收敛了笑容,对流苏说,“云流苏下士,也许我们应该单独谈一谈。”这是她最近第二次被邀请“单独谈一谈”,对流苏而言,简直是先出龙潭,又入虎穴。路过司曜的时候,后者没有任何表情,严肃地像是一尊石像。陶桢的确是从军部会议现场直接赶过来的,证据是桌上放的一份机密纸质文件。在末世的今天,纸张这种东西几乎在联盟绝迹,在中州的偏远地区还硕果仅存。但是她听洛林讲过,军部会议上的、甚至是军部最高会议的圆桌会议的材料,都是纸质的,人类依赖了纸张这种媒介载体几千年,这种依赖似乎成为一种信赖。人类并不相信电子这种随时可能被盗取的数据,对白纸黑字一往情深。这份可能决定千万人前途的机要文件就被主人这么漫不经心地摆在桌子上,流苏只扫了一眼就挪开了视线,以她今时今日的低位没有资格知道。就算陶桢真的摊开让她看,她也有贼心没贼胆。陶桢脱下军帽,坐在椅子上,手边是一杯冒着余热的咖啡,他方才的凌厉气质似乎随着咖啡的雾气一起消散了,颇为和颜悦色,“坐。”流苏只坐了三分之一的空间,双腿并拢,双手放在膝盖上,一副标准的小学生坐姿。“下士,你不必紧张,我不打算追究你袭击叶执中尉的事情——那是你和叶执中尉的事情。我一开始和你说过,我只是需要一个助手,不在乎她的过去,不在乎她的未来。”陶桢揉了揉太阳穴,呷了口咖啡,映像中陶桢总是那么疲倦,“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也不在乎她会愚蠢地以身犯险。我要的助手不是任何人都可以的。”“云流苏下士,需要我特意向你说明吗?你的这种行为不被允许。我不会花功夫和你讨论这种高风亮节的行为的重大意义,是不是符合议长先生提倡的新时代精神。我实验室的成员需要记住的第一条,就是危急时刻保住性命比一切都重要。”“真是可惜了,云流苏下士,现在早已过了个人英雄主义的年岁。”
同类推荐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