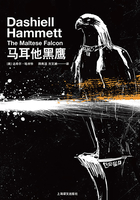“所以,现在海滩正在对你说些什么呢?”费普斯问,表情像个传教士一样正经八百。
“闭嘴!”我的脸已经红了好几小时了,“你才是怪胎。你是个乳头怪胎,你知道吗?”
“我有否认吗?你火大是因为我告诉那位女士你是怪胎吧?所以你才心情这么差吧?你应该以身为怪胎为荣才对,迈尔斯。看,大家多注意你啊!”
“是啊,真是太棒了!”
“嘘!”费普斯打断我,“我想海滩刚刚好像在说什么呢。嘘……”
“少来。”
“嘘……它又说话了。”他压低了声音,嘴唇真的几乎没有动,“我等不及那该死的、他妈的潮水赶快涨上来了。”
他大笑着,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平衡和呼吸,看起来实在太笨拙可笑了,害我也差点忍不住笑了出来。
这天我们又来到了查塔姆湾,根据我们的判断,退潮的水位是负二。即使天空阴阴的,太阳还是像七月时一样炙烤着我。费普斯却没有这样的困扰,照他自己的说法,因为他又高、又黝黑、又迷人。每当我觉得自己的确晒黑了一些时,他就会将红彤彤的手臂伸到我的旁边,吹着口哨,进一步证明我比他想象的还弱小。
在我们休息吃午餐时,我担心起弗洛伦斯来。过去一星期来,我帮她准备了六天的午餐,虽然只是鲔鱼三明治和一些葡萄,但我看得出来,如果我没准备,她就根本不吃饭。我想到她坐在椅子里等我的样子,才惊觉到这一星期以来,我的心情已经从很自傲能帮她准备午餐,变成了如果没去就会自责。
费普斯打断了我的罪恶感,他说他又带了另一个富有教育意义的玩意给我。我本来预期他又要念一段《教父》,让我自觉像个发育不良的小矮子,没想到他这次带的是一本叫《变化》(Variation)的杂志,大小和《电视周刊》差不多。封面上的女人对我展示着舌头和胸部。
“你从哪儿拿到的?”
“从我哥的《汽车与驾驶》杂志后面拿到的。”
“她是歌手吗?”
费普斯大笑:“这很重要吗?”
“我只是很好奇她是不是演员或歌手,或者某个我们认识的人。我只是想知道自己看到的人究竟是谁罢了。”
“是吗?”他又大笑,“那你来看看这个宝贝,也许你可以认出她是谁哦。”他快速地一页页往后翻,里面大部分是文字,但也有很多小照片。他翻到某一页,上面有个穿牛仔短裤的女孩,不过裤子已经褪到她的膝盖附近了。她用双手托着自己的乳房,像在卖苹果一样展示着,照片上还有一行字:邻家女孩 。
“认得她是谁吗?”费普斯设下圈套。
我的脑子里一片混乱:“不认识。”
“她是那个邻家女孩啊。”他挤了挤眼睛。
“谁的邻居啊?”我开始冒汗了。
“某人的邻居啊。你以为漂亮女孩就没有邻居吗?”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她看起来的样子,就像是胸部摸起来很舒服,舍不得将手放下似的。费普斯解释说,这照片一定有用喷枪美化处理过,他听他哥哥说这种图像处理小技巧可以盖掉青春痘、蚊子叮咬的痕迹和胎记。“还可以改变嘴唇、微笑、眼睛颜色和乳头大小呢。”他一副行家的口吻说道。
“我知道。”我说。这种无知的感觉让我十分厌烦。
他继续用手指一页页地翻,找别的东西看。突然间他翻到一堆小小的照片,上面的女人展示着自己的私处,引诱我跟她们上床——至少那大大的标题上是这么写的,上面还登着她们的电话号码。我简直不敢相信。显然如果你有胆的话,就可以马上打电话给她们。
我往后退,觉得难以接受。我看过《花花公子》的插页照片,也仔细研究过《体育画报》比基尼专题里的每一张照片,但我从来没看过女人的私处就这样明目张胆地展示在她们的电话号码旁。费普斯大笑道:“怎么了?你不喜欢看裸体的女人啊?”
“我又不是她们的医生。”我说。对费普斯这种人来说,这个回答真是愚蠢到家了。
他在旁边自顾自地大笑了一阵,然后说:“我打睹你一定想当安琪的医生。”
他还在那摇着后脚跟,半闭着眼的当儿,我扑上去啪地给了他一巴掌,开始拼命地追,直到他上半身躺平,膝盖整个跪在沙滩上为止。但他还是没忘了把他老哥那本变态杂志紧紧抓在胸前(天啊!),免得把书弄湿了。
事情发生得太快,连我自己都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在费普斯来不及第二次骂我“他妈的怪胎”之前,我听到摄影师的声音,还看见那个在我发现巨鱿的早上问过我许多问题的女记者。他们一面磕磕绊绊地跨过覆满藤壶的岩石朝我们走来,一面大声说话,对于自己的大嗓门毫无知觉。
“糟了,”我说,“是电视台的人。”
“太好了,”费普斯爬起身来,“他们可以拍下我把你踢得屁滚尿流的样子。”但他显然只是嘴巴说说而已,谁会想被拍到自己以大欺小的样子?
那个女记者大声喊着我的名字,挥手跟我打招呼的样子好像我们是表姐弟一样。
“她很可爱。”费普斯根据远在十五米外的判断,断言道。
她走了过来,向我伸出一只手。我试着想和她握手,但又有点尴尬不知该真正握住,还是用对待淑女那样只是轻触手指。她握完后连忙检查手上有没有沾到泥巴,结果还真的沾到了一些。
“还记得我吗,迈尔斯?”
我心想,你就是那个呕吐的假人模特儿,然后点了点头。我打定主意什么也不说,但会不会事情其实没那么严重?如果她和我对话的方式,就像那个记者小姐一开始时的那样,又该怎么办?
她并不像费普斯说的那样性感可爱,两只眼睛分得太开,看起来好像一只双髻鲨。她说了一大堆废话,我都没仔细听。最后只听见她提到发现巨鱿的那个早上,我说过也许地球想要告诉我们什么。
费普斯强忍着没笑出声。
“我不应该那样说的。”我咕哝着。
“为什么不应该?当时我们都觉得这句话很有煽动性,是一种很聪明的说法。现在,根据你所发现的鼠鱼来看——”
“是褴鱼!而且我也没有任何证据!”
“什么东西没有证据?”
“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地球想告诉我们任何事!”我听着海滩、海水和天空的声音,就是没去听她在说些什么,但我努力别让人看出来。
“那么,你要怎么解释那条……什么鱼呢,迈尔斯?”
“我没办法解释,我只是看到它而已。”
“很好,好极了!那我们可以跟着你在这儿逛逛,看看你看到了什么吗?”
我故意看看四周,又低头看她脚上全新的橡皮靴。“我们只是在挖蛤蚌和找些东西而已。”我说。
“太棒了!”这时她才终于想起,向我介绍了一下那位摄影师,他含糊地打了声招呼。摄影师肩膀上扛着摄影机,半蹲着身体,看起来好像要放屁或是掷铅球一样。
我忘了自己到底有没有同意,还是我根本什么也没说,反正她和那个摄影师就这样跟着我们往潮汐线走去。这个时候,费普斯自动变身为我所见过最权威、知识最渊博的标本采集家。“看到那个钥匙孔形状的洞了吗?”他指着泥地上的一个小洞,“那底下有一只大约二十厘米长的奶酪蛤。”他用铲子瞄准那个洞,用夸张的姿势往里用力地铲了几下,然后用铲子边缘轻轻地刮,直到那只肥硕的灰色软体动物现身为止。接着他将贝壳轻松铲起,得意扬扬地丢进篮子里,双手完全没沾到一下。电视台的人呆呆看着那只从壳中探出身体的小家伙,又惊讶地看看费普斯。他对着他们眨了眨眼睛。
我在不断后退的潮汐线边缘闲晃,听着费普斯胡说八道,希望他们会因为听不下去而离开。
这时我发现一个象拔蚌的呼吸管,只好不情愿地把他叫过来。他这次可真成了英雄人物。他英勇地铲着,额头上冒出了点点汗珠,因为铲出的洞又迅速被水填满。当他整个胸部贴在泥地上,伸长手臂把象拔蚌给抓出来时,我听到那位女士由喉咙里爆出了阵阵笑声。我就知道费普斯会这样做,但我不想看,因此转身大步走开了,几秒钟后,就听到他像匹种马一样自鸣得意地笑着。
有好一会儿他们都没跟上来,我喜欢这样,因为身边没人时,我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但她很快又赶到我的身边,问我在找什么。“最主要是海星,”我说,“但任何其他特别的也都可以。”
我希望她能离开,但又忍不住把那些在浸水区舞动羽状触手的藤壶指给她看,就像花枝招展的南方女子。“它们正在捕捉细小的动植物,抓进壳里吃掉。看到了吗?”
她嘀咕着说了些什么它们“很难拍”之类的,但她离我太近了,飘来的阵阵香水味让人很难专心。有些香水会让你敬而远之,或让你打喷嚏,但她的味道却能诱惑人更靠近一些。
“你连藤壶都有兴趣啊?”她问。
“要不是有它们,我们可能都不会存在。”我告诉她。
她张大了嘴巴,但发不出任何声音。我继续往前走,将她带进深及足踝的海水里,介绍黑爪泥蟹、沼地瓷蟹和绿滨蟹的分别。她要我抓一只螃蟹来看看,但摄影师就尾随在我们身后,我不想拿着某个我根本不会想搜集的玩意,又被拍到一张做作的照片。
“你有听到嘎吱嘎吱的声音吗?”我问。
“有。”
“因为你踩死了很多沙钱。”
她缩了一下。
“走这边吧。”我说。
她有点不好意思,小心翼翼地跟在我旁边。摄影师咕哝了几句,然后打了一个哈欠。
“你觉得那是什么?”我问。
“轮胎残骸?”她顺着我指的方向看去。
“不对。”
“通马桶的活塞?”
“也不对。那是上千个月螺的卵。”我开始解释月螺是如何将卵和沙子、黏液混合在一起的,还有它们庞大身躯上的保护膜会分离出来,不经意地遗弃在沙滩上。有些好心来沙滩上捡垃圾的人就会把那也当成垃圾捡起来。
正当我努力讲些无聊话题好让她不耐烦离开时,突然看见某个长得像是太阳一样的多触脚生物,在沙滩上爬行。
它差不多有一个下水道的盖子那么大,背对着海水一寸寸地在沙滩上爬着,速度是我所见过的海星里最快的。它那偌大的微微发亮的红棕色身体,被二十二只触脚簇拥着。女记者倒抽了一口气,摄影师则是一阵咒骂。
“它在这里做什么?”她问。这时费普斯也赶了过来,嘴里忍不住爆出一串脏话。
“享受蛤蚌大餐吧。”我带着推测的语气回答道,“通常只有潜水员才有机会看到向日葵海星,尤其是体型这么大的,不过这家伙显然只顾着吃忘记了时间,或者根本没想到海水会涨到这么高的地方来。”
我伸出双手,小心翼翼地把它翻过来,它那带着上千只细小吸盘的脚微微地闪烁发亮。我将它翻回来,把它每一只脚尖端上对光线十分敏感的眼睛指给其他人看。“向日葵海星是全世界最大的海星,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很有可能就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只呢。”我向他们解释,向日葵海星就像是潮间沼地上的大灰熊,“其他海洋生物一嗅到它的味道就吓死了。海参会立刻让路,海扇贝会连忙往水里跳,连沙钱埋进沙里的速度都会比平时快。”我开始测量这只海星的尺寸。
我仔细研究它的体色,又用一根手指摸过它多刺的背部,
“你觉得为什么会是你发现了它呢,迈尔斯?”女记者突然问。
我刚想开口回答便被呛到了。
“为什么你似乎总能在这片海滩上发现奇妙的生物呢?”她锲而不舍地问。我注意到她手上银色的麦克风,又看向她身后的摄影机。
“因为我一直在看,”我说,“这里有太多东西值得我看了。”
“但是你不断发现人们在一般状况下应该不会看到的东西,不是吗?”
“如果你在这里待得够久,不同寻常的东西也会变得极其普通。”我忍不住说个不停,“就像威士忌角那些钳子上长毛的新种螃蟹,我五个星期前才第一次看到它们,现在那里已经到处都是了。还有煎饼湾也被一种新的海草占据了,你在那里几乎很难看到其他种类的海草。”
在我还说了一些类似的东西同时,她身后有一只大老鹰正准备往水里潜,但又突然放弃了突袭行动,改从海滩边上滑翔而过。跟老鹰相比,其他鸟类看起来实在是太过寒酸了。
“所以,或许呢,”她试探性地问,“就像你发现巨鱿那天所说的,也许地球想要告诉我们什么事。如果真的如此,你觉得它想说的是什么呢?”
我犹豫了一下,说:“它或许是在说:‘你们要注意了。’”
“这意味着,你觉得人们不够注意某些东西吗?”
我闭上嘴巴,听见费普斯嘀咕着:“你又来了。”
“我没有说这是一个问题。蕾切尔·卡逊曾说,人们对海洋了解得越多,就越不可能去伤害它。”
“谁是蕾切尔·卡逊?”
费普斯在我身后咯咯傻笑。“她是个天才。”我说。
“死掉的天才。”费普斯补充道。
她试图让我再多说一些,但我已经说完了。我告诉她我累了,这是实话,但更重要的是,我希望这一切就到此为止。
“你觉得有什么事是我们该做的呢,迈尔斯?”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我想我该把这只大海星放到我的水族箱了。你能不能拉我一把?”
她当然照办了。她也像安琪那样把手臂环在我身上,但没有任何感觉是值得我留念珍藏的。
突然间,她的香水味变得如此刻意,和这块泥沼地格格不入。这让我感到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