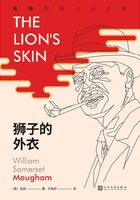那条鱼到了早上就和巨鱿一样,被拖到同一所大学实验室去了,克拉马教授和其他科学家到现在还在检查那只该死的巨鱿。隔天,一位记者打来,问她是否能来和我谈谈那条不寻常的鱼。
我打开门后,有一位瘦骨嶙峋、相机斜挂在胸部正中间的高个子女士低头看着我,问我迈尔斯·欧麦里在不在家。当我告诉她我就是时,她的欣喜让人一目了然,而我只能微微一笑。
“就是你发现了那只大鼠鱼吗?”
“是褴鱼!”
“发现那只巨鱿的也是你?”
“嗯哼。”
我还以为她会尖叫呢。她的脸看起来就是那种,你得聋了才能和她相处愉快的人。她问我爸妈在哪里,知道他们都去工作后,她似乎更开心了,不停地四处打量。然后我把她带到外面,让她去看我的房间。她跪下来,潦草地记下堆在我床边的蕾切尔·卡逊和其他海洋书籍的书名。从我的角度看过去,她那没扣住的衬衫领口可以窥视到蕾丝胸罩和大小适中的上半个浑圆。我就是没办法控制自己不去看,要是让费普斯看到这一幕的话,他大概连三只水母都咽得下去。我让她看我的水族箱,又和她聊到我的标本采集生意。她边听边点头,好像听的是她最喜欢的音乐。
我猜这一切都让她着迷不已,就像它们吸引我一样。我终于发现在我的引导下,也有人能分享我所着迷的事物了。启迪费普斯是如此的费力且无果,但之后竟能发现一位漂亮女士,看起来不但能理解这些让我兴奋的事,连我说的话都会记笔记,这简直让我乐到发抖。在我们往海湾走的路上,她不断鼓励我继续发表长篇大论的无聊废话,还开始帮我拍照——她疯狂地拍着,好像我是什么牛仔裤广告模特儿一样。
“假装你在采集什么东西的样子。”她从镜头后面指导我摆姿势。
我四下看看:“可现在是涨潮呢。”
“你涨潮时就不采集东西了吗?”
“应该不会吧。”
“哦,那就假装一下好了。”
有些小孩很会假装,我不算很擅长,但如果你看到那些照片就知道,我蹲下来捡起一个普通扇形贝壳时的迷惑表情,还真像捡到了什么神秘宝贝似的呢。
“迈尔斯,那是什么?”她一边按快门一边问。
“一个蛤壳。”我说。
“真的吗?哪一种蛤类?”
她蹲下身子,相机仍然贴在脸上,上衣领口垂下露出一个口。我忍住自己再去窥视的冲动,紧张地看看四周,确定没有人跪在我后面,免得我心跳加快时一往后退就被绊倒。像费普斯,他就最喜欢这种恶作剧了,而且他会这么做,一点也不让人意外。不过,四周除了我们两个外没有别人。
就在我目光扫过海湾时,她拍下了那张登在报上的照片,照片里的我拿着那个愚蠢的贝壳,凝视着水面,好像正要发现另一只褴鱼、巨鱿或十几只蓝鲸的样子。
我本来以为这些东西都只会被埋在报纸的某个小角落而已,但之后她突然向我要克拉马教授和爸妈办公室的电话。她还说,她想和史坦纳法官及费普斯也聊一聊。
“为什么?”不断涨起的海浪将一根海草或是垃圾什么的悄悄送到她身后。
她不耐烦地皱起眉头。“如果我要写你的故事,就必须和认识你的人谈谈,不是吗?”
“我还以为你要写的是褴鱼的故事。”
她大笑起来。她倒很坦白:“只是个关于某个小男孩不断在峡湾区发现新奇玩意的小故事而已。”
“怎么样的故事?”
“好故事。一个很好的小故事。”
我点点头,但其实还是很困惑。她放下相机,朝她车子的方向看去。
“下一次的大退潮是明天的七点十八分。”我绝望地说,“你需要的话我可以带你到处看看。”我感觉自己好像快要失去一个朋友了。
“我很乐意。”她说,但她的表情告诉我那不是实话,“但我不确定是不是一定能过来。”
她瞄了一眼手上小巧的腕表。“迈尔斯,以你的年龄来说,你会不会太矮了?”她说。
“以你的年龄来说,你会不会太没礼貌了?”我脱口而出。
她往后退了几步,好像我吐了口水在她额头上似的,然后像卡通人物一样哈地干笑了一声。
“说得好。”她说。
突然,她向我致谢,并用温热的手用力地和我一握,仿佛我免费帮她的花园除了草似的。
接着她便一路小跑到她的车边,把车开走了,车轮还扬起了阵阵沙粒。
我走到水深及臀的地方,去查看刚刚漂到她身后的是什么东西。那玩意上面长满了细小的藤壶,等我把它翻过来才发现原来是一只曲棍球手套。
如果是棒球手套还比较合理,我认识的人里没有在玩曲棍球的。而且,那手套已经硬得像木头一样,又重得不可思议。我研究了好一会儿,心想不知道这是否也有什么特殊寓意。
我妈妈看到报纸时,双手都发起抖来。
有时候,光是她的脉搏跳动就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她的骨头会随着每一次的心跳而晃动。我爸爸的手就从来不会抖,不过他常常很臭,身上不是沾着古风止汗剂,就是曼能痱子粉或斯科普漱口水的味道;否则就是鲔鱼味掺上BO白兰地以及皇冠牌威士忌的大杂烩;甚至可能以上皆有。这天早上,他的嘴巴臭得简直就是一个月没清洗的水族箱。他站在妈妈身后看报纸,每当她要翻页就不停地叫她等一下、等一下。
那篇报道我已经看过两次了,一次是在信箱旁边,一次是走回房子的道上。那位记者女士把我塑造成本地的汤姆·索亚,整个夏天都和伙伴“哈克”·费普斯在海滩上寻宝。克拉马教授称呼我是小天才,“对海洋生物有着永远无法满足的兴趣”,还说巨鱿和褴鱼是南湾有史以来最重大的发现。然后是史坦纳法官,他宣称在他雇来照顾牡蛎田的所有年轻人里,我是知识最丰富、最值得信赖的一个。至于我最忠实的好伙伴费普斯呢,对我的评论则是:“他是个怪胎。这家伙还算不错啦,但只要一谈到海洋生物,他就变成一个彻底的怪胎。”
报道里面有我说过的话,也有那位女士宣称是我说过的话。这篇文章将随着时间泛黄,最后会像那些冰冷的历史资料一样,垫在人们的抽屉里当衬底,一想到这我就忍不住口干舌燥,头晕目眩。我自己在脑海里先将这些都想过一遍后,才不情愿地将报纸递给妈妈,那感觉就好像床上盖了好多层毯子,让你的感冒由发冷变成冒汗。我知道那篇报道会写一些糟糕的事,但这天早上我看过之后完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如此大胆无耻的谎言,让我说不出话来——“海滩对迈尔斯·欧麦里所说的话。”
我可没这样告诉过她啊!我和她谈了将近两小时,从来没说过海滩曾告诉过我什么狗屎东西!她是从哪听来的啊?其他小孩已把我当成科学怪胎了,还有必要再让他们以为我是能跟沙子说话的疯子吗?
我等着爸妈来质问我有关那句话的事,质问我是不是个疯子,但他们只是匆匆地略了过去。真正把妈妈惹毛的是文中对我们家房子的描述:“两栋寒酸破旧的小屋,看来就像随时会崩塌在海滩上一样。”
“西恩,她说我们很穷!”
“她在哪里这样说?”老爸的两眼充满血丝,看了半天还没发现在哪里——也许其实他已经看到好几次了。“看起来还好啊。”他说,然后又回头从他刚才看到一半的地方继续看。妈妈只好不断偏过头去避开他的呼吸,并反复地指着那行字——“迈尔斯的爸爸西恩·欧麦里在酿酒厂工作”。她一心想激起他的怒气,说道:“她没有提到你是轮班经理,不是吗?”
爸爸咕哝了几声,耸耸肩。当有人问到他的工作时,爸爸总是回答做啤酒,只留下妈妈去夸耀他手下还带了二十六个人。他缓慢吃力地看完那篇报道,然后看着我,既没有骄傲也并不觉得丢脸,而是一脸疑惑地问道:“你床边堆了这么多书,而且几乎每本都看了至少两次?”
他不断发出哇的惊叹声,不过对我的评价并没什么提高,直到电话不断响起,他们接到四个朋友兴奋的来电后,情势才有了改观。突然间,妈妈开始煮起我最喜欢的荷包蛋,而且还管我叫做“我们的天才宝贝”。我很喜欢她用“我们”这两个字。一只丑陋的怪鱼竟然能帮忙把我爸妈凑在了一起,这听起来实在不太合理,但自从史坦纳法官说她是他所知的最见多识广的公民以来,我还没见妈妈这么开心过。至于爸爸呢,则是一副头刚刚被猛撞过的样子。他跟在我后面。走进好几个月没来过的车库,盯着我不断翻搅的半满水族箱,目光停在那只橘红色的海蛞蝓身上久久不能移开。
爸妈去上班后,另一波的电话蜂拥而至。《塔克玛新闻论坛报》、《西雅图时报》和其他三家报纸的记者,都努力地想哄我邀请他们过来谈谈。可我没什么想谈的。我拿起那个《奥林匹亚报》的记者留在我们桌上的名片,打电话给她。电话还没响满一声,她就接起来了。
“我是迈尔斯。”
“大红人迈尔斯?有什么事吗?”
“我从来没说过沙滩会对我说话。”
她哈地干笑了一声:“那是我说的,不是你说的。那是我用来传达的一种方式,你知道,就是你非常了解沙滩的意思。”
“那只会让我听起来像个疯子!我的意思是我听到蛤蚌喷水的声音,那告诉我它们可能很紧张;我听到潮水流经沙砾的声音,那告诉我它们正在往后退而非前进;我还听得到螃蟹掠过水面的声音,和藤壶闭上壳的咔嚓声……但海滩并没有对我说:‘嗨,迈尔斯,最近好吗?’”
她又哈的短短干笑一声,仿佛很赶时间没法好好笑完。“那会让人感觉你很聪明,而不是疯狂,所有读过报纸的人都知道,只有加上引号的句子才是当事人说的话,其他的部分都是我说的。迈尔斯,是我根据我所观察到的东西说的。”
她这很明显是在试图狡辩,但我也不想让她觉得有罪恶感。就是有这么一种人,无论你给他们多少次机会,他们永远都不会承认自己把事情搞砸了。“两小时之内就要退潮了,”我说,“如果你真的想看海滩上有什么的话。”
“什么?”她听起来像是突然变了一个人,“抱歉,我得去忙了。再联络吧。”
她当然没再跟我联络,直到她捏造出的小迈尔斯·欧麦里的神话有了更戏剧化的转变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