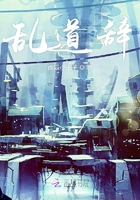“请大叔务必救他。”我含泪恳求。
“爹,快想办法啊!我看封小爷比上次严重多了!”晏老头儿子也是一脸焦急。
“自然要救,一定要救!宜笑姑娘莫急。”晏老头嘴里安慰我,急得也是来回走动,最后道,“罢了,还是找原先的郎中瞧瞧。他多少跟我有点交情,应该不会透露一点风声。再说,他是方圆几十里最有名的郎中,虽比不得皇城里的太医,稳稳病情也是有的。”
当机立断,晏老头儿子赶车去请郎中。这里小香已经端来了烧好的水,又放了碗稀粥。我给封逸谦洗了脸,端起粥碗一口一口地喂他。大概是饿了,加上他迷迷糊糊的,一碗粥很快地下了肚。
我稍微松了口气,正要站起,封逸谦倏然痉挛了身子,哇的一声,刚下去的粥全部吐了出来。
“阿谦……”我收拾床上的狼藉,心疼地叫道。
封逸谦抓住我的手,止不住地咳嗽,缓了半晌的气,才说道:“宜笑,看来我是不行了。我预感到会有这么一天,没想到这么快,我娘在那边等着我……”
我呜咽道:“阿谦,我们不是说好再不分开吗?你要挺住,为了我,也为了我们的将来!”
封逸谦迷蒙地看着我,看得久了,粲然一笑,“是啊,我们的将来。我要活下去,宜笑,帮我活下去……”
帮他活下去。
救他,也就等于救自己。
医院,几乎都被我遗忘的名词,似是除了自己,这世上还没诞生的名词,突然地在我脑海迸出,深深扎入我的神经。
此时此刻,我清楚地明白,万不得已之际,我要动用我的第二枚玉珠了。
郎中来了。
果然,跟上次一样,郎中搭脉探舌之后,摇头道:“此病凶险。病人脉弱、四肢发冷、眼眶下陷,非一般之病啊!”
我回答道:“听太医说,此病叫消渴症。”
“消渴症?”郎中略加思忖,点头道,“略微听说过,此乃一大奇病啊。据说其为病之肇端,皆因酒色劳伤,多是富贵人家才得。”
我苦恼地说:“请郎中下药救人。”
郎中沙沙写了药方,交给晏老头,拱手道:“恕在下学医不精,此药只能缓和一时。病人气血皆已销铄,赶快另请高明吧。”
晏老头送郎中出门,我情知郎中话里多有隐藏,悄悄跟随出去。却见郎中站在门口与晏老头告辞,我隐约听到最后一句,顿感冷水浇顶,从头到脚凉透。
“此爷病势险恶,无力回春了。”
晏老头呆呆地站着。
我近到身后,含泪道:“大叔,请你照顾一下阿谦,我去想办法。”
晏老头转身看我,也是老泪纵横,“宜笑姑娘,你还有什么法子?郎中说,封少爷时日不多了。”
“不用告诉任何人,我两天后一定会回来。我一定要救阿谦!大叔,如果他问起我,就说我给他找药去了,要他务必等我回来!”
晏老头一瞬不瞬地直视着我,想看出我的心思端倪。我不想告诉他,只是投给他一个肯定的微笑。晏老头颔首示意,他说,他明白了。
就在那天夜里,我吻别了封逸谦,在他耳边细声低喃。我想,尽管他一直昏睡着,梦里一定听见我说的话。
“阿谦,等我。”
玉带河泛着青碧的波光,恍如封逸谦幽澈柔情的眼眸。我咽下了第二枚玉珠,感觉自己的身体在升腾,风声呼啸而过,接着,黑暗潮水般向我涌来。
安洲城,我回来了。
小巷深处,灯光幽暗。
一对男女醉醺醺地下来,看见我,笑得前仰后合。
“哈哈,唱戏的!”
待那对男女走后,出租司机从车内伸出头,好奇地问道:“小姐,要不要打车?”
我还在东张西望寻找自己家的位置,脑子尚未清醒,只是下意识地摇摇头。司机嘀咕了一句,调转车头走了。
我至今搞不清楚自己究竟离家多少日子。小巷也变了模样,沿巷开了几家店铺,顶棚几乎要伸到巷子中心。部分人家的墙面上,巨大的“拆”字还在,只是比以前淡了许多。
顺着记忆,我摸索着拐过小弄,前面就是我家了。
我从信箱底层摸到了家里的钥匙,做贼似地上了楼,费了不少劲儿才打开家门。我听见邻居田妈家有人咳嗽,慌忙将门关上了。
家里一切照旧,想是无人踏门一步,桌子上、橱柜上都积满了厚厚的灰尘。一只饿死的蟑螂横尸在厨房,风干了的模样。
我顾不了这些,先脱下身上的古衣,换上自己的衣服。正折腾着,有人在敲门,是田妈的声音。
“宜笑,是你吗?”
我赶紧应了一声,却不敢过去开门。田妈也在犹豫,说道:“这孩子,神神秘秘的。一走又是两年半……”
原来我又消失了两年半。
我心里一阵酸楚,极力控制自己的声音,装作很平静地应道:“田妈,我刚回家很累,想早歇了。有事明天再说,好吗?”
田妈也没勉强,关照了几句,就进了自己家。
我梳洗好自己,就开始翻找银行存折。存折是夹在书架上的,总算找着了,我抽出来,啪嗒,一本书也跟着翻落下来。
拾起一看,原来是冯大泉母亲写的《司鸿志》。经过这么一摔,后面的几页都脱了。我恍恍惚惚地翻了翻,定了定神,将脱落的几页小心地夹好,放到原来的位置。
存折里也就几千元,是我在中兴大酒店攒下的。
我枕着存折入睡,脑子里全是封逸谦不省人事的样子,眉心紧蹙,脸色苍白。
“宜笑,你在哪儿?别离开我……”
空茫的静夜里,仿佛听见他在唤我。我翻来覆去,泪水****了半个枕头。
好容易挨到天亮,我起来收拾好自己。正要出发,田妈又来敲门了。
田妈是给我送早点的。我打开门让她进来,她一见我,便大呼小叫道:“这孩子,怎么瘦成这样?天哪,你在外面可是遭什么罪了?”
我连忙掩饰过去,淡淡一笑,“也没什么事,就是忙了些。和朋友合伙做点小买卖,一日三餐就顾不上了。”
“苦命的孩子。”田妈感慨万千,又关心地问,“有没有男朋友了?你都二十三了,在外面跑,应该有个好男生照顾你。”
我愣了愣,还是摇了摇头。时光流逝,曾经莽撞倔强的黄毛丫头,眨眼间已经二十三岁了。
“我妈有没有回来过?”我故意岔开话题。
田妈说:“你妈还在康宁医院住着呢。上半年我随居委会几位姐妹去看过她,胖了,白了。脑子也清爽不少,看见我,还认得我。当时不知是谁提起了你,她还骂呢,说宜笑这丫头,算白养了,至今还没去看她。”
几句话说得我泪水在眼里打转,田妈见状,又安慰起我,“你也是为了你妈,冯老板花钱治你妈的病,你一定想早点还清这笔人情债。唉,都怨那个!”她突然想起来,说,“你那个父亲来过,打探你究竟去了哪儿?我可是一点都不知道,也不想多说。他给了我电话号码,说你一旦回来,马上告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