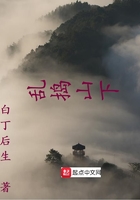他从拥挤的人群里看见父亲。他们围在出站口的铁栅栏门边,接客的,拉客的,大旅馆的服务员,小旅馆的老板和老板娘,开出租车的,蹬人力三轮的,骑电动摩托的,亲人、朋友和乞丐,父亲踮着脚,脖子越伸越长想从众多人头里冒出来,他的火车头棉帽子在昏暗的灯光下摇晃着十年前的光。这帽子是他硕士毕业后,工作第一年给父亲买的,他带父亲在商场里逛,想买一个时髦洋气的棉帽子,父亲看中的还是火车头栽绒帽,厚,重,戴在头上心里踏实。这个除夕夜,天不好,昏昏沉沉的不太平,随时可能飘下雪花。下车的人很多,他和老婆孩子从背光的通道里走出来,父亲无论把脚踮得多高都不可能看到他们。
父亲搓着手说:“回来了啊。”
“晚了半小时。”他说。
正常这趟车晚上九点到站,因为是普快,其实相当于慢车,见着像样的车都得让道,晚了半小时才到。父亲的脚踮了至少半小时。他发现三年不见,父亲又变矮了。
老婆叫一声:“爸。”
“冻坏了吧你们?今年冬天冷得邪乎。”父亲说,伸出手要抱一下孙子,“来,牛牛,给爷爷看看冻着了没有。”
孩子被老婆抱着,歪着小脑袋刚醒过来,对这个陌生的开阔世界还没回过神来。车站前的广场很大,寒风浩荡。几天前下了场大雪,一垛垛堆在广场边缘。白天化过雪的地方结了冰,经过的人颤颤巍巍。孩子看见一个陌生的老人向自己伸出手,吓得哇地哭起来。
“牛顿乖,不哭,”老婆颠着哄孩子,“爷爷就是想看看咱们宝贝牛顿。”
“牛——顿,”父亲为了这个转折一口气差点没接上来。“牛顿,爷爷就是看看你,那爷爷回家再抱你。不哭不哭。”
牛牛是当初父亲给孩子取的小名。父亲说,贱名好养,这名字听着身体就好,精神。都定了,临到孩子出生,他老婆不乐意了,牛牛?土死了!心眼歪的人没准会叫咱儿子“小鸡鸡”呢,不能叫。坚决不能叫。他熬了几个通宵终于想出了两全之策,叫“牛顿”。老婆才满意,跟巨人同名,这多敞亮。
他跟父亲说:“邻居有个孩子叫牛牛。就改牛顿了。”
“牛顿好。”父亲笑了笑,说,“这名字好。回家得跟你妈说说,她不知道牛顿是谁。牛顿不哭,爷爷这就带你坐车回家。”
父亲租了邻居的昌河面包车,开车的是邻居的儿子天北,他念大学那年这小子刚出生,小脸皱得像核桃。论辈分天北得叫他叔。来之前他跟父亲说,没必要租车,他直接打个车回去就行了,这么空车来再跑回去太折腾。父亲一定要来接,他说这几年变化大,县城变化大村里变化也大,河流填平了田地里建起了房子路也改道重修了,大晚上的,雪重路滑,你回来都摸不着家门。还带着媳妇和宝贝孙子,冻坏了可不行。那就接吧。他对回家的路的确没太大把握,头脑里的路都在太阳底下,不管拐多少个弯,总能明晃晃地从火车站通到家门口;那是三年前的路,乃至三年之前的很多年前的路,比如他在县二中念书的回家的路;现在从北京回老家的火车突然改到白天了,一大早从北京西站出发,晚上九点到县城,下了车他看到的只能是黑路。黑夜里他不敢确定能准确地走上正道。
变化很大,火车站这一带就很大。过去没这么多人在除夕夜回家,谁会赶着在团圆之前才往家赶?也没这么多人堵在出站口,都回家过年了,谁会放着年夜饭不吃跑这里冰天雪地地挣那几块钱?不是不缺钱,是这钱不能挣。大过年的,没钱也得好好过,都这么想。现在变了,鞭炮声已经远远近近地响起来,他们还围在这里想再赚一点儿。他觉得这是个好事,陈旧的脑袋瓜子终于开窍了。天北问父亲:
“爷,原路回?”
“原路。”父亲说,从副驾驶座上转过身,对他和媳妇说,“你们要不要看看县城?都变了。我也几年没来,路都不认识了。”
他看看老婆,牛顿又歪着脑袋睡了。老婆说:“看看你读书的中学吧,你总说有多好多好。”
“二中?”天北说,“叔,二中搬了,盖商场了。叔你想看老二中还是新二中?”
老婆说:“新的老的都想看。”
老婆比他小九岁,且不说年龄上和他基本上是两代人,就是性格,也看不出有多少相似处,很多观念和想法完全是两代人。她从小长在城市,独生子女,分不清麦苗和韭菜,算那种所谓的“八0后”。他第一次见到肯德基和麦当劳时,她已经吃腻了好多年了。乡村对她来说要么是美丽新世界,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要么就是万恶的旧社会,看哪里都觉得脏乱差,时刻准备哀民生之多艰。她对他过去的一切事情都感兴趣,那股劲儿和小时候她对她爸的历史满怀好奇大差不离。他想,那就看看吧,毕业以后再没去过。他经常想起母校,怀念那时候青葱勃发的年轻生活,但他就是没回去过。回到一个经常记忆的地方他总感到难为情,就像碰到一个念念不忘的故人一样让他难为情,说不清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