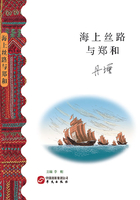下午五点刚过,正是下班时节,一辆拖着两节车厢的四路公共汽车开过来了。它像个怀孕的胖妇人,走进被革过命以后叫东风路的总府街,一步三摇,探头探脑,踟蹰爬行。穿过稠密的人丛,迈过成群结队的自行车,蹑手蹑脚绕开邮局期刊门市部门口鼓起来的那一砣兜售畅销书的黑市,小心谨慎地躲着126号市废旧物资公司寄卖行门口挤得水泄不通的买卖手表、录音机、原声磁带的自由交易市场,终于笨拙拙地站在文化宫车站上。
等车的人一窝蜂扑向前、中、后门,三道门立即吊着纵身跃上去的年轻小伙子。门下,人头黑压压一片,里三层是青年人、壮年人,外三层是不敢招战、只能互相挤挤靠靠的老弱妇幼……
车门“哧呼、哧呼”喘息着,吃力地向两边收缩,传来“快让”“哎哟”的尖叫。
中门挤开一条缝,现出一张老头惊慌的胖脸。他拼命地往后退靠,呼救地大叫“慢点、慢点挤”,招来上下一阵吆喝。他急中生智,翻转身踮起脚尖,抓住车门左侧扶手,双腿一曲,奇迹般悬吊起来,竟腾出一块空隙,车门“啪”地打开了。谁也没工夫注意这老头儿,车上的人山崩般跌滚到车下去,吓得外三层的爷爷奶奶闭上眼睛直呼“天啦”。不等人下完,车下的人早就按捺不住直往车上拥。越挤越把门堵得死,越是挤不上去。后面的人推着前面人的腰,前面的人拉开两肘,死死卡着后面的人,不准抢前半步……中门最后上车的是一个穿军便服的小伙子。他又高又壮,堵在门口像一扇门板,后面的人哪里挪得动!同时,他却显得过分热心地用肩膀抬前面那个一脚悬空的乘客的屁股。当售票员尖厉的“后面来车了”的喊声一起,穿军便服的小伙便纵身猛挤,连推带撞全身使劲。大张着嘴巴的车门“哗——”地紧贴他的背脊,总算闭上了。一截衣服夹在车外,像免战旗,宣告这场越栏、滚爬、推挤的“混战”暂时休战了……
“妈呀!”穿军便服的小伙突然一声吼叫。
原来,吊在扶手上的胖老头行李卷似的坠落下来,正落在小伙子跟前的缝隙里,脚没地方站,移又移不开。胖老头抱歉地:“嘻嘻,对不起!我买的吊票、嘻嘻……”
中门售票员位置上坐着个瘦老头,他慌忙站起身来拉胖老头:“来,从下面钻过来。”说着把背紧靠窗子,他太瘦,竟像剪纸般贴到了窗上。
胖老头试着挪动,可是棉衣里裹着一大堆肉,加之又挤,夹在缝缝里哪里动得了?只好昂着头连声说:“大爷,谢了!”
“我拉你嘛!”瘦老头伸出去的手还没缩回来,又伸出了另一只手。这种真诚和热心吸引了中门口的人,都把眼光转向他:皮帽下的白发、青筋鼓暴的手背上的寿斑表明他年过古稀了,但那种灵活敏捷却又富于壮年人的精力。他中气很足地说:“小伙子,搭个手,推一把。”
“算事!”穿军便服的小伙十分热情。
胖老头弥勒佛似的笑皱了脸,接二连三地说“谢了”。但突然,一脸笑纹全拉成“八”字,他身子往前一挺,下意识地低头看自己的衣袋:一只大手正慢慢伸进去。他本能地调头侧目,恰恰碰上穿军便服小伙那冷冷逼视的目光。他连忙眨眨眼,假装若无其事地转过脸。
这一切被瘦老头看得一清二楚,像犯了气管炎,他胸部急剧起伏着,嘴里烦躁地长吁短叹,终于忍不住咋呼道:“胖伙计,钻过来!”同时,意味深长地瞄着另一个紧靠扶手撑杆的、穿宇航服的小伙子,咄咄逼人地说:“中间很空,往里移嘛!堵在门口方便钳(钱)工么?”
穿宇航服的小伙傲慢地微微一笑,根本不屑看瘦老头似的。只见他扭动着猪儿虫般的身子,往中间踩了一脚。这一下,像松了榫头,人们的身子才可以摇晃了。胖老头趁势转过身,在军便服小伙的“帮助”下,从阶梯扶手下钻到了瘦老头的位置上。
没等胖老头坐稳,瘦老头就埋怨起来:“欺上脸了还不敢吭声,枉自长了百多斤肉!”
穿军便服的小伙冷冷一笑,用一副视而不见的神态打量瘦老头,然后拉拉帽檐,一个一百八十度转身,把脸朝门窗外,打了个尖利的呼哨。
胖老头平静地从脖子上取下围巾——那是一条乌糟糟的白布裹着棉花的代用品。他胡乱理一下,重新缠上,息事宁人地:“嘿嘿,他用我用都一样嘛!”
瘦老头惊讶地把头凑近胖老头:“你就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地做人?”
胖老头扯着围巾,不以为然地:“我有什么油水哟,连这个都换熬锅肉吃了!那皮包,空空的!”
瘦老头肝经火旺地擂一下车厢板,正要发作,汽车拐弯了。人们失去重心,发出一阵躁动:
“妈呀——踩着不硌脚么?”一个中年妇女推一掌前面的姑娘。
“小轿车不挤,你去坐嘛!”姑娘不用想一下,立即就回骂……
那边,一个穿海虎绒大衣的小媳妇使劲扭动肩膀:“靠着我干啥?我身上又没有皮包!”
“我有,还是大皮包哩!你来靠着我嘛!”小媳妇背后的眼镜汉子也不甘示弱。
“大家熄点火!”瘦老头大声劝解,“正是下班时间,是挤点。嗯,目前国家困难,汽车是少了点。嗯,再说造汽车哪有这几年娃娃生得快呢?嗯,克服、克——服……”
车内粗鲁、污秽的叫骂横飞,淹没了瘦老头的招呼声。见人们根本不听他的,他的忍耐到了限度,于是瞪着眼,伸直脖子,竭尽全力吼道:“看着斯斯文文的,张嘴就喷臭!这儿是猪圈还是牛棚?嗯?”咳嗽使他住了口。
“啧啧……”胖老头打了一长串啧啧,“尽都吃了火药么?哎呀!”
窃窃笑声像风吹散了汽车内的浊气。
汽车在中心菜市场前又一个拐弯,向人民东路驶去。要下车的慌慌张张往门口挤,不下车的拼命往里钻。乱哄哄中,穿军便服的小伙与人交换了位置。上完中门的三级阶梯,又转了两个三百六十度圈,窜到汽车中部的过道上,用一种没有表情的表情,注视穿宇航服的小伙子。瘦老头神不知鬼不觉地也站到过道上来,并且刚巧夹在两个小伙子的中间。正当汽车开始滑行,准备停车的时候,瘦老头猛地抓住穿军便服小伙的手,不动声色地喊:“拿出来!”
“你疯了!”那小伙凶神恶煞般吼起来。
瘦老头的手钳子般钳着他:“休想滑脱了!”
“吃多了,胀饱了,活得不耐烦了?”穿军便服的小伙虚张声势地狂吼着。
“耍腻了,骨头酥了,自在得不耐烦了?”猛刹车使满车晃荡一下,瘦老头边骂边对后门售票员喊了声,“别开门!”
售票员顺从地放下刚举起的手,做出一副超然的样子,嘟起嘴唇,“呼呼”地吹着自己额前那排整齐的刘海,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
瘦老头凑近穿军便服小伙的脸,厉声教训着:“以为还像‘四人帮’那阵,干坏事没人敢管?扰乱社会治安,破坏安全没有你的好下场!”唾沫星子飞溅着。
穿军便服的小伙被紧紧揪着,自感力薄,心开始虚了。只管闷声招架,两人扭成一团,在水泄不通的过道上揉面似的拉扯。
右边,穿海虎绒大衣的妇女六神无主,捏紧摩登皮包,胸一挺、腹一收,惊恐地一脚踩进座位前,几乎扑在坐着的姑娘身上;左边,戴眼镜的中年人手扶镜架,急忙后退,慌里慌张,接连踩了两个人的脚;前后的大姑娘、小伙子也各自寻找退路,生怕——可能怕血溅到自己身上。远处的人专注眼前的格斗,像看一部蹩脚的打斗影片,不哼,不喊,连眉也懒得皱。
争持了两分钟,穿军便服的小伙被捏痛得发出一声号叫,实在熬不过去了,他的目光迅速流过摇下玻璃的车窗,低声下气地乞求说:“钟大爷,你老人家松、松一把……”
“嘻嘻!你知道我是钟大爷!那,还想滑脱?”瘦老头发现自己小有威名,不免得意地仰起脸,眯缝着眼睛朝众人笑笑。
穿军便服的小伙趁机挣脱左手,扔下一个小塑料包。在钟大爷弓腰捡皮包的当儿,挤进中门边的座位,跨过胖老头的腿,翻出窗子,越过车下的人头,撞倒一个妇女,从人丛中冲过去,跳上街沿,夺路而逃。
几乎同时,中门大开,钟大爷高喊“抓住他”连滚带跌落下车去。可惜,车下的人不顾一切地拥向车门,挡了钟大爷的去路,转瞬间,穿军便服的小伙便逃之夭夭了。
钟大爷气急败坏地重新挤上车的时候,车内的人正热闹地议论着呢:
“跑得脱啥子,下面那么多人!一个吹他一口气,都把他‘抬’起来了!”
“现在的贼娃子太猖狂,三五结伙无法无天,公安局该狠狠打击……”
“去年,有个农民的老婆查出了血癌,他倾家荡产凑了一笔钱赶进城来。刚下火车就被偷得一干二净,气得他一头钻到汽车轮轮下,压断了脚。可怜乡下还有三个娃娃……”
人们七嘴八舌,唉声叹气,诅咒小偷,抱怨公安工作不力。
汽车刚起步,售票员急切地问:“钟大爷,抓到没有?”
人们“哗”地转过头,眼巴巴望着钟大爷,静静地期待回答。车内笼罩着一种神圣的气氛。
看到大家期待、信任的目光,钟大爷突然感到窘迫,羞怯。他低头嘟哝道:“人老了,是跑不赢小伙子了。”接着,举起手中的塑料皮包,抬头四顾,“谁的皮包?下车了?哎呀……”他焦急地翻看钱包,见钱不多,才安下心来。
“小偷怎么知道你是钟大爷呢?”海虎绒妇女有了安全感,兴趣来了。
“岂止知道!”钟大爷挺了挺腰,像个受了表扬的小学生,喜滋滋地摇晃着头,“他们那帮人,有恨我的,有怕我的,也有教育好了放出来找上门谢我的。退休以后我就当上义务治安员,跟那些失足娃娃打了十三年交道,凡是落到我手中,跑脱的是极少数……”
“可惜,今天的跑脱了!”一个穿得花里胡哨、留着长发的小伙子冷冰冰地戳了一句,他坐在车尾那排椅子上。
传来几声窃窃的笑。
“跑得脱初一,跑不脱十五嘛!”钟大爷才不在乎笑声里含着什么,自负地说。可是,当他看见说话的是那样一个青年,并触到那带商标的蛤蟆镜下冷冷嘲笑的神情,脸色陡然阴沉下来。他痛苦地半睁眼睛,半闭嘴巴,转瞬间就变得衰老、颓唐了。他移动迟钝的目光,环视车上的人,深深痛惜道,“今天,要是哪位同志帮我一把,搭上一只手,偷儿就跑不脱了。唉,也难怪呀,这些年颠来倒去,人的脑壳都搅木了……”
难堪的寂静。汽车引擎也屏声静气羞于出声一般。悄悄侧过的脸,尴尬的苦笑,惭愧垂下的眼皮,也有若无其事的顾盼,冷漠的目光。
“帮?要是捅我一刀呢?”
钟大爷看见说话的还是那个时髦过分的青年,火气冲到脑门上:“要捅,也先捅到我身上呀!我七十三岁的人都不怕嘛!”
“那当然,能活到你那个岁数,挨一刀当英雄,我也要干呢!”青年的话还没完,就招来几声带怒的吆喝。他鄙夷地撇撇嘴,把两臂趴到前排椅背上,吊儿郎当地吹起口哨来。
“看到你这种样子,我死得下去吗?死了也闭不上眼睛呀!”
“当真?不闭眼睛一定很好看。”青年慢吞吞地故意气钟大爷,“你死的时候要通知我一声呵。”
钟大爷嘴唇煞白,张开口说不出话来。
售票员狠狠地瞪一眼那青年人,急忙转脸安慰:“钟大爷,你下命令我就没开门,是不?好人有的是!”
钟大爷颤颤巍巍地点点头,这才缓过气来,可火气一时压不住,胸膛还在大起大伏。
“那么认真做啥子,现在的事情,咳!”胖老头恬淡地笑笑,摇头晃脑规劝,“反正,又没有偷到你名下。”
“怪不得!”钟大爷的火有了火山口,跳着脚申斥道,“贼从你眼皮子底下跑得脱,你!”
胖老头碰了一鼻子灰,阴阳怪气地说:“就算我说错了嘛!我又不吃这碗饭。”
一听认错,性情宽容的钟大爷心里的气先就消了一半:“嘿,你是吃什么饭的?”
“我?我为社会主义负了伤,休息二十多年了,我在吃安胎钱。”胖老头这句哗众取宠的话倒没引起什么反响,不过,那自鸣得意的神态却引来好些鄙视的眼光。他才不在乎什么眼光呢,继续说,“一大把年纪了,我不想自己找些虱子在身上爬!”
“自己找?”钟大爷朝胖老头轻蔑地哼哼,一种优越感悄悄爬上心头,“不是我吹,我们搬运公司退休千多人,只挑选了三百人!人家王干事亲自看了档案的,历史上有‘疤疤’的、成分孬的都不要。”他瞟一眼胖老头继续说,“只对熬锅肉感兴趣——表现不好的人也不得要——”突然,他哽咽一口,话被堵住了。汽车正横穿人民南路广场,他僵立着,呆呆地望着主席台的台阶,像是充满了某种莫名的思绪……
“说下去,说下去呀!”胖老头压着自己的火气,嬉皮笑脸地揶揄,“是在忆苦思甜了吧?莫非你当年就在这皇城坝卖打药,吃了上顿没下顿、一床破棉絮五个人盖……”
车上有捂着嘴的笑声,也有不满的嘘声……
钟大爷纹丝不动,目不斜视:“你呀,脸皮比城墙倒拐拐还厚,成了混世魔王了!”
“该我混!”胖老头感到人们的情绪倾向瘦老头了,忙大声表白,“我也光荣过的。大跃进那阵是全队的先进!现在我的腰杆、颈子的骨质增生就是从房架上摔下来造成的。我站不直了,要躺下去
才好受……”一种不自觉的潜在的哀愁,像尘埃样飞卷过来,蒙在心上,他蓦地缄默了。
“难怪!你的声音总像是从地底下升起来的。”一直静观的几个学生开始搭话。他们不懂得胖老头此刻心灵的颤动,酸不溜秋地嘲讽,“看不出来呢,你原先还亮过一阵。可是现在你熄灭了,你完了!”
善良的钟大爷挥挥手,想制止这种讥讽。
“什么完了!”胖老头把脖子一伸,恼怒地嘟着嘴,“你们称二两棉花去纺(访)一下,我们三公司二队谁不知道,我胖子热过、烫过、‘咕嘟、咕嘟’开过!”
车内爆发了一阵大笑。
“看你往哪儿跑!”钟大爷洪亮的喊声盖过了所有的笑声。
穿宇航服小伙的背对着钟大爷,神情异样地向着窗外。
目光从不同角度射向钟大爷。
钟大爷的右手把穿宇航服小伙捏紧的拳头举得高高的,那拳头里有一根长长的金属链子,一直连在钟大爷的腰上。
“钟大爷,怎么了?”穿宇航服小伙假装吃惊,可是他疼得松开手,众人眼见一样东西掉下去……
“以为怀表到手了?想杀我钟大爷的威风?哼!”钟大爷简直高兴得“老还小”了。
穿宇航服的小伙矜持地抿嘴笑着,不动声色,腿却偷偷地往旁边挪动。
戴眼镜的中年人扶扶镜框,瞅一眼穿海虎绒的妇女。两人完全忘记了刚上车时的谩骂,交换了一个会意的眼色,互相往拢一靠,刚刚顶住穿宇航服的小伙后退的脚。他狼狈地缩回脚,惊慌失措地回头一瞥,万万没想到,汽车才跑两站路,瘦老头这盘死棋就下活了!
钟大爷兴奋地向“眼镜”和“海虎绒”眨眨眼,滑稽地歪歪嘴,拉着穿宇航服的小伙那只手直摇晃:“这一回,你就长了翅膀也飞不了啦!快说,要软的还是要硬的?”
穿宇航服的小伙无可奈何地低下脑袋:“软的……”
钟大爷伸出他那双钳子般的手。前后左右的大姑娘、小伙子,同时伸出好几只手来,很快就将穿宇航服的小伙的手反剪到背上。
钟大爷忍俊不禁,大笑起来,笑得像青年、像孩子一样富有感染力:“亏得大家,三刨两爪就抓到了,光靠公安怎么行!”他转向胖老头,完全忘记了刚才受的讽刺、嘲笑和争执,诚恳地说,“其实我们都一样,都该管的,是不是呢,你说?”
胖老头皮笑肉不笑地张了张嘴,说不出什么,尴尬地调开脸。等汽车在人民西路停下,见钟大爷押着“宇航”小伙下了车,他才不服输地嘟哝道:“管?他又不是我的儿!”
钟大爷冲胖老头歪嘴一笑,他理解这种嘴犟的人,但还是严肃地说:“胖伙计,人心都是肉长的,看着被偷的人往汽车底下钻;看着这么敦敦笃笃的小伙子摔进泥坑坑,你就不知道心疼么?我不信!”说完,拂袖而去。
当钟大爷拖着疲惫的步子回家时,天已经漆黑了。老伴串门去了,他把热在铝锅里的饭菜端出来,把洗脸水倒进盆子,卷起了衣袖——
“嘟嘟!”一辆汽车气势汹汹地停在大门口,车门重重的撞击声显示自己背负公事。一个鸭青般的嗓子高喊:“钟大爷家有人吗?”
“有,有人。”钟大爷捧着热扑扑的洗脸帕,热心热肠跑到门口来。
“人停在哪儿的?嗯?”鸭青嗓绷着脸,昂起脖子。
“什么?”钟大爷摸不着头脑,谦恭地问。
鸭青嗓不耐烦地朝车上招招手,连看都不看一眼钟大爷:“我们来抬钟大爷!”
“抬我?”钟大爷莫明其妙地感到受宠若惊了。
鸭青嗓眨眨眼,直盯钟大爷,沉吟片刻,冷冰冰地说:“你?没死?你是活的?”
“我一直是活的呀!”钟大爷猛然明白了鸭青嗓的来意,愤怒地挥动着热气腾腾的毛巾,“活得很自在,活了七十三,还要活下去!还要活下去!”
“那,谁打来的电话?谁打来的电话?”
“你问那些贼娃子兄弟伙呀!”钟大爷见车边举着担架的两个人在窃窃发笑,气得吹胡子瞪眼睛,“呵,不管死人活人,你们只管往炉子里抬,好挣奖金呀!”
“我们不能白跑!按经济规律核算,这汽车费该你给!”鸭青嗓嘎嘎叫着。
“你把枕头垫高点想嘛!”钟大爷明知作怪的是那帮小偷,可哪个喊火葬场这个鸭青嗓碰上了呢!他又“老还小”了,他幸灾乐祸地笑着说,“活该!偷鸡不着倒蚀一把米。去法院告我嘛!”
围观的邻人笑开了。
隔壁赖大嫂双手往腰上一叉:“去找阎王爷,告钟大爷不交买路钱!”
钟大爷手一挥,拍拍胸自豪地说:“我们这儿尽都是活人,没你们火葬场的生意,快走!”
鸭青嗓发现自己上了当,自讨没趣,无可奈何地钻进驾驶室。喇叭怒气冲天吼两声,他把头伸到车窗外,抱怨道:“该死的贼娃子,害老子白跑一趟!”
钟大爷看着疾驰而去的汽车,猛然想起有句重要的话要说,忙踉跄几步疾呼道:“告诉那些贼娃子,我钟大爷就是死,在阴间也要逮贼娃子……”
1981年4月8日于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