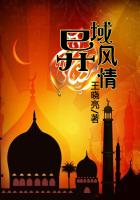在当局对整个空中图书馆的规划当中,最没有被严谨思考的一个环节应该是食物的环节。我们每天几乎都在吃同样的东西,这些东西塞满瓶瓶罐罐,份量大得好像生活在这儿的不是图书管理员,而是两头关在笼子里的野兽。而我们对付这种歧视的方法也很简单,把大部分食物埋在树根底下。树显然喜欢吃油腻的东西,因此它们的生长速度惊人,而我们消瘦的速度也同样惊人,以至于最后我们发现对方都伶俐得像猴子。而且,我们竟能迅速地在树上爬上爬下,不只是为了采摘水果,而是把坐在宽阔凉爽的树荫里看看落日或云层的变化当作一种休息。
坐在这里看云层可以让我们追忆在地球上看天空的样子。不过,地球人在云层的下面朝上看,我们却明白自己是在云层的上面朝下看。云端显然离我们更近,有时候它们就像洁白的大花一样突然开放,花瓣无限伸展,把我们包拢起来。我们被它托浮起来,感觉到这个小星球正在往远处漂移。这样像神仙一样过了一阵子,我惊觉羽翼消失了,自己浑身湿透地坐在树上。于是,我跳下树,对着飘走的云狠狠骂几句。
这些日子,图书馆里被我们整理得像一面光可鉴人的镜子。除了继续阅读小H抛过来的书,以及在意见分歧时故意大喊大叫地吵闹一番、以打破星球上的沉寂之外,我生活得就像个农夫、园丁或习惯在树上发呆的猴子。
在图书馆最里面、靠右边的第三个窗户下面,有一个小小的蓝色按钮,通过这个,我们可以和地球那边的联络员通话。我们谁也没有心情和那边通话。但这一天,我有点儿百无聊赖,希望和那边开个玩笑。我按下按钮,故作冷静地说:“这里是空中图书馆,给我们送一个女人来。”短暂而让人紧张的寂静之后,我听见一个像蜜蜂一样嗡嗡的声音说:“收到,收到。”接着又恢复了寂静。
热气球降临的那一天,我正坐在树下看书。是我看见那个东西越来越清晰,于是我大声呼喊小H,他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我们两个一起往停靠台那边跑去。气球降落了,一个穿得也像鼓囊囊的气球的女人从上面跳下来,她招呼我们去帮她拿行李 - 一个手提包和一个箱子。后来,她告诉我们,她是第一个被允许来到空中图书馆的参观者。我们的管理者已经决定开放空中图书馆给地球游客,大家都很兴奋,尤其是孩子们。至于为什么她是首位被批准的实验参观者,她很神气地说,这是因为她喜爱阅读,这个优势是别的申请人所不具备的。“在我的箱子里头就放了两本书,我旅行的时候总爱带着书。”
对于开放图书馆给地球游客这件事,我和小H只能生闷气。谁也没有通知我们,没有任何人问我们的意见,我们只是图书馆的看护者,从来都不是所有者。但这个女人的到来,多少冲淡了这种郁闷。
她的确爱阅读,但如果让她讲一下她读了什么,那必定是一团混乱。她好像故意东扯西拉,她具有把一个整体拆散,弄得七零八落、找不到头绪的本事。小H坚持说,这并不代表她没有体会到真意,这只是表达的问题。我则比较严厉,每当我听到她的那些凌乱描述时,我就忍不住露出笑意,我感到漫天飞舞着不知所终的羽毛,长的、短的、翅膀尖上的硬翎,屁股处的茸毛,黑色的、黄色的、绿色的、带有条纹和暗花的,鸟儿的、鸡们的、火鸡们的、鸵鸟们的……我只能头脑发晕地找个借口中途告退,留下小H目瞪口呆、迷茫而执着地继续聆听。一个极为有序的人就这样被极为混乱的人俘虏了。
但这个乘热气球降临的夏娃是迷人的,我虽然总在她的谈论中头痛退出,但我还是不断地去寻找重新聆听的折磨。她没有走的意思,我们就在图书馆的一角给她用几个书架围成一个临时的房间。
在这期间,小H依照他所构思的一套勾引女性的路线进行阅读。例如,他和她在一起时阅读的第一本书竟然是贾德?戴蒙的《枪炮、病菌和钢铁》。我想这个名字本身就非常雄性,带有某种暗示意味。小H告诉我选择此书的原因是,一开始不能露出任何锋芒,要选择中性的读物,色调刚硬,这本以生物学原理解读殖民历史的书带有恰到好处的、人类学的中性意味,不多也不少,足够显示一个人的博学兴趣,又不像哲学那样使人怀疑你故意掉书袋摆架子。小H说,一开始尤其不能选择诗歌,那会给人留下多愁善感又善变花心的初始印象。第二阶段,小H选择了小说,他说在证明了自己是个对各方面都感兴趣的求知者之后,也要恰当地表现出艺术和灵性的一面。但他绝不选择那些赫赫有名、过于经典的作品,尤其不能选那些描绘女性、催人泪下的小说,也绝对不能选择女性们不感兴趣的作家如君特格拉斯或曼。因此,他保持着低调姿态阅读的是一本出自名家的不怎么有名的作品 – 福楼拜的《三故事》。这本书必将引起夏娃的注意。在几本小说之后,他把手伸到了哲学书的书架上,但他绝对不先去碰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更要远离康德或罗素这种人,他只是随手翻看了一本尼采的不太为人所知的《朝霞》。当最终来到诗歌这一高潮部分时,他首先选择了亚力山卓,在一个沉闷午后的聊天中,他才无意中透露出自己曾熟读聂鲁达的情诗,还即兴朗诵了帕斯捷尔纳克那首至为感人的《屋子里不会再有人来……》。
小H成功了,其成功的收获就是总被置于满天凌乱的羽毛之下。女人们倾诉的欲望太强,甚至强过男人们对温柔的渴望。因此,在我看来,小H所面临的是一出悲剧。但这出悲剧已经使小H顾不上果树和池塘了。现在我的角色就是一个冷眼旁观的农夫和园丁。
但我的心里蒙着一层浓重的阴影。如果那个女人终究要离开这里,我的朋友也许会随她而去。这个地方剩下我一个人,我该离开还是留下来?地球游客的观光团就要到了,到时候这里可能变得热闹、拥挤、人声鼎沸,也许会有人愿意接替我们的位置,但这些书怎么办?这个世界真可怕,莫名奇妙被抛弃,人类还不如传说中的狗啊猫啊忠诚……我心里各种念头跌跌撞撞,像鸟群扑棱棱乱飞,我甚至想到也许结果是他们两个留下来,而我得出走,远离我的图书馆。
我开始冷淡地回避他们,但有时候怪念头突然冒出来,使我失去控制,跑去对他们恶毒地嘲讽一番。可我发现小H的态度也有一些变化。譬如,有时候当我正在对她说话的时候,他会假装不经意地离开。我不禁怀疑,他是否在策划什么新的追求花招。那天晚上,当我们在书架之间不期而遇时,我直接问了这个问题。
他有点儿尴尬地说:“我以为你也喜欢单独和她在一起。”我故意大声冷笑,然后低声把那个关于羽毛的可笑联想告诉他。我说:“我不需要你这方面的慷慨,如果我要追求她,那是我自己的事儿。你不要中福克纳老头的毒,念念不忘‘荣誉’。对待夏娃们,我会像于连学习,而不至于像于洛男爵那样让人丧气。”
小H虽然笑了,却显得心事重重。他说:“希望我们两个不会因为她而有什么误会,在我看来,这种友情比什么都重要。我这几天也在考虑……”
“如果三个人留下来会有一个多余人的话,你和她留下来是最好的办法。”我马上说。
“不行,我宁可是我们两个留下来。这个图书馆得由我们两个来保护,一直以来都是这样……不管因为什么,我都不会离开。有些东西会让你很快乐,但谁也不能什么都有,可能它也不是你想的那么重要,”他说着,把一叠选好的书递给我,“如果她要留下来,我绝不会再妨碍你们,我想过了。”
“但是,我也是这样想。”
“这不是分享的事儿,看她的选择,但我们不能因为她相互怀恨或是分开,这一点儿最重要。”
“你和我担心的东西一样。”我又说了一句。
“我不管你担心什么,”他激动地挥了一下手,“我们两个都必须在这儿。”
不知道是我们的矛盾被她发觉了,还是我们两个的刻意躲避、推让使夏娃恼怒,也或者她已经厌倦了这沉闷的地方。有一天,她收拾好行李,登上了她的气球。除了她带来的两本书外,她还带走了一本由我们共同赠送的图书馆藏书 – 《修道院纪事》,因为在她未来记忆里,这地方想必就像个修道院一样沉闷,我们两个就像僧人,这个名字至少能使她产生一点儿对这里的联想。我们在上面郑重签上名字,并注明书的出处 - “空中图书馆”。
当夏娃的热气球慢慢在视线中消失时,我们都暗自神伤。一个女人的离去能带走一个地方大部分的生机,安静得枯寂的生活又恢复了。我开始怀念那些漫天飞舞的羽毛,被我冷嘲热讽的颠三倒四,我满怀趣味的回味它,因为它而发笑。有时候,一个使你发笑的女人带来的快乐远超过那些仅仅令你垂涎其美色的女人,因为这种快乐不是短暂的,而是历久弥新;不是在你眼前闪动,而是储藏在心里。当快乐来到时,它就像一股泉水突然从心里迸出,流淌到你的全身各处,使每一块肌肉和每一根汗毛都得到甘甜。
但我们没有多久的时间沉浸怀念中,因为第一批地球观光客很快就光临了。当我们像两个酒店堂倌儿一样为他们推开图书馆的大门、并垂手立在两边观看他们鱼贯而入时,我们就知道新的灾难开始啦。
事实上,图书对他们来说和一叠白纸没有任何区别,他们的兴致是冲着这个悬在空中的球体来的,他们把这里当作带小畜牲们看新鲜的新型游乐场。但这些人显然把图书当成了此地唯一的纪念品,他们偷书、撕页,把这些东西带回地球向亲戚朋友炫耀,证明“老子到此一游”,毕竟地球上已很难见到书了。
当盗窃行为泛滥得难以容忍时,我们向管理部门要求安置防盗装置,但没想到这给图书馆带来了更大的麻烦。游客代表组织索性向管理部门提出申请,要求允许地球游客从空中图书馆借书,因为图书馆是属于大家的,纳税人的钱维持着它,它存在的意义就是向大家提供借书服务。他们赢了。于是,观光客堂而皇之地带走他们的“纪念品”,从此一去不返。我们又申请在地球上开辟一些书籍回收点,但这个申请被无限期搁置了。理由是,没有那么多地方和人力来管理书的事情。
每一次地球的观光客来,图书馆都要面临一次洗劫。他们把书带走了,我们知道很快这些书就会被丢弃。小H说,他们正在变相地销毁这座最后的图书馆,但这一次没有惨烈的销毁仪式所引发的同情,一切都合法地悄然进行,就像巨大的宝藏正经由一个看不见的漏洞被吸入一个深渊。这一次我们无计可施,彻底绝望。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最喜爱的书偷偷运送到我们的房间里,但做这件事也异常困难,当你选择把一套书藏起来就意味着留下另一些书面对永久失传的危险,这个时候不怎么让人好受。最后,我们的房间里堆满了杂乱无序的、高到屋顶的书,一旦倒塌,就会把人砸死。但我们深知,这些被抢救出来的书不及馆中书籍的万分之一。我们今天发现失去了整套的马基雅维里,三天后又遗失了黑格尔。然后,不可避免的,休谟、卢梭、马克斯?韦伯……观光客似乎特别喜欢装订精美厚重的古代思想家和历史学家的全套书 - 那种他们最不可能读的书,因为这些书足够分量,让他们感到不虚此行,反正他们能够托运回地球。
每个观光客都参与到销毁图书的游戏中来,来来往往、乐此不疲。痛苦不像打在头上的一记闷棍,而像那种古老的凌迟酷刑,一刀刀有节奏地割下去。这个小星球已经不属于我们,也不属于书籍,它是地球人最后的寻欢作乐场所。在地球伸出的枝杈之上的这片叶子上,孤独、洁净再也没法存活了,连果树也因为过多的垃圾而枯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