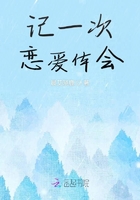第仆妄谓性命之理不可讲也,虽讲,人亦不能听也,虽听,人亦不能醒也,虽醒,人亦不能行也。所可得而共讲之,共醒之,共行之者,性命之作用,如诗书六艺而已。即诗书六艺,亦非徒列坐讲听。要唯一讲即教习。习至难处来问,方再与讲。讲之功有限,习之功无已。章人之岁月精神有限;诵说中度一日,便习行中错一日;纸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存学编》一,2)
所以他的《存学编》的宗旨只是要人明白“道不在诗书章句,学不在颖悟诵读,而期如孔门博文约礼,身实学之,身实习之,终身不懈”。
学习什么呢?《尚书》里的
六府:金,木,水,火,土,谷。
三事:正德,利用,厚生。
还有《周礼》里的
三物:六德,——智,仁,圣,义,忠,和。
六行,——孝,友,睦,姻,任,恤。
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这都是应学习的“物”。“格物”便是实地学习这些实物。格字如“手格猛兽”之格,格便是“犯手去做”。
这些六府六艺似乎太粗浅,故宋、明儒者鄙薄不为,偏要高谈性命之理。这正是魔道。颜元说:
学之亡也,亡其粗也。愿由粗以会其精。政之亡也,亡其迹也。愿崇迹以行其义。(《年谱》)
这真是重要的发明。宋、明儒者不甘淡薄,要同禅宗和尚争玄斗妙,故走上空虚的死路。救弊之道只在挽回风气,叫人注重那粗的浅的实迹。颜元又说:
孔子则只教人习事。迨见理于事,则已彻上彻下矣。(《存学编》)
宋儒的大病只是能静坐而不习事。朱子叙述他的先生李侗的生平,曾有一句话说:
先生居处有常,不作费力事。
这句话引起了颜元的大反对。颜元说:
只“不作费力事”五字,将有宋大儒皆状出矣。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天下事皆吾儒分内事。儒者不费力,谁费力乎?夫讲读著述以明理,静坐主敬以养性,不肯作一费力事,虽日口谈仁义,称述孔孟,其与释老之相去也几何?(《存学编》二,13)
用“不作费力事”一个标准,来比较“犯手去做”的一个标准,我们便可以明白颜学与理学的根本大分别了。
颜元的思想很简单,很浅近。因为他痛恨那故意作玄谈的理学家,
谈天论性,聪明者如打诨猜拳,愚浊者如捉风听梦,各自以为孔、颜复出矣。(《存学编》一,1)
他也论“性”,但他只老老实实地承认性即是这个气质之性。
譬之目矣,光明之理固是天命,眶疱睛皆是天命。更不必分何者是天命之性,何者是气质之性。(《存性编》)
这便是一笔勾销了五百年的烂账,何等痛快!
人性不过如此,最重要的是教育,而教育的方法只是实习实做那有用的实事实物。颜元是个医生,故用学医作比喻:
譬之于医。《黄帝》、《素问》、《金匮》、《玉函》,所以明医理也。而疗疾救世则必诊脉,制药,针灸,摩砭为之力也。今有妄人者,止务览医书千百卷,熟读详说,以为予国手矣;视诊脉制药针灸摩砭,以为术家之粗,不足学也。书日博,识日精,一人倡之,举世效之。岐黄盈天下,而天下之人病相枕,死相接也。可谓明医乎?
愚以为从事方脉,药饵,针灸,摩砭,疗疾救世者,所以为医也。读书,取以明此也。若读尽医书而鄙视方脉,药饵,针灸,摩砭,妄人也。不惟非岐黄,并非医也。尚不如习一科,验一方者之为医也。读尽天下书而不习行六府六艺,文人也,非儒也;尚不如行一节,精一艺者之为儒也。(《存学编》一,10)
他在别处又用学琴作比喻:
以读经史。订群书为穷理处事以求道之功,则相隔千里。以读经史,订群书为即穷理处事,曰道在是焉,则相隔万里矣。
譬之学琴然。诗书犹琴谱也。烂熟琴谱,讲解分明,可谓学琴乎?故曰以讲读为求道之功相隔千里也。
更有一妄人,指琴谱曰,“是即琴也。辨音律,协声韵,理性情,通神明,此物此事也。”谱果琴乎?故曰以书为道,相隔万里也。
歌得其调,抚娴其指,弦求中音,徵求中节,声求协律,是谓之学琴矣,未为习琴也。手随心,音随手,清浊疾徐有常规,鼓有常功,奏有常乐,是之谓习琴矣,未为能琴也。弦器可手制也,音律可耳审也,诗歌惟其所欲也,心与手忘,手与弦忘,私欲不作于心,太和常在于室,感应阴阳,化物达天,于是乎命之曰能琴。今手不弹,心不会,但以讲读琴谱为学琴,是渡河而望江也。故曰千里也。今目不睹,耳不闻,但以谱为琴,是指蓟北而谈云南也。故曰万里也。(《存学编》三,6至7)
这种说法,初看似很粗浅,其实很透辟。如王阳明说“良知”,岂不很好听?但良知若作“不学而知”解,则至多不过是一些“本能”,决不能做是非的准则。良知若作“直觉”的知识解,若真能“是便知是,非便知非”,那样的知识决不是不学而知的,乃是实学实习,日积月累的结果。譬如那弹琴的,到了那“心与手忘,手与弦忘”的地步,随心所欲便成曲调,那便成了直觉的知识。又如诗人画家,烂醉之后,兴至神来,也能随意成杰作,这也成了直觉的知识。然而这种境地都是实习功久的结果,是最后的功夫,而不是不学而知,不学而能的呵。
又如阳明说“知行合一”,岂不也很好听?但空谈知行合一,不从实习实行里出来,那里会有知行合一!如医生之诊病开方,疗伤止痛,那便是知行合一。如弹琴的得心应手,那才是知行合一。书本上的知识,口头的话柄,决不会做到知行合一的。宋人语录说:
明道谓谢显道曰,“尔辈在此相从,只是学某言语,故其学心与口不相应。盍若行之?”请问焉,曰:“且静坐。”
学者问如何行,先生却只教他静坐,静坐便能教人心口相应,知行合一了吗?颜元的批评最好:
因先生只说话,故弟子只学说话。心口且不相应,况身乎?况家国天下乎?措之事业,其不相应者多矣。
吾尝谈天,道性命,若无甚扞格。一著手算九九数,辄差。以此知心中醒,口中说,纸上作,不从身上习过,皆无用也。(《存学编》二,1)
这是颜、李学派的实习主义(Pragmatism)。
四戴震(东原,生1724,死1777)
十七八世纪是个反理学的时期。第一流的思想家大抵都鄙弃那谈心说性的理学。风气所趋,遂成了一个“朴学”时代,大家都不讲哲学了。“朴学”的风气最盛于十八世纪,延长到十九世纪的中叶。“朴学”是做“实事求是”的工夫,用证据作基础,考订一切古文化。其实这是一个史学的运动,是中国古文化的新研究,可算是中国的“文艺复兴”(Renaissance)时代。这个时期的细目有下列各方面:
(1)语言学(Philology),包括古音的研究,文字的假借变迁等等。
(2)训诂学(Semantics),用科学的方法,客观的证据,考定古书文字的意义。
(3)校勘学(Textual Criticism),搜求古本,比较异同,校正古书文字的错误。
(4)考订学(Higher Criticism),考定古书的真伪,著者的事迹等等。
(5)古物学(Archaeology),搜求古物,供历史的考证。
这个大运动,又叫做“汉学”,因为这时代的学者信汉儒“去古未远”,故崇信汉人过于宋学。又叫做“郑学”,因为郑玄是汉代的大师。但“朴学”一个名词似乎最妥当一点。
这个运动的特色是没有组织大哲学系统的野心,人人研究他的小问题,做专门的研究:或专治一部书(如《说文》),或专做一件事(如辑佚书),或专研究一个小题目(如《释绘》),这个时代的风气是逃虚就实,宁可做细碎的小问题,不肯妄想组成空虚的哲学系统。
但这个时代也有人感觉不满意。如章学诚(实斋)便说这时代的学者只有功力,而没有理解,终身做细碎的工作,而不能做贯串的思想,如蚕食叶而不吐丝。
其时有大思想家戴震出来,用当时学者考证的方法,历史的眼光,重新估定五百年的理学的价值,打倒旧的理学,而建立新的理学。是为近世哲学的中兴。
戴震是徽州休宁人。少年时,曾从婺源江永受学,江永是经学大师,精通算学,又长于音韵之学,又研究程、朱理学。在这几方面,戴震都有很精深的研究。他是一个举人,但负一时的盛名,受当世学者的推重。壮年以后,他往来南北各省,著作甚多。乾隆三十八年(1773)开四库全书馆,他被召为纂修,赐同进士出身,授庶吉士。他死时(1777)只有五十五岁。他的《戴氏遗书》,有微波榭刻本。其中最重要的哲学著作是他的《孟子字义疏证》。此书初稿本名《绪言》,现有《粤雅堂丛书》本可以考见初稿的状态,但当时是个轻视哲学的时代,他终不敢用这样一个大胆的书名,故他后来修正此书时,竟改为《孟子字义疏证》,——表面上是一部讲经学的书,其实是一部哲学书(参看胡适校读本,附在他的《戴东原的哲学》之后,商务印书馆出版)。
我曾指出理学的两条路子,即程颐说的:
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
程、朱一派走上了格物致知的大路,但终丢不了中古遗留下来的那一点宗教的态度,就是主敬的态度,他们主张静坐,主张省察“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是何气象”,主张无欲,都属于这个主敬的方面,都只是中古宗教的遗毒。因为他们都不肯抛弃这条宗教的路,故他们始终不能彻底地走那条格物致知的路。万一静坐主敬可以得到圣人的境界,又何必终身勤苦去格物致知呢?
颜元、李塨终身攻击程、朱的主静主敬,然而颜、李每日自己记功记过,“存理去欲”,做那“小心翼翼,昭事上帝”的工夫,其实还是那“主敬”的态度。相传李塨日记上有“昨夜与老妻敦伦一次”的话,此言虽无确据,然颜元自定功过格里确有“不为子嗣比内”的大过(《年谱》,《畿辅丛书》本,下,页十)。他们尽管要推翻理学,其实还脱不了理学先生的陋相。
戴震生在朴学最盛的时代,他是个很能实行致知格物的工夫的大学者,所以他一眼看破程、朱一派的根本缺点在于走错了路,在于不肯抛弃那条中古宗教的路。他说:
程子、朱子……详于论敬而略于论学(《疏证》十四)。
为什么程、朱有这根本大病呢?因为他们不曾抛弃中古宗教留下来的谬见。戴震说:
人物以类区分。人与人较,其材质等差凡几?古贤圣知人之材质有等差,是以重学问,贵扩充。老、庄、释氏谓有生皆同,故主于去情欲以勿害之,不必问学以扩充之。
在老、庄、释氏既守己自足矣,因毁訾仁义以伸其说。陆子静、王文成诸人向于老、庄、释氏,而改其毁訾仁义者以为自然全乎仁义,巧于伸其说者也。
程子、朱子尊“理”而以为天与我,谓理为形气所污坏,是圣人以下形气皆大不美,而其所谓“理”别为凑泊附著之一物,犹老、庄、释氏所谓“真宰”、“真空”之凑泊附着于形体也。理既完全自足,难于言学以明理,故不得不分理气为二本,而咎形气。盖其说杂糅傅合而成,令学者眩惑于其中。
理为形气所污坏,故学焉“以复其初”。“复其初”之云,见庄周书。(《庄子·缮性》篇)盖其所谓“理”,即如释氏所谓“本来面目”。而其所谓“存理”,亦即如释氏所谓“常惺惺”。(《疏证》十四)
他认清了理学的病根在于不肯抛弃那反人情性的中古宗教态度,在于尊理而咎形气,存理而去欲,故他的新理学只是并力推翻那“杂糅傅合”的,半宗教半玄学的旧理学。旧理学盲目的推崇“理”,认为“天理”,认为“得于天而具于心”,故无论如何口头推崇格物致知,结果终走上主静主敬的宗教路上去,终舍不掉那“复其初”的捷径。旧理学崇理而咎欲,故生出许多不近人情的,甚至于吃人的礼教。一切病根在于分理气为二元与分理欲为二元。故戴震的新理学只从推翻这种二元论下手。
他的宇宙观便否认向来的理气二元论:
一阴一阳,流行不已,夫是之为道而已。(《疏证》十七)
他说:
“道”犹行也。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疏证》十六)
阴阳即是气化的两个方面,五行只是五种气化流行,“行”即道也。
他论“性”,也否认理气二元。性只是气质之性。他以为古书论性的话,最好的是《大戴礼》的分于道谓之命,形于一谓之性。
道即是阴阳五行;“分于阴阳五行以有人物,而人物各限于所分以成其性。阴阳五行,道之实体也。血气心知,性之实体也。”(《疏证》十六)
这是很明白的唯物论(Materialism),宇宙只是气化的流行。阴阳五行的自然配合,由于分配的不同,而成为人物种种不同。性只是“分于阴阳五行以为血气心知”。血气固是阴阳五行的配合,心知也是阴阳五行的配合。这不是唯物论吗?这里面正用不着勉强拉出一个“理”或“天理”来“凑泊附着以为性”。于是六百年的理学的天论与性论也都用不着了。
他是主张“性善”的,但他的根据也只是说人的知觉,高于禽兽,故说人性是善的。
性者,飞潜动植之通名。性善者,论人之性也。人以有礼义,异于禽兽,实人之知觉,大远乎物,则然。(二十七)
这样看来,说人性善,不过是等于说人的知觉比禽兽高一点。人性有三大部分:欲,情,知。三者之中,知最重要。
惟有欲有情而又有知,然后欲得遂也,情得达也。(三十)
情与欲也是性,不当排斥。
喜怒哀乐,爱隐感念,愠懆怨愤,恐悸虑叹,饮食男女,郁悠戚咨,惨舒好恶之情,胥成性则然,是故谓之道。(《原善》中)
他又说:
凡出于欲,无非以生以养之事。天下必无舍生养之道而得存者。凡事为皆有于欲,无欲则无为矣,有为而归于至当不易之谓理,无欲无为,又焉有理?(《疏证》四十三)
这是反对向来理学家的无欲论。他说:
使饮食男女与夫感于物而动者,脱然无之,以归于静,归于一,又焉〔有恻隐〕,有羞恶,有辞让,有是非?此可以明仁义礼智非他,不过怀生畏死,饮食男女,与夫感于物而动者之皆不可脱然无之,以归于静,归于一;而恃人之心知异于禽兽,能不惑乎所行,即为懿德耳。古圣贤所谓“仁义礼智”,不求于所谓“欲”之外,不离乎血气心知。(二十一)
这是很大胆的思想。性即是血气心知,其中有欲,有情,有知觉;因为有情有欲,故有生养之道,故有事业,有道德。心知的作用,使人不惑于所行,不糊涂做去,便是美德;使行为归于至当,便是理。道德不在情欲之外,理即在事为之中。
这种思想同旧日的理学家的主张很有根本的不同。朱子曾说:
理在人心,是谓之性……性便是许多道理,得之天而具于心者。
理学家先假定一个浑然整个的天理,散为万物;理附着于气质之上,便是人性。他们自以为“性”里面具有“许多道理”,他们误认“性即是理在人心”,故人人自信有天理。于是你静坐冥想出来的,也自命为天理;他读书附会出来的,也自命为天理。人人都可以把他自己的私见,偏见,认作天理。“公有公的道理,婆有婆的道理。”人人拿他的“天理”来压迫别人,你不服从他,他就责你“不讲理”!
戴震最痛恨这种思想,他说这种态度的结果必至于“以理杀人”。他说:
六经孔孟之言,以及传记群籍,“理”字不多见。今虽至愚之人,悖戾恣睢,其处断一事,责诘一人,莫不辄曰“理”者,自宋以来始相习成俗,则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因以心之意见当之也。于是负其气,挟其势位,加以口给者,理伸;力弱气慑,口不能道辞者,理屈。呜呼!其孰谓以此制事,以此制人之非理哉?
昔人知在己之意见不可以“理”名,而今人轻言之。夫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未有不以意见当之者也。(五)
以意见为“理”,必至于“以理杀人”。
呜呼!今之人其亦弗思矣!圣人之道使天下无不达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文集·与某书》)
怎么叫做“以理杀人”呢?例如程子说:
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