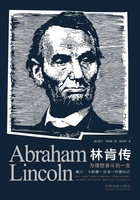九、齐璞,1987年5月29日作古。如裴世五大哥,我们也是因同乡而相识。他长于我一岁或两岁,可是在小学不同学。印象是最初相见,他已经是药王庙小学的教师。其后他入了警务学校,毕业后先在铁路的魏善庄站工作,然后到天津,仍在警界,解放后受了些处分,改为到中学教语文课。由他教小学时期算起,半个世纪以上,我们虽不住在一地,来往却很多。他性格严谨,好文,重交谊,尊重我,视我为第一知己。晚岁,他健康不佳,心境也不好,就更希望同我会面,多谈谈。可是我忙,只能秋天去天津一次,中秋(他这一天生日)的中午在他家共酒饭。已成惯例,这一天上午,我们夫妇由小花园步行一段路,向右拐入唐山道,必远远看见他拄杖站在门口,向街口瞭望。午后辞别时也一样,到街口我们向左拐,他还是站在门口看着。他走了,想到他瞑目前的心境,我未能在他跟前,无论为他想还是为我想,都是无法补偿的遗憾。
十、杨功勋,1988年8月24日作古。怀念的这些人里,只有他,是我在堂上讲、他在堂下听认识的。那是1936年暑后,我在进德中学为人代课,至多一个月吧,建立了师生关系。其时我自然不记得他,后来仍是不记得,以何因缘就有了来往。他是山西洪洞县人,具有山西人的地域特性,细致稳重,保守少变,因而敬我为师长,数十年如一日。其实我长于他至多只是十岁,既然他执弟子礼甚恭,我也就只能待之如半友。他也读书,但文的方面先天后天都不高,所以如其先君,走了货殖的路。知道我穷苦,有好的入口腹之物,如山西醋、陈年酒之类,必尽先给我。近些年来,我们老夫妇倚老卖老,每到老伴的诞辰(我的算做附庸,合并到一天),家里就聚餐一次,至时他们夫妇必登门,提着寿桃之类,举杯前行礼如仪,祝寿。自他走后,至时家里人仍聚餐,就不再有行礼如仪之事了。他在世时,常同我谈及洪洞县的旧事,大槐树和苏三监狱之类。不久前我去看,在洪洞宾馆举杯时想到他,不由得悲从中来,心里说,真想不到,他却先走了,不能陪我在他熟悉的地方转转,如果他有知,也会落泪吧。
十一、刘慎之,1991年4月12日作古。他辞世后,我曾以“刘慎之”为题,写了他(收入《负暄三话》)。我怀念他,主要是因为:一、性格温厚,像他这样的,世间稀有;二、视我为《后汉书·范式传》中说的“死友”,我们心中都怀有深深的知遇之情。他受家教,通国学,不像我,诌打油诗,说“何如新择术,巷口卖西瓜”,却未能改行。他是真改了行,解放后成为花木工人。可惜是天不假以健康,内脏多病,而且逐渐加重,入80年代,就只能闭门坐斗室或卧斗室,服药,希望下降不过速了。记得是80年代末,他住在前门外华仁路他的长女家养病,我们夫妇曾去看他一次。不久他迁回他的住处,新街口外文慧北园,我还常常想到他,只是因为忙,又无代步,就未能去看他。直到他作古之后,问他家里人病危时的情况,才知道常说,就是想我。他仍视我为“死友”,我却未能,至少是素车白马,送他走,几年来每一想到,就为愧对这样一位“死友”而痛心。
十二、韩文佑,1991年7月24日作古。他长于我一年有半,就年岁说是货真价实的兄长,可是换为看品德和学识,我应该称他为师长。我们是在天津南开中学结识的,多有来往是1936年夏回到北京以后。共书,共酒,共苦乐,共是非,至少是心情上,成为同生共死的朋友。50年代前期,他调往天津师范学院(后改为河北大学)任教,来往不能如以前那样多了,可是韩伯母仍旧住在北京,他有时要来探亲,我天津亲友多,有时要到那里去,来来往往,就仍旧可以聚会,饮白酒,为半日之谈。文化大革命时期,韩伯母病逝,我们二人恭送往东郊平房火葬场火化,他回天津就以莫须有的特务嫌疑被赶入牛棚。大革命之后,如许多牛棚中人,又经一次解放,名誉恢复,可是健康却一去而不复返,也就不再到北京来。
幸而我还能挤公交车,至少每年的中秋要到天津住几天,也就一定要去看他,比如中午到,总要次日走,为的是能够挑灯夜话。这样的聚会,最后一次是1988年10月,也是住一夜,挑灯夜话。其时他的身体已经很不行,秋风送爽之后就不敢下楼,因为一着凉就感冒,一感冒就要输氧。他住在南开区的西湖村,记得是住一夜的次日上午,我们夫妇辞出,往南,行由径,入天津大学去看倪表弟。他们夫妇送到天津大学界,我们走出很远,回头看,他们还是在那里站着。没想到这就是最后一面。此后我们就没有再到天津去,因为他走了,就不再有勇气在南开一带徘徊。如何悼念他呢?写,想到他的品德和学识,我们的情谊,感到太难,所以直到一年之后才完篇。写完,念念,觉得很不够,力止于此,也就勉强收入《负暄三话》,希望对我还能起些鞭策作用,即处顺境的时候不敢忘其所以是也。
最后写加说的一位,杨沫,她小于我将近五年,于1995年12月2日作古,反而比我先走了,也可以说是意外吧。过了二十天,即同年同月的22日下午,在八宝山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我未参加。相识的,不相识的,不少人,有闲心在这类事情上寻根索隐,希望我说说不参加的理由。我本打算沉默到底的,继而想,写回想录之类,应该以真面目见人,又,就说是小人物(指我自己)吧,关于史迹,能多真总是好的,所以决定到最后破一次例,说说。而人事,也如河道之有源有流,欲明其究竟,就不能不从源头说起。时间长,为避免繁琐,尽量简化。
站在最前的是合和分。合是常,分是变,好事者更想听的大概是变。可是变会带来伤痕,触及难免不舒适。又关于致伤的来由,前面“婚事”一题里已大致表过,所以这里从略。
其后是抗战时期,我们天各一方,断了音问。解放以后,她回到北京,我们见过几面。50年代,她写了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主观,她怎么想的,我不知道;客观,看(书及电影)的人都以为其中丑化的余某是指我。我未在意,因为:一、我一生总是认为自己缺点很多,受些咒骂正是应该;二、她当面向我解释,小说是小说,不该当做历史看。听到她的解释,我没说什么,只是心里想,如果我写小说,我不会这样做。
文化大革命中外调风正盛的时候,是北京市文联吧,来人调查她。依通例,是希望我说坏话,四堂会审,威吓,辱骂,让我照他们要求的说。其实这一套恶作剧我看惯了,心里报之以冷笑,嘴里仍是合情合理。最后黔驴技穷,让我写材料,我仍是说,她直爽,热情,有济世救民的理想,并且有求其实现的魄力。这材料,后来她看见了,曾给我来信,说想不到我还说她的好话,对于我的公正表示钦佩。可见她是以为我会怀恨在心的。我笑了笑,心里说,原来我们并不相知。
但对人,尤其曾经朝夕与共的,有恩怨,应该多记恩,少记怨。直到90年代初,有关我们之间的事,我都是这样对待的。所以80年代前期,我写忆旧的小文,其中《沙滩的住》(收入《负暄琐话》)末尾曾引《世说新语》“木犹如此,人何以堪”的话,以表示怀念。
70年代末,我们的唯一的女儿与我有了来往,连带的我们的交往也就增多。都是她主动,因为她是名人,扯着名人,尤其女名人的裤脚,以求自己的声名能够升级,我是羞于做的。她像是也没忘旧,比如送我照片,新拍的几张之中,夹一张我们未分时期的,并且说明,因为只有一张,是翻拍的。
是80年代后期,有个我原来并不认识的人写了一篇谈她早年感情生活的文章,触及上面提到的伤痕,她怀疑是我主使,一再著文申辩,主旨是我负心,可憎,她才离开我。这些文本,都是关心我的人送来,我看了。我沉默,因为:一、对于斗争我一向缺少兴趣;二、我不愿意为闲情难忍的人供应谈资;三、她仍然以为我心中有恨,所以寻找机会报复,这是把她自己看做我的对立面,移到我的眼里,她是失之把自己看得太重了。
但就是这样,我还是淡然视之。她像是也没把这类扬己的文章深印于心。比如90年代初,我的一本拙作《禅外说禅》出版,她还让女儿来要。记得我给她一本,扉页上还题了“共参之”一类的话。
其后过了有两年吧,又有好心人送来她的新著,曰《青蓝园》。是回想录性质,其中写了她的先后三个爱人。我大致看了看,感到很意外,是怎么也想不到,写前两个(第三个不知为不知)仍然用小说笔法。为了浮名竟至于这样,使我不能不想到品德问题。有人劝我也写几句,我仍然不改沉默的旧家风,说既无精力又无兴趣。可是心里有些凄苦,是感到有所失,失了什么?是她不再是,或早已不再是昔日的她。我也有所变,是有一次,写《惟闻钟磬音》,真成为“随笔”,竟溜出这样几句:“如有人以我的面皮为原料,制成香粉,往脸上擦,并招摇过市,我也决不尾随其后,说那白和香都是加过工的,本色并不如是。”
至此,具慧目的读者必已看出,她走了,我不会去恭送。但这里还想加细说说。是遗体告别仪式的头一天晚上,吴祖光先生来电话,问我参加不参加。我说不参加,因为没接到通知。其实内情不如此简单,且听后话。是仪式之后,我接到女儿的信,主旨是生时的恩恩怨怨,人已故去,就都谅解了吧。我复信说,人在时,我沉默,人已去,我更不会说什么。但是对女儿更应该以诚相见,所以信里也说了“思想感情都距离太远”的话。所谓思想距离远,主要是指她走信的路,我走疑的路,道不同,就只能不相为谋了。至于感情,——不说也罢。回到本题,说告别。我的想法,参加有两种来由,或情牵,或敬重,也可兼而有之。对于她,两者都没有。而又想仍是以诚相见,所以这“一死一生”的最后一面,我还是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