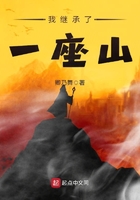关于沙袖肚子里尚未成形的孩子,他们俩发生了争执。一明觉得极其别扭,这不是自己的地里被别人抢先下了种那么简单。这种子是一个人,它有朝一日要来到这个世界上,和自己生活在一间屋子里,和他面对面坐在一个饭桌前吃饭。他不能想像,如同不能想像边红旗每天都要在他们的生活里插一杠子一样,那个孩子的眼里闪动的是边红旗的目光。他要沙袖做掉。
沙袖一度答应的,但是后来又变卦了。变卦的原因我不是很清楚,好像是一个女人打电话来,找一明,听口气跟一明很熟,而且不是一般的熟。不知道是不是沙袖太过敏了,要么就是那个开宝马的白领打的。总之那个女人的声音改变了沙袖的决定,我听到她挂电话的声音,简直是摔。听到动静我从房间里出来,她站在电话旁边,手按在上面,人在抖。
“做掉,”一明还在坚持。
“不,”沙袖脸转到一边。“这孩子是我的。”
“可它不是我的!”
“是,它不是你的。有什么是你的?”沙袖的声音十分悲凉。
“做掉!”
“我不做。”
一明的决定无效,那个可耻的小东西不在他身体里。一明受不了沙袖的绝决,彻底垮了,他蹲下来的样子像个囚犯,捶脑袋揪头发都干。他不坐沙发,就蹲着,或者坐在地板上,烟头扔了一地。我打扫卫生时,在沙发前扫出了很多头发,他的头发本来就不景气,现在更荒凉了。他们为此争论了两天,沙袖坚决不让步。她说:“你怎么说我都可以,怎么做也都可以。我只要这个孩子。”
一明一气,在中午衣衫不整地离开家,然后就没回来。晚上也没回来,打他的手机不通,总说关机。第二天还如此。沙袖打电话问他的导师和同门师兄弟,也没人知道他的下落。我们都急了,四处找,把北京能找的地方都找了,就差打110和登寻人启事了。我们在外面跑了三天,回来后都很疲劳,尤其是沙袖,这些天她的休息和饮食都成问题,站在公交车人都在抖。她老是问我,一明会到哪儿去呢?我说没问题,他不会丢了的,这么大的人了,一时想不通是正常的,不要担心。沙袖就说,他烦我了。我劝她不要瞎想,一明不是这样的人。晚上我随便吃了一点东西就睡下了。半夜里起来上厕所,看到沙袖房间里的灯还在亮,我轻轻地敲了几下门,门开了。沙袖还没睡,床上摊了一堆衣服。
“你在干吗?”这阵势我看不明白。
“我回香野地去,我走了他就会回来了。”
“不行,”我夺下她的箱子,“你就这么走了不是让他更担心?”
“可我真是想要这个孩子,”沙袖说,坐到床上捂住脸,这么多天第一次哭出来。“我知道我配不上他。我什么都没有了,一想到还有个孩子在我身体里,我才觉得我还有点东西是自己的。你知道吗,我在这里总觉得飘着,脚不着地,它让我实在一点。你不会明白的。”
我的确没法真正体会到她的感受,我不知道一个尚未成形的孩子对母亲和沙袖这样的女孩意味着什么。可是我得阻止她继续收拾,他们的事情是要他们自己解决,但也应该等一明回来再说。第二天我早早就醒来了,睁开眼就想一明会去哪,突然想起了香野地,赶快爬起来找沙袖。她已经起床了,正坐在椅子上发呆。
“一明是不是回老家了?”
“没回。他走的第二天我就打过电话了。”
“要不再问问,都几天了。有病只能乱求医了。”
沙袖又打电话。
一明果然在香野地。沙袖的母亲在电话里说,一明两天前回的老家。他说很久没有回来了,要给父母烧几刀火纸。她又问沙袖,是不是吵架了?一明回来时头发乱糟糟的,精神也不好,衣服脏得不像个样子。沙袖说没吵架,一直都好好的。她骗她母亲说,一明本来是到其他地方有点事的,临时决定回家,所以换洗衣服什么的都没带。她母亲说,没吵架就好,以后要好好给一明收拾一下,不能穿得这么乱糟糟的,男人嘛,出去得有个样子。
沙袖母亲又说,她爸陪一明去了坟地,他说一明在父母的坟前哭得死去活来,可心酸了。前天晚上一明还说,他要和沙袖结婚了,他说袖袖已经有了孩子,不结婚怕不太好。所以昨天上午,沙袖父亲陪着一起到派出所已经把证明开了,这几天他就回北京去。她母亲说,现在有喜了,一定要注意身体,可不能马虎大意,等日子差不多了,她就过来帮着照看一下,生了孩子由她来带。沙袖的母亲说了一大堆贴心贴肉的话,然后才想起来说,一明还没起来,要不要叫醒他接电话?
“不要了,让他睡吧,没什么事。”沙袖说,“我在这边挺好的,就是想家。你让一明带点家里的东西来,煎饼、咸菜,什么都行。”
沙袖放下电话就开始哭,整个人瘫在椅子上。这些天一直紧张,突然放下心来,她有点承受不住了。我说这还哭什么,什么事都解决了,一明我知道,他对你真是没的说,离不开你,你看,想通了不是天下太平了。
“担心死我了,他一定把自己折磨坏了。那几天他也不知跑哪儿去了。”
“可能是找个地方想事了。”
沙袖看看我,说:“你跟我说实话,一明他真的没变?”
沙袖的样子很无助,事实上她对自己的生活也无从把握,在这里,她完全失去了在香野地的坚强和自信。
“当然没变,这么多年一直没变。说实话,我挺羡慕一明的,有你这样一个顶梁柱支撑他的生活。”
“你在安慰我,我哪能支撑别人,自己都支撑不了。可我没有办法。”
不管怎么说,情况是好起来了。中午我们做了一顿不错的饭菜,也是这些天吃得最踏实最放松的一餐饭。吃完了睡午觉,要把亏欠的都补回来。我还在做梦,沙袖敲我的门。开了门,她说:
“你陪我去一趟医院。”
“干吗?”我还没睡醒。
“我想,还是不要了。”
“什么不要了?”
“孩子。”
我的哈欠打了一半,一下子睡意全无。“你要,做掉?”
沙袖点点头。
“一明不是想通了么?”
“可是,我觉得挺不好的,我也觉得别扭了。”
“是不是等一明回来再说?听听他的意见?”
“你要不陪我去,我就自己去了。”
我还能怎么说,只好去了。我明白她的意思,她想在一明回到北京时,看到一个和过去没有区别的清清爽爽的沙袖。说真的,这事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医生显然把我当成了沙袖的男朋友,上来就责怪我一点都不用心,现在到处都是卖套和避孕药的,就不知道防护一下,只顾自己快活,让女人遭罪。
“多久了?”长相慈蔼的女医生问。
“不太久,”沙袖说。
“反应强烈吗?”
“还行。”
“什么叫还行?”
“不太强烈,”沙袖说,然后胆怯地问医生,“很疼么?”
“不动手术,服药就行了。新出的药。你们这些年轻人啊,都快做爸爸妈妈,平常也不注意学习一点生育知识。决定了?”
沙袖说:“决定了。”
医生又看看我,我赶紧说:“是,医生,决定了。”
医生唰唰唰开始开单子,把单子递给我的时候叹息一声:“又是一条命啊。”
这句话让沙袖出了门就哭了,她靠着墙,觉得身体发虚。我扶着她坐到椅子上,让她等着,我去取药。付药的医生从窗口递药的时候,在口罩后面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搞得我很不自在,她大概觉得我是个杀人犯。我真是替人受过啊,是边红旗还是一明?
从香野地回来,一明气色好多了。他带来了不少香野地的特产,还带回来一块玉佩,是沙袖母亲当年生沙袖时戴过的,她说这是块吉祥的玉,可以保佑孩子在母腹里的成长,对将来顺产也有很大的好处,她让沙袖从今天起就戴上。沙袖拿在手里看了看,放到了抽屉里。
“戴上啊?”一明说,“你妈说戴得越早越好。”
“没了,”沙袖说,起身去了卫生间。又哭了。
一明看看我,我说:“她还是决定做掉了。除了你,现在她什么都没有了。”
一明的表情很复杂,说不清楚。他自己大概也说不清楚听到这个消息是什么感受。生活瞬息万变,很多事情都来不及让你想明白,来不及让你接受。就变了。我指指卫生间,让一明过去,他们的生活需要重新开始了。
本来想抽个合适的时间去看看边红旗的,听一个和警界有关的朋友说,这一茬抓的人都关在看守所里,还没判。我想一个人去,不让一明和沙袖知道,边红旗无疑是他们生活里最为浓重的一块阴影。还没成行,家里又打来电话,母亲说,有急事,他们托人给我在市里的晚报社找了个工作,很不错的,要我回去面试,越快越好。我说我不想回去,母亲很不高兴,说我不懂得父母的辛苦,他们在家为了我的将来伤透了脑筋,我却不领情,偏要留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闯出个名堂也就罢了,都上顿不接下顿了还不回头。这句话说到了我的痛处,几年了,我就过成这样。母亲又说,她和父亲眼看入土半截了,想过几天放心日子我都不让,养个儿子还有什么意思。母亲威逼利诱之后,姐姐又来电说,要我明家理识大体,父母大半辈子不容易,他们想抱孙子都快想疯了,几乎到了见到邻居家的小孩都流口水的程度。一句话,如果我尽快回去娶妻生子,完全是在为我们家做贡献,老祖宗都会感激我的。这些都是大话,说到底,他们其实是担心我再混下去,什么都得不到,最后连基本的事业和正常的生活都丢了。
放下电话我就开始抽烟,开始想,一副痛定思痛的模样。几年了,我在北京到底干了些什么?北京对我的意义到底在哪里?过去不是没想过这个问题,但都是一闪念,过一下脑子就忘了。是啊,为什么偏要留在北京?为什么那么多人削尖了脑袋要在北京占下一块地方?大家就那么爱北京么?我想肯定不是这么回事,但是,为什么很多人混得已经完全不像样了,还放不下这个地方?烟盒里的烟都抽完了,还是没想明白。
可是面试的日子已经定好了,由不得我不回去。
回到家,父母见了我眉开眼笑。他们说,应该没什么问题,晚报社好着哪,在我们这地方算是很不错的单位,关键是人家赏识我,将来的前途至少不会差的,据说编制问题也会尽快解决的。这不是一般的诱人了,难怪我父母扛不住。
面试的时候是那个女孩陪我去的,就是上次别人给介绍的女朋友,姓童,我叫她小童。上次见面之后,我们一直联系,打电话,发手机短信,感觉很不错,有点像热恋了。小童让我不要紧张,她爸已经和报社社长兼总编打过招呼了,应该不会有问题。我父母所谓的托人,大概就托她爸了。他们十二道金牌把我招回,也算是一举两得。小童在我父母和姐姐的监督下,把我收拾得很利索,让我觉得镜子里的那个人看起来还像模像样。
小童直接把我带到社长办公室前,敲门,出来一个头发花白的胖老头,我在本地的电视新闻里见过。
小童说:“余伯伯好。”她的手在我身后碰碰我,我说:“余总好。”
老头呵呵笑了,“疯丫头,两年多没去我家了吧?越长越漂亮了。”他又看看我,“这就是,啊?丫头,眼光不错嘛。进来,进来。”
小童对他撒了一通娇,说:“他胆小,可不要乱吓唬啊。”
老头说:“我敢吓唬他,那你还不跑到我们家,把冰箱里的东西都吃光。”
“多少年前的事了,余伯伯还提。”
“好了,不提,说正事。”老头坐到老总椅子上,从档案夹里拿出一大堆纸,随便翻了翻,“丫头送过来的资料我都看了,文章写得很不错,有几篇小说我也很欣赏。年轻有为啊。一会儿几个部门领导都过来,问什么你就说什么,放松点。”然后给秘书打电话,让她把有关领导叫过来。
我看看小童,她竟然把能找到的我的东西都复印下来了。她说:“是写得很好嘛。”
过来三个男的一个女的,围坐在旁边的会议桌前。老头介绍,我向他们一一致敬。然后就开始了。开始也是随便说。他们分别把我赞扬了一番,说我是眼下本市十分活跃的青年作家,写出了不少质量上乘的小说和散文,虽然人在北京,但是留有余香,能回到家乡效力,理当欢迎。尽管他们夸得还算有节制,但我还是觉得十分难堪,当时我的脸一定被他们夸得青一阵紫一阵,身上开始流汗,真如芒刺在背。接着是闲聊,让我说说对北京的感觉,对北京报业的看法,以及对晚报的一些想法。我就顺嘴瞎说,想到哪说到哪。他们都嗯,或者点头,或者微笑。大概情况就这样,他们都觉得我很不错,年轻,有锐气,有想法,有才华。他们当着老头的面,凡事都说好。接下来我退场,在门外等他们商定结果。大约五分钟,我刚抽完一根烟,一个领导让我和小童进去。
结果出来了,老头说,综合各位领导的意见,面试很成功,他代表晚报社向我表示祝贺,从现在开始,我就是晚报社的一名员工,可以回去准备一下,也可以明天就来报社上班。鉴于我对本市的社会各界情况还不是很熟悉,先让我做一段时间记者,各处跑跑,到时候再视工作情况另行委任。领导们鼓掌,一一和我握手,祝贺我重新成为本市的人。领导们散会了,老头向我和小童表示祝贺,问小童,什么时候请他喝酒。
“随便什么时候。”
“那不行,是那个酒。”老头天真起来也挺可爱。
小童挎着我的胳膊,说:“余伯伯,你再说,我就去你们家把你们家冰箱里的好东西全吃光。”
老头呵呵地笑:“丫头也不好意思了。好了不说了,”他拍拍我的肩膀,“小伙子,好好干,先做一段时间记者锻炼一下,对你有好处。还有,要好好对我们的疯丫头,我可是看着她长大的。”
我点头答应。
出了报社,我把领带解下来,到路边买冷饮。刚喝两口水,一明打电话来。
“怎么样?面试顺利吗?”
“还行。”
“那就没问题了。祝贺你!什么时候再回北京?”
“再说吧,可能要过几天。结婚的事筹备得怎么样了?”
“差不多了,我和袖袖决定简单一点,就几个人吃个饭,喝喝酒。你一定要赶回来喝喜酒啊。对了,袖袖让我问一声,你什么时候结婚?她想看看你那位哪。”
我看看小童,她听见了,对我嘟了一下嘴低下头,来回地转手里的矿泉水瓶子。我揽过她的肩膀说:“尽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