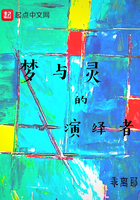等居延向他道歉时,唐妥火气早消了。一是唐妥性格如此,过了就忘了。二是他前两天接了个打错的电话,他说他不是武冰,对方不信,那你是谁?唐妥。唐妥是谁?没听说过。这也是常有的事,但唐妥就想进去了,妈的,没人知道你是唐妥,还理直气壮地报出家门,你以为你是谁啊。然后想到居延的“寻人启事”,实在没必要惊慌失措。不就借张脸么,多大的事,就算名字打上去也没什么,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居延也不容易,一张张贴出来,一次次往网上发,换了自己女朋友丢了,他未必能千里迢迢地来忙活。
居延说:“我请你们吃饭。”
距照相那天已经一周,很多人见到了那张“寻人启事”,这两天已经没人再向唐妥通报他曾被瞻仰过。这说明认识唐妥的人也就那么几个。但是胡方域杳无音讯。居延依然说,她谢谢大家,在支晓虹的房子里亲自下厨,请唐妥、支晓虹和老郭吃饭。
手艺不错。他们都吃出来了,尤其红烧和清炒两种,该浓酽的麻辣香醇,该清淡的松脆清明。唐妥他们三人在北京待久了,都染上了一口麻辣,吃得丢了半条舌头,就好奇居延生活在海陵,居然也麻辣得如此地道。居延腼腆地笑笑说:
“他喜欢麻辣。”
为了胡方域对辣椒和花椒的嗜好,她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学习川菜,厨房的墙上贴满了从网上下载的菜谱,办公桌抽屉里也放着两本书,没事了就翻出来溜一眼。她是南方人,过去沾了麻辣就跳脚,现在若去重庆和成都,吃遍一条街都不会有问题。热热闹闹的饭桌上慢慢就静下来,大家突然发现胡方域走丢对居延来说是件多痛苦的事了。两分钟之前还觉得居延千里寻准夫挺好玩,甚至荒谬和滑稽。看来凡事只要你干得认真,都能够生出足够的悲剧感来。
支晓虹咬着筷子问:“你要找到什么时候?”
“找到他走到我跟前,说,我们回家。”
她在一所中学教书,碰上了他也去上班,下了课她就在办公室里等他,等他站在门口敲敲门,说我们回家。她习惯了。她的中学跟他的大学相距不远,都上班的那一天,他们只骑一辆电动车。当然这是在居延离开工作单位之前。从去年开始,胡方域觉得两个人都忙,家里就荒了,也不缺那几个钱,就让居延办了停薪留职。居延有点舍不得,但也没到伤筋动骨的地步,就回家做了全职准太太。胡方域课不多,但学问做得辛苦,的确也需要一个人专门伺候。
“有希望么?”老郭说完了才觉得自己不厚道。
“只要我在找,就有希望。”
唐妥没说话,只在心里摇摇头。虽然居延的回答坚决得如同格言,但如果胡方域根本就不在北京,或者打死也不愿意露头,前提都没了,哪来的希望?这相当有可能。太有可能了。唐妥觉得他这辈子最大的美德之一就是,不相信奇迹。但是居延的信心像只防风的打火机,慢慢地又把饭桌上烤热了。大家换了个方向继续聊。
就说到了拉郎配借唐妥做花瓶。居延再次道歉,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她进苏州桥北边的大洋百货里买手机充值卡,旁边是拍大头贴的摊位。一个女孩挑了几个大头贴相框,拍的时候发现有个相框太大,一个人根本填不满,问了老板才知道那是两个人合影的相框,当然大。女孩就拉了一个正挑旅行包的陌生男孩来填空。男孩说,你朋友吃醋咋办?女孩气呼呼地说,酸死他,让他不陪我!居延觉得倒可以借鉴一下,胡方域能吃麻辣也能吃醋。谁知道还是没效果。居延说,一定是他没看到。
“要是他还念着你,不用找也会回头。”支晓虹还守着她的老逻辑。
“我一定得找到他,”居延把茶杯转来转去,“没有他,我都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
“没他怎么就不行?一个人有这么重要么?”唐妥说。
“人家感情深呗。太感动了”,老郭吃了辣椒似的嘶嘶啦啦直吸气,“以后不能再离了。”
唐妥的疑问得到支晓虹的附和。支晓虹没离过婚,但她前后谈过不下八个男朋友,不知怎么就好上了,一不留神又分了,马不停蹄地花前月下,因此十八岁以后的生活格外充实。分多了就没感觉了,所以也不觉得哪个人有多重要。三条腿的蛤蟆难找,两条腿的男人遍地都是,死了一半地球照样转。
居延小声说:“我都明白。”就不往下说了。倒是老郭有了某种优越感,喝着居延的啤酒数落唐妥和支晓虹:“你们哪,一个字,俗!”
支晓虹赶紧摸胳膊,这是他们俩习惯性的斗嘴,呀呀,老郭你看,鸡皮疙瘩掉了一地,都是你给瘆的。
一通大笑。接着说正经事,怎么找更有效率。说来说去无非那老三篇,不过就是再来一遍,往细节上落实:人工找,在街头和网络上发寻人启事;在报纸上登寻人启事,比如《北京晚报》和《新京报》等;报警,让警察帮忙。后来唐妥又想出一个,发动连锁的兄弟店面一起帮忙,在每家房产中介的房源信息张贴栏里贴上一份寻人启事,多一个人看见就多一分希望。这事有点难度,得支晓虹和老郭一起上。支晓虹拿下公司最高领导,让他同意加一份寻人启事;老郭是本店店长,负责把兄弟店长搞定,务必认真帮这个忙。至于唐妥自己,他住在北大西门外,每天上班前坚持到北大和清华贴一圈启事。
就这么定了。第二天也就办成了。
难度最大的是支晓虹,她亲自跑到公司总部,先是磨了半天副总,副总不敢点头,因为这事说小是小,说大也大,一堆房源信息里猛不丁蹦出个寻人启事,实在有点怪异,影响公司形象。支晓虹只好又去磨正总,把居延都上升到了现代孟姜女的高度。孟姜女起码还明确知道老公在长城工地上,居延根本不能确信她男朋友是否在北京,帮一个弱女子胜造七级浮屠啊。而且,换个思路想,一张扎眼的寻人启事恰恰说说我们公司仁爱义气,这是免费的广告呢。支晓虹没想到自己的口才这么好,把自己都感动得鼻涕眼泪一大把。老总扛不住支晓虹不停地抽他办公桌上的抽取式纸巾,就答应了。
回到店里,支晓虹趾高气扬地一挥手:统统拿下。晚上到了住处,她沉痛地对居延说,不容易啊,为了你我差点跟我们老总上床了。居延心眼实,看不出来她在开玩笑,答应一定好好再烧一桌川菜请他们吃。
唐妥的工作最简单,也最繁琐,每天都要往北大清华跑。启事上依然有他貌似幸福的脸,张贴进海报栏时常有学生惊异地发现,照片上那个面带微笑的男人好像跟贴启事的人很像啊,就勾过头来看他。唐妥笑笑说,是我。习惯就好了,就像每天他得早起四十分钟,开始困得眼睛睁不开,几天也就习惯了。
《北京晚报》和《新京报》分别刊登了“寻人启事”,间隔三天。启事见报的那两天,唐妥都有点神经质了,一看见别人在看报纸,就下意识地去瞅他们看的是否是刊有启事的那版,若是,就继续看人家眼光落在哪里;如果不是,他就会失望得干着急,恨不得直接上去指明方向。就那么小豆腐块大的方框,淹没在众多广告和别的信息里,唐妥心底里对它几乎不抱任何希望,作为一个资深的报纸读者,很多年来他都没想过要把眼光偶尔放到那个嘈杂拥挤的地方。
二十二天过去,北京如常。居延早出晚归,回来时依然是孤身一人,当她站在房产中介的店门口时,唐妥、支晓虹和老郭一起对她无奈地摇摇头。所有的信息出去后再没有回声。那天傍晚,天挺冷,居延站在店门口,隔着玻璃门对唐妥说: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