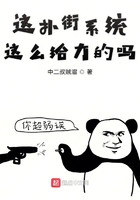葬礼过后,赵星给了姚丹一千块钱作为报酬。姚丹不要,理由是,难过说到底都是自己的,她觉得人这辈子不容易,想哭就哭了。赵星不答应,这也是花街的规矩,若不接受,老头子去了那个世界也是不安心的。没办法,姚丹只好收下了。
老赵的死为姚丹留下了好名声,她竟然哭得那么好,货真价实的儿媳妇怕也赶不上她的悲伤。在我们花街那地方,多少年了,想找这么一个能够尽心尽职地哭丧的合适人选太不容易了,都是事情来了,随便找一个搪塞了事。只有姚丹体现出了想当的敬业精神。有了第一次,就有了第二次。春节前,理发店杜小丁的娘去世,杜小丁的大姐在海南没能及时赶回来,死人又不好留在家里吃饺子,必须赶在除夕之前下地。杜小丁决定请姚丹当一回他大姐。姚丹开始不愿意,但是没办法,别人的儿媳妇都当过了,一条街上的,不能厚此薄彼。又答应了。她又哭得很好。然后不得不接受杜小丁给的八百块钱报酬。
接下来事就多了,挡都挡不住。不仅是一条花街,就是两边的东大街和西大街,遇到了人手不够都过来请姚丹。第一个推不掉,第二个推不掉,第三、第四就更推不掉了。在别人眼里,姚丹似乎顺理成章地成了一个专事哭丧的人,葬礼举行的时候哭上一哭,然后接受可观的报酬。
对此我母亲曾试探性地问过姚丹,母亲说:“这么做下去合适吗?”
姚丹说:“有什么不合适?找到一个可以大哭一场的地方也不容易。”
春暖花开的季节,我们家来了客人。那个人穿一身警服,戴着我从小就梦想的大盖帽,眉眼粗大,满脸都是胡茬。他从水上来,搭乘一艘过路的小船。我正在石码头上打捞水上飘来的小玩意,木头片什么的。他向我走来,几步外我就闻到一股新鲜的水味。他向我打听父亲的名字,我用树枝指指我们家的饭店,带着他进了饭店。
他们像老朋友那样握手。我听到大盖帽说:“可以找个地方谈谈吗?冯大力的事。”
父亲带着他上楼。我跟在他们后面,我喜欢他的大盖帽。
刚坐下,大盖帽就说:“冯大力死了。”
父亲手里的茶杯差点掉下来,“你说大力怎么了,老贾?”
“死了。越狱逃跑时被巡警击毙了,他差一点就翻过了墙。”
父亲的那杯茶最终没有倒完,坐到了大盖帽对面的椅子上。“怎么会这样?上次我看他不是还好好的吗?”
“他越狱,”老贾又重复了一遍。“都怪我,我应该考虑到这一点。他早就跟我说过,他想回家看看,他一直觉得家里出了事。”
“没出什么事啊,”父亲说。“她们娘儿俩都好好的。我回来后就让姚丹给他回信,他没收到?”
“没有,差不多两年了没收到一封信。大力都快急疯了,常常半夜里一个人哭起来。”
“大力跟你说过什么没有?”
“好像含含糊糊说过一点,”老贾说。“说花街这地方不干净,很多女人都靠身体吃饭。他是不是——你懂我的意思。”
“这个,”父亲抓了抓头发,对我说,“你到楼下去玩。”
我刚要下楼,老贾说:“是不是把姚丹找来?她是当事人,大力的后事还要她来处理。”
父亲想了想,对我说:“去把姚阿姨找来,别多嘴,就说我找她有点事。”
我一路小跑到了青禾家,姚丹正在洗脸,过一会儿准备去西大街的一个葬礼上为人家哭丧。她让我先走,她随后就到。
我说:“不,我等你。”
姚丹笑了,笑有些干,好像已经不习惯这种表情了。
去我家的路上她问我是什么事,我说没事,又说不知道。可我的两条腿老是出问题,走路突然不利索了,两条腿总打架。我闭紧嘴巴,不让自己再开口说话。
我把她领上楼。姚丹看到老贾坐在那里,整个人剧烈地哆嗦了一下,僵硬地站在门口不进来。屋子里的人都站了起来,老贾,父亲,还有母亲。母亲上前把她搀进了房间。
房间里的沉默让我恐惧,我觉得身上有点冷。我把脸转过去,看到了阳光底下完整的花街,青砖,灰瓦,高瘦的房屋和门楼,方方正正的一个个小院和院子里的老槐树。还有姚阿姨家的小楼。这是白天的花街,看不见在风里摇动的小灯笼,也看不见那盏诡异的红灯。后来我听到老贾说:
“大力死了,越狱逃跑被击毙了。”
“他,死,了?”姚丹说得很慢,不像阳光底下发出的声音。“他,为,什,么,要,越,狱?”
“他想回家看看,”老贾说,“看看你是不是那个,就是那个了。”
母亲叫起来。我转身看见姚丹像件衣服一样慢慢落到地上,松散地摊成一堆。我觉得她一下子老了,脸上似乎现出了灰扑扑的笑,冰凉的,整个人则和她的目光一样,突然间空空荡荡。
“姚丹,你怎么啦?”母亲摇晃着她。“你说话呀,你说话呀姚丹!”
姚阿姨似笑非笑地斜坐在我家二楼的水泥地板上,两手软软地支撑着自己。母亲急切地摇晃她,像在抖动一件衣服,姚阿姨的脑袋跟着母亲摇晃的节奏轻易地摇荡。
母亲说:“姚丹,姚丹,难过你就哭出来,你哭呀姚丹!你别吓唬我,姚丹。”
姚阿姨还是一声不吭,脸像一张空白的纸,几缕头发垂下来。
“你出点声呀姚丹,”母亲都哭了。“你们看她怎么不出声啊?”
老贾说:“让她静一静,可能是突然失声了。”
后来我才知道“失声”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下子发不出声音。我不知道当时姚丹是否真的失声,如果是失声,那她眼泪总该是有的吧,可她当时的眼泪到哪里去了呢。她没有声音也没有眼泪。
我和母亲把她扶到椅子上。母亲看她嘴唇干得起了皮,让我给她倒一杯水。姚丹就这么面无表情地歪在椅子上,什么声音都没有。她喝了两杯水。然后她要走,母亲问她干什么,她指了指西大街的方向,唢呐声从那边传过来。姚丹还是按时去了西大街,我父母和老贾怎么劝都无济于事,她执意要去。父亲不放心,让我和母亲跟着她,有什么意外也好照应一下。我和母亲一直跟着她,直到那天晚上的葬礼结束。
在葬礼上,我看到姚丹跟在送葬的家属队伍里,好长时间都没有一点声音,她失神落魄地跟着队伍走。沉默的姚丹让大家吃惊,哭丧的人怎么可以一声不吭呢?再说,她是一个优秀的哭丧手啊。旁边的观众骚动起来,开始抱怨,拿别人的钱怎么能不做事呢。
母亲说:“她心里难过。”
旁边的人说:“当然要难过,不难过怎么哭?”
他们不明白母亲的意思。母亲想和他们争辩,又觉得没什么好说的。说什么好呢?这时候,围观的人群又骚动起来,姚丹开始哭了。开始声音很小,像抽泣,突然之间,猝不及防地大起来,像一个瓶子被猛地摔碎了。在接下来的葬礼上,姚丹哭得比以往的任何一次都卖力,都悲痛欲绝,她嘹亮的哭声和滂沱的泪水,赢得了死者家属和旁观者的更高的赞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