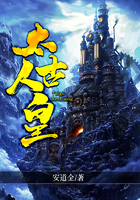那天下午,我去东大街给茴香修鞋,我叔叔和冯长官他们在石码头上掷骰子。还是老规矩,谁输了谁请酒,没钱请酒就摸女人屁股。在过去总是我叔叔输,赢了也是输,明明叔叔的点大,当兵的都说冯长官大,那就冯长官大。我叔叔也乐得巴结他一下。我叔叔知道自己必输,干脆身上从不带钱,要不万贯家财也不够请。他就摸女人屁股。来来回回在石码头上转悠的往往都是妓女,他即使没摘过她们的灯笼上过她们的床,收钱的时候多少也摸过一两把。
本来我叔叔做好认输准备的,但玩了一半,酸六从石码头上经过,冯长官就把他招过去了,让酸六替他掷。输了算他的,赢了算酸六的。冯长官明知道他和酸六是仇人,还拉扯到一起,让我叔叔很郁闷,不仅觉得失了宠,还有被蔑视之感,下手就狠了点。酸六哪玩得过我叔叔,哪个点都小,裤子都要输掉了。结果算冯长官的。叔叔这回较了真,一肚子怨气都撒出来,输了就请酒,没二话!
“真让我请?”冯长官说。
我叔叔梗着脖子说:“请!”
冯长官掏了半天口袋,没带钱,“怎么办?”
我叔叔狠狠地说:“摸!”
冯长官脸上下不来了,话都放出去了,手下的都看着呢。要借钱开不了口,摸一下就摸一下,反正是妓女。石码头上当时有好几个女人,但冯长官就看中了茴香,他知道茴香和我叔叔的关系。他对茴香下手,陈满桌一定会阻止,他跟着就坡下驴,事就算了了。陈满桌偏偏就没阻止,他看见冯长官上了船,也歪着头上了船。茴香正站在货架前张望,还以为冯长官要买东西,没想到冯长官的手就伸到她屁股上了,茴香尖叫着跳起来。冯长官把手伸出去之前还看了一下我叔叔,我叔叔一声不吭,但当茴香跳起来时,我叔叔一下子扑到冯长官身上,他居然把冯长官压到身底下,挥起了拳头。
这是我所知道的叔叔这辈子最勇猛最像个男人的一次。
当然,最后的结果很明显。冯长官鬼哭狼嚎地叫起来,一群当兵的冲进船舱,拽出冯长官,然后把我叔叔结结实实揍了一顿。我回来时,看见他鼻青眼肿地坐在石码头上,衣服上的扣子掉了一半,敞着怀,肋骨上也有一块块的青紫。我叔叔目光呆滞,稀拉拉的几根白头发被风吹散。
叔叔回到家里,失落、后悔、不甘和恐惧在他的眼里交替出现。出现最多的是失落和恐惧。这一回合酸六胜了。他竟然打了冯长官,在过去是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叔叔越想越怕,连冯长官都打了!一连好多天都不敢出门,怕遇到冯长官;还躲,我离开院子他总让我帮他把大门锁上,免得冯长官找他麻烦。
我叔叔多虑了,没人找他,冯长官看样子很忙。我在石码头和花街上看见他,总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头歪得更厉害了,有人跟他打招呼也不理,或者压根没听见。据我的一点经验,局势可能有点紧张,摆在他脸上呢。冯长官的手下每天巡逻三次,东大街西大街甚至更远的地方都要顾及到。到我们的船铺子上买东西的当兵的也少了,一天也就两三个,买完就走,不像过去那样缠在那里,两只眼贼溜溜地往茴香身上瞅。有个下午我看见酸六撩着长衫跟在冯长官屁股后头,一个劲儿地说,他又写了一幅字,感觉相当好,想献给冯长官。冯长官向他摆摆手,酸六不识相,还跟着。冯长官突然甩了他一耳光,说,你他娘的想吃枪子啊!酸六捂着腮帮子愣了,等回过神来,吓得撒腿就跑,腰疼都忘了。等我去蓝麻子豆腐店买豆腐回来,又遇上酸六,酸六看样子相当悲哀,说鬼话似的问我,唐长官好还是冯长官好?我哪认识什么唐长官,冯长官好不好也不清楚。酸六就说,还是唐长官好,写完祝辞还对我好,请他喝酒吃肉,还对他笑眯眯的。
下午冯长官突然下令搜查码头上的船只。所有泊下的船都不许动,全部查完了才可以离开。查得非常仔细,有地方还用刺刀去捅。我们的铺子查完了,干耗着没生意做,我就和茴香去了叔叔家。我跟叔叔说,没事了,冯长官根本顾不上你,没准儿要打。叔叔高兴坏了,打仗好,打仗好啊,一打仗他就更顾不上我了。然后又诡异地一笑,说:
“打死了更好,这辈子他都顾不上我了。”
茴香哼了一声,“就那点出息!”摸屁股这事茴香根本没放在心上,不就摸一下么,摸完别扯出乱七八糟的事就行。
我叔叔为了庆祝冯长官顾不上他,决定开始喝花椒送的补酒。我说花椒嘱咐了,酒不纯,别喝了。叔叔说,喝,一定得喝,五谷送的。去蜡封的时候他一定想到了五谷,还摇头晃脑地唱了几句小曲。茴香说:
“喝,喝!喝死你!”
叔叔说:“五谷送的酒,喝死也痛快!”
我和茴香吃完了饭,叔叔还在喝。茴香要上树玩,我就拉拉扯扯把她弄到树上,两人坐在树杈间去看石码头。冯长官的人还在船上跳来跳去地搜查,不知道到底要查什么。然后我们俩说起话来。茴香说,几年前她看见我整天爬到树上非常羡慕,也想学会爬树,可我就是不教她,气得她睡不着觉,睡着了却梦见她爬上去了,我也要爬,她就在上面用脚踹我,踹得我一次次掉到地上狗啃屎。多年前的时光重现,那时候我生活中最重要的除了婆婆,就是这棵老槐树和石码头。在槐树上玩,一年四季向四周看,吃槐树花,抱着一根树干睡觉。石码头去得更多,我喜欢水,喜欢来来去去的大小船只,也喜欢一年到头在水上跑来跑去的船老大,他们喝了酒就开始讲经见过的稀奇古怪的好玩事。我在槐树和石码头上一点点看见了这世界。
黄昏来临,我听见屋里咚的一声闷响,然后听见叔叔的哼哼声。我伸头从树上往屋里看,没点灯,晦暗不清。茴香说,别理他,喝得忘了自己是谁了。叔叔的哼哼声越来越大,他在喊茴香和我的名字,叔叔说:“茴香,茴香,木鱼,救,救救我。”我再伸头看,叔叔正爬着越过门槛,上半身已经到了门外,嘴和鼻子在往外流血。我吓坏了,要下去,茴香突然掐了我大腿一把,小声说:“不许下!”我看看她,她还是说,“不许下!”掐我的劲儿更大了。
叔叔继续在叫我和茴香的名字,一边尽力往外爬。眼睛里也开始往外流血。他浑身都在哆嗦,爬得艰难。几绺头发沾到眼里流出的血上,那张脸像年画里恐怖的鬼脸,一条条血如同一根根虫子在爬,越爬越大。叔叔伸着一只胳膊斜指向天,只指了很短的时间就摔到地上,他拉着下半身终于拖过了门槛。叔叔的声音越来越怪异,听起来凄厉而遥远,既像一个球将要爆炸,又像一条河即将干涸。叔叔说:“茴香,救我。木鱼,救救救我。”茴香掐我的手一直没停下。
“妈,妈呀!救救我!”叔叔突然大喊一声,脑袋摔到地上,过一会儿慢慢又抬起来,声音已经极其衰弱了。“妈,妈,我是满桌。”
他在叫婆婆。我不能再不下去了。我挣脱茴香的手开始下,茴香一字一顿地说:
“花椒出嫁的当天晚上,他硬是爬上了我的床。”
我的脚悬空,两只手吊在树上,僵硬地停在那里。墙头上冒出来一个脑袋,叫了一声就不见了。叔叔还在爬,一寸寸爬到了我的脚底下,身后留下几条发黑的血珠子线,他还在说:“妈,妈,救救我,我是满桌啊。”茴香坐在树上,什么声音都不发。我就这么吊着。
大门被人撞开,隔壁的妓女惊惶地跑进来。“哎呀,出事了!”她说,“死人了,死人了!”她想把我叔叔从地上拖起来,没弄动,见我还吊着,就说,“还不下来,你叔叔要死了还不下来!”我落到地上,刚把叔叔扶起来,叔叔撇撇嘴笑一下,想说什么,突然七窍猛地窜出七股黑血,头一歪,死了。隔壁的妓女拍拍叔叔的脸,又试了一下鼻子,手定在那里,沾满了血,她突然叫起来:
“你们还是不是人?在眼皮底下都不救!”
我慢慢放下叔叔,给他合上眼皮,然后在他身边蹲下来,一瞬间我泪流满面。我止不住地哭,一点声音都不出。
叔叔的坟在婆婆旁边。大地上的又一个包。埋完后,我坐在坟边陪叔叔喝了会儿酒,离开的时候给他磕头,然后给婆婆磕。茴香跟在我后面也磕了。然后上船,所有的家当都在船里,我们以船为家。
船离开石码头是个傍晚。行了五六里路天黑下来。我们都不说话。远处传来巨大的爆炸声,我们的船摇荡几下。然后是另外的爆炸声和枪声。我回头去看,石码头和花街的方向起了火,有遥远得如另一个世界的喧嚣声从水面上波及而来。火光开始还小,很快就越升越高,半个天都是翻滚着的红。我停下手里的橹,心里一下一下地疼。茴香挽住我胳膊把我身子转过去,说:
“走吧,没有人需要你。除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