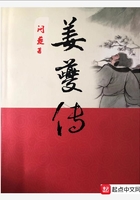一
潘黄牙这段时间过得暗无天日。在炮楼里动辄挨荒井原的训斥,有时挨让他眼冒金星子的耳光。荒井原那把寒光闪烁的军刀,时不时还在他头上比量。他已经尿过好几回裤子了;回家以后,他老婆也没个好脸子,时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为什么要跑到金牛顶去给你找解药。还不如直接在那跟了二当家的。”她摸着微突出来的肚子,悲悲戚戚。“黄杏儿也怀孩子,我也怀孩子;她过的是什么日子,我过的是什么日子。”
看在老婆怀着孩子去匪窝求解药的份上,潘黄牙再一次原谅了女人的絮叨。“皇军刚才抓了那么多人,鸡飞狗跳,你知道是干什么吗?”潘黄牙从笤帚上拽了一根下来,剔他那两颗大黄牙。
“不是修围子吗?”他老婆说。
“屁。娘们知道什么。告诉你吧,去趟雷。前两天在炮楼里,我听荒井原说,要用老百姓去对付地下魔鬼。荒井原说,老百姓有的是,死一批再抓一批;鸟窝村的抓光了,就去抓其它村的。哼!皇军还能没有办法治那些魔鬼?”潘黄牙扑一口吐出块饭渣子。他觉得两颗大板牙中间的豁口越来越宽了。“你现在知道跟着我的好处了吧?要不是我,你也被拉去趟雷了。”
“你肯定他们不会来拉咱们去趟雷?你不是趟过一次了吗?”潘黄牙老婆心有余悸,立即往他后腰上看。又去摸自己的肚子。
“皇军现在知道我是忠心的,还要委派大任务给我呢,哪舍得让我去趟雷。”
“屁!那是他们觉得你还有利用价值。我看你是脑子糊涂了,整天做飞黄腾达的梦。你真以为日本人能打下这片江山,给你个县长当当啊?你也不退一步想想,要是小日本打不赢,你会是什么下场?可怜我儿子生下来,头上就戴着顶不光彩的帽子。”
“男人要想成就一番大事,就得冒险!娘们懂个屁!”
潘黄牙又骂开了。他觉得老婆的话不吉利。正骂着,外面远远地传来轰一声响;又一声。潘黄牙从炕上蹦下来,跑到门口,朝风波镇的方向看。他这阵子不受待见,很识相地猫在家里,也不知道荒井原那边什么时候展开行动。
“炸了!”潘黄牙在门口眺望风波镇的方向,听到那边轰轰声不断,火光一团一团地炸了又灭,灭了又炸,起起伏伏。一阵子火药味顺风飘过来,辣得他打了个喷嚏。
“炸的是咱鸟窝村的老百姓,你咋呼什么!前两天你后腰上淌臭水,前院老朱老婆还偷偷跟我说抹点锅底灰试试呢。老朱也让日本人抓走去趟雷了吧?这都是做的什么孽呀。”
潘黄牙老婆又想哭号。潘黄牙喝住她,让她看清形势。“敌众我寡,日本人什么装备?咱们什么装备?早晚是败!要是再啰嗦下去,我看太君就要想办法调用更厉害的武器了:飞机大炮什么的。几发炮弹过去,就解决问题。”
潘黄牙老婆停止哭号,警惕地看了看手搭凉棚正在眺望的潘黄牙。“不是你给日本人出主意,让老百姓趟雷开道的吧?”
潘黄牙不吱声,换了一只手放在眼眉上方;另一只杵在后腰上。他不吱声,他老婆就哭号开了。“你这个不积阴德的死老潘哪,叫我们娘俩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都什么时候了,又哭!也不看看,那边都打成什么样了!要是今晚日本人打进风波镇,往后这一带就更是日本人的天下了!一路南下,打进麦县,还不是小菜一碟?你是要保命还是要积阴德?”
潘黄牙老婆想想,也挑不出他男人的话有什么不对。只好担心起薛寡妇来。想那薛寡妇等了快一辈子,才把锔锅匠等来,这一回还不知怎么个死法呢。
那边的火光过后,乒乒乓乓地打起枪来。“遇到抵抗了。”潘黄牙评论道。只听枪声,无法分辨谁占上风。潘黄牙放下搭着凉棚的手,跑到前院老朱家旁边的一条胡同,往南又跑了几步,跑到日本人修的围子跟前。他正在考虑要不要再往南去一去,查看那边的动静,一颗子弹无声地飞过来,啪一声钻进土围子里。潘黄牙掉转身就往回跑。
约莫过了一个小时,外面呼呼啦啦地响起走路声。潘黄牙听了听,是日本人的靴子声,拉拉杂杂的。他正要从炕上爬起来,他家那扇刚换上的崭新的核桃木门就让人一脚踹开了。他听那动静,估摸门扇已经掉了,不禁心疼得骂了一声娘。骂声刚落,灶屋的门也被踹开了。潘黄牙掀开门帘一看,几个日本兵已经站在灶间;荒井原和胡谦及另外一名中队长在后面鱼贯而入。潘黄牙看了看荒井原的表情,好像不对。又看了看前面的几个日本兵,身上都挂了彩,黄屎色军装破破烂烂,且熏得黑不溜秋。一看就是地雷惹的祸。
荒井原两手拄着军刀,刀杵在潘黄牙家地上的几棵柴火上,人看起来极其生气,叽里咕噜地说了一大通;由旁边的胡谦翻译给潘黄牙听:“皇军很生气,因为中了埋伏。”
“怎么会呢?前面不是有老百姓趟雷开道的吗?”潘黄牙觉得后腰那里隐隐作痛。
“老百姓都过去了,没炸着;皇军走的时候却被炸了。死伤了三十多人。一定是他们暗中在地雷上动了什么手脚。”胡谦说。
“他们大大地坏。”潘黄牙说,“不是我的主意不好。”
荒井原又乌鲁哇啦说了一些话,由胡谦翻译。“皇军说,一定有人告了密,被他们知道咱们要用老百姓开道了。”
“有道理。我的主意是很好的。”潘黄牙生怕荒井原指责他主意出得不好。
“潘黄牙!你告了密却还装模作样!皇军很生气!”胡谦说。
“我?我为什么要告密?不是我!我对皇军是忠心耿耿的!”潘黄牙这才明白荒井原那张驴脸为什么拉着了。他吓得不轻,只恨自己不会说日语,和荒井原直接交流和沟通,解除误会。
胡谦附耳对荒井原说了几句什么,大概是翻译潘黄牙的表白。荒井原根本就不信。他把军刀在地上使劲戳了几下,乌鲁哇啦又说了几句。潘黄牙吓得尿了裤子,赶紧去看胡谦。
“皇军说,你让地雷炸了,却找他们要到了解药。别人都死了,你却活着。他们为什么要给你解药?一定是你暗中背叛了皇军,和他们勾结起来。”
“冤枉啊!胡谦老弟,求你和皇军解释解释,我下辈子作牛作马也报答你!”潘黄牙扑通一声跪下了。
“我解释了,皇军不听啊。死伤了三十几人,这笔账只能记到你头上。谁让你和那边勾结呢。皇军现在还怀疑,你前几天去风波镇,名义上是去探听情况,实际上是勾结去了。你今夜这命是保不住了。不过你放心,你老婆肚里的孩子,我会求皇军开恩给你留下的。”胡谦蹲下身,捡起地上的一棵柴火,放在手里玩。
潘黄牙觉得胡谦的眼里飕飕在往外冒凉气。他们俩一直不合。“我看你才是告密者!你爹你妈都在风波镇,你不是告密者,谁是告密者?你一向嫉妒我的才干,生怕皇军重用我,暗地里没少在皇军面前说我的不是,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这是在诬陷我!我要让皇军杀了你!”潘黄牙看着胡谦那一双冷飕飕的眼,忽然间心里有灵光闪烁。他觉得胡谦特别像一个告密者。
然而,他想什么也白搭了。他正在再次感叹自己不会说日语的时候,就看到那把杵在地上的军刀飞了起来。接着,他觉得那些人在他眼里莫名其妙变成横的了,像一根根房梁一样横在空中;等他看到跪在地上的自己脖子上什么都没有了,血从碗口大的窟窿里往外冒的时候,才知道自己的头已经掉到地上了。
二
几个人在胡宅开会,胡菰蒲照例为刚结束的一场战斗做总结。“今晚一仗,小鬼子死伤三十多人;我方只受伤四人,且都是轻伤。被驱赶着趟雷的老百姓安全地踩着雷过来了。这说明,我们刚刚研发的长藤雷十分成功。另外可以看出,我们的地雷在杀伤力上有了很大进步,炸死炸伤小鬼子已经不是难事了。地雷组功不可没。”
这次开的是扩大会议,除了韩角声、老黄、曲则全以外,徐铁匠和徐石匠哥俩、陈麻子也列席了。老黄越发奋力地往本子上记录,一张脸庄严地崩着。
“应该的,应该的。”地雷组的几个人纷纷谦虚。“其实主要应该归功于提供情报的人。咱们要不是事先知道鬼子打算驱赶老百姓趟雷,哪能想出赶制长藤雷呢。”徐铁匠说。
“那是,那是。”陈麻子说。他第一次参加这么严肃的会议,在胡菰蒲家的八仙椅上坐得很不自在。经过这几场战斗,他彻底服了胡菰蒲,觉得初秋就该跟这么个爷们儿才对。初秋端茶来的时候,他很惭愧地低下了头。
“咱们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咱们风波镇现在仰赖的就是地理优势,只要把大路和庄稼地守好了,就暂时没有大碍。但小鬼子肯定会卷土重来。一旦久攻不下,我担心他们会调动大型武器。飞机大炮什么的,都说不准。到那时,恐怕地雷也救不了咱们了。所以,还是得做好思想准备。”胡菰蒲说。
“什么准备?”徐石匠问。
“拼命。”胡菰蒲简略地说。在场的人除了韩角声,都面面相觑。老黄记下拼命两个字,抬起头,不无忧虑地看了看大家伙。
“有那么严重吗?”陈麻子问。
“有。很严重。”胡菰蒲说。
“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一直没说话的曲则全很激动地站起来。“打他个小日本的!有枪就用枪,没枪就用头锄头,再不行就用拳头!”
“则全很像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胡菰蒲笑着说。他一直很赞赏这个青年。“角声,你怎么看?”胡菰蒲转向韩角声。
“咱们不能被动挨打。炮楼需要的给养,现在除了从四邻八村靠日伪军抢掠老百姓,主要是从虹城往这边运。老百姓都被抢得实在没什么可抢了。我觉得,咱们可以暗中发动各村秘密造雷,截小鬼子的给养。能截多少就截多少。这样一来,既可以把给养抢来用,又可以让小鬼子腹背受敌,两头乱忙。”韩角声说完,看了看其他人。
“这主意不错。反正到头来免不了一死,还不如多杀几个小鬼子再死。”徐铁匠第一个表示赞同。
会议结束,形成一个决议:由地雷组派人到能遏制运输道路的村子里,秘密开展宣传发动工作。当地有地下民兵组织的更好,可以互相配合。
大家四下散去,回家补觉。老黄又誊抄了一份决议内容,和韩角声一起离开厅堂。
“角声,老爷是要把我誊抄的那份决议报给组织上吧?”老黄边走边问。
“这还用问啊?”韩角声说。
“咱们这几次行动,都是事先得到了可靠情报。所有情报都是从厂里来的吗?可厂里一来一回得有几十里地呢。”老黄不解地说。
“这有什么奇怪的。水浒里不是有个神行太保戴宗吗?日行千里,赶得上汗血宝马。咱老爷手里说不定有这么个神人呢。”韩角声笑着说。
“真的啊?”老黄刚想惊叹,扭脸却看到韩角声在偷笑。“你就别拿老黄我寻开心了。”
“神行太保那肯定是不靠谱的。但老爷自有老爷的办法。要不为什么他是老爷,你是老黄呢。”韩角声说。
两人站在二道门的暗影里又说了一会儿话,韩角声回到拳房去了。老黄回屋躺下,怎么也睡不着,想想几个小时前那乱成一锅粥的枪战,就起身披了件衣服往风波湖去了。
疯女人的小木屋里还亮着灯,从唯一的一扇小窗户里渗出来。老黄松了一口气。这些日子他总是觉得命很贱,说没就没了。老黄敲了敲门,发现门没关,闪着一条缝。他又敲了敲,里面传出疯女人的声音:“老黄吧?进来吧。”
老黄推门走进去,发现疯女人不是一个人:胡逊正坐在一张小马扎上,两手托腮,无比忧郁。看到老黄进来,疯女人伸手从床底下又拿出一个小马扎。老黄对这些小马扎很熟悉,因为都是他做的。选的是念头岭上的红枣木,打磨得光洁细腻;支撑轴用的是黄铜,也打磨得像条黄金。疯女人编了渔网做凳面。渔网经纬线交叉编结得细密,坐起来很是舒服。
这种优质红枣木做成的马扎抗用。时间越久,颜色越鲜亮。老黄仔仔细细地把屁股安放其上,生怕把它坐疼了。“你什么时候来的?”他看了一眼胡逊。后者把托腮的两只手拿下来,不知道往哪里放,只好颓唐地搭在两只膝盖上。其实,老黄知道胡逊没事时经常来。这个小木屋,就数他一老一少来得多。老黄也知道胡逊近段时间闷闷不乐的原因。“没关系,男人都得有个开始。”老黄想了想措辞,说。
“什么开始?”胡逊懒洋洋的。
“就是和秦腊八成婚的事啊。哪个男人要成家过日子了,都会想东想西的。过日子也就那样。过着过着,人就老了。也没什么可怕的。”老黄用过来人的口气安慰胡逊。
“老黄,我现在还不想娶人。”
“我知道你喜欢的是杏儿,可你没那个命。杏儿没出息,跑去当了土匪婆,你就把她忘了吧。连我都把她给忘了。”老黄说着违心的劝慰话。“虽说现在打着仗,可日子还是得过呀。秦腊八刚死了爹,也够可怜的。”
“老黄,问你个事。”胡逊现在提起秦腊八,就打心眼里烦恼。“是不是男女之间有了那事,就非得结婚?”
“也不一定吧。不过,不结也不对。秦腊八一个黄花闺女,肚子里又怀了你的孩子,你要是不娶她,她就没活路了。是不是?”老黄寻找着合适的措辞和态度,争取从情感和道义上都说得过去。
“你们两个正好都在,我打算问你们一件事。”胡逊呼哧呼哧喘了两口气,吹得他脚面下的渔网不安地颤悠。“我先问你吧老黄。二十年前,你把我从门口捡回来时,究竟看没看到她?”
胡逊指指疯女人。
“什么意思?”老黄糊涂的样子不像是装的。“她不是你三岁时领回家来的吗?”
疯女人还在织渔网,手里拿着老黄用枣木给她做的梭子。那东西薄得像纸片,一头尖尖的,看起来像一把小匕首。老黄对自己的手艺非常满意。疯女人拿着这把像小匕首一样的梭子,套着一根绿色的渔网线,在灯光下绕来绕去,仿佛没听见老黄和胡逊的对话。老黄觉得,她在织渔网的时候很美,一点都不像疯子。
“人家说,我爹是胡菰蒲。”
疯女人没反应,老黄却反应得厉害,霍地从小马扎上掉到地上:“谁说的?”
“别管谁说的。到底是不是?”
“你是我从门口捡的呀!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啊?”
“这就能说明我爹不是胡菰蒲吗?”
老黄渐渐明白胡逊的意思了。他一张脸拉得老长,五官都拧到了鼻子周围。“那,人家说没说,你娘是谁?”
“说了,是她。”胡逊看看疯女人。
“谁说的?”老黄重新坐上小马扎,揉着太阳穴。
“薛寡妇说的。锔锅匠说,她是当年在虹城剧院唱戏的小花梨。他见过她。”
“那也不能说明什么呀!”老黄急着想否定这件事。他觉得很危险。
“薛寡妇以前也曾听有人告诉她,胡菰蒲在虹城和一个戏子关系不错。”
“薛寡妇的话能信吗?”
“为什么不能信?她家里进进出出的都是些什么人!都是在江湖上混的。”
老黄觉得胡逊的话很有道理,他想反驳都反驳不了。他转而求助疯女人。“大妹子,大妹子!这事只有你知道。”
疯女人停下梭子,从门缝看看外面的夜色,答非所问地说:
“下了大雨,湖水就要涨了。水涨船高,鱼跃龙门。”
三
胡逊和老黄一起走回落日街。刚进门,哑巴厨子从厨房闪出来,指着厅堂,一阵子乌鲁哇啦。
“怎么了,哑巴?”老黄问。老黄胆小,见哑巴厨子歪斜着嘴,似是厅堂里的人或事极为棘手,不免脚步有些犹疑。胡逊却正好和他相反,一个箭步窜出去两米远。发觉老黄没跟上来,胡逊不耐烦地回头拽他的胳膊,绑架一样把他拽上台阶。
厅堂里的格子窗用不透明白纸糊得很严密。尽管如此,太太初秋仍是在里面加上窗帘,用的是布店里最厚的布。老黄和胡逊如果不进去,根本不知道里面坐着的人竟是白鸥。这姑娘依旧一身男子装扮,揉着一块手绢哭哭啼啼。
胡逊看到胡菰蒲仍像往常一样坐在他那把专属椅子上,头上的白发没少一根,就放下心来。但他随即又对自己刚才的焦急很不满。他厌恶地看了眼胡菰蒲,恼怒自己为这么一个人,刚才恨不得脚踏风火轮冲进屋来。他到底是不是我爹?薛寡妇说得那些话是不是真的?所有围绕这件事而生出的疑问,都在他脑子里打起了结。他没有凭据,只能凭直觉。直觉告诉他,眼前这个可恶的人,一定是他爹无疑。他怎么能不恨这个无情无义之人呢——这个无情无义之人,应该把疯女人接进家来,好好对待。
白鸥停止哭哭啼啼。韩角声和曲则全已经在老黄和胡逊之前就到了。
“好像是要开支委会呢。”老黄悄悄对胡逊说。
“你们聊着,我先走了。”胡逊一听,感到自己在场不合适。他有些不悦——凭什么曲则全是组织里的成员,他却不是。他还是胡菰蒲的儿子呢。
“胡逊不用走,坐下来听听。不是外人。”胡菰蒲说。胡逊只好留下来,找了把椅子坐下。白鸥开始说事情的经过,间歇性地抽泣上几声。
听了一会儿,胡逊才明白她说的是砖瓦厂的事:白老板不幸遇难了。关于这个白老板的身份,胡逊从老黄那里听过一些,加上他在落日街上那几场魔术秀,在胡逊心里就落下了个神出鬼没的神秘印象;现在一听他遇难,竟然有点不相信。仿佛白老板是传说中那些永远不死的神人。
白老板前段时间在策划武装起义的事。按照上级部署,特委成立了抗日救国军,发动了一次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这给了白老板很大的信心,他们决定在虹城东北七十里的石竹县再来一次武装起义。石竹县伪县政府刚成立没多久,力量不是很强大。发动共产党员和民兵秘密收集枪支弹药、争取各方力量的的前期准备进行了一个多月,然后在一个叫红竹的镇子上集合了起义队伍共五百多人,长枪短枪五百多支。短短一月时间拼凑起来的队伍,很顺利地攻克了石竹县城。实际上也谈不上攻克,基本没费什么枪支弹药。五百多人的起义队伍到达县城西门外,稀稀拉拉地放了示威性的几枪,石竹县临时政府县长就带领他的一班局长出城迎接,表示愿意支持抗日,无条件投降。这样一来,起义队伍就撤离县城,挥军石竹县旁边的几个镇子,收缴了乡校中队的很多条枪支。在他们兴致盎然地收缴枪支时,石竹县县长却火速派人跑到赤丘市,请来几百号日军驻进石竹县。起义部队返回头来第二次杀向石竹县城,被日本人的重机枪打得颇有折损,只好退回去另待时机。
那段时间,基本上就是在忙这件事。砖瓦厂平日除了保证有几个同志佯装干活外,其余特委办公人员其实也不算多。书记白芦、秘书白鸥、一个负责技术的同志、两个负责交通的同志、一个干事,另外还有白千春和负责交通的老万的爱人,她们两人负责做饭。特委领导下的几个县陆续在秘密发展抗日队伍,负责交通的两个同志每天都在外面跑,人手严重不足。白芦就抽调平日干活的同志去跑联络工作。
出事那天,砖瓦厂只有白芦和白鸥、白千春,另有一个干活的、一个看大门的,一共五人。老万爱人生病,老万用黄包车拉着她去看病,同时送一份文件到老万爱人的娘家村;这样一来,只有白千春一个人在厨房准备晚饭;白鸥和另一个同志在晾晒场干活,一人用圆筒做瓦坯,一人用矩形木框倒砖坯。白鸥喜欢做瓦坯。正做着,听到大门口乱哄哄的,负责交通的老万拉着黄包车疯似的跑进来,车上坐着他已经中枪死去的老婆。老万边跑边回头开枪,然后就一头栽倒了。黄包车载着他老婆,从他身上轱辘辘地跳了过去。
白芦正在屋子里和负责技术的同志商量事情,从窗户里往外看看,看大门的同志已经牺牲了。白芦和负责技术的同志一起跑出屋子,拖着老万就往晾晒场汇合。几个人边打边分别退到三口窑里。窑里码着一垛垛砖瓦坯,散发着冷飕飕的泥土气味。
“老万,老万!”白芦趴在老万脸上,抹去从他头上流下来的一绺糖浆似的血,以便让他把眼睛睁开。
“老钱……”老万干裂的嘴皮好不容易才张开。
“老钱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老钱……叛变了……”
老万牺牲了。血改变方向,流向他的太阳穴。
“今天看样子是得死了。没子弹了。”一阵乱枪过后,白芦又朝外放了一枪,打死一个鬼子,回头对白鸥说。那边往这边砰砰地放枪,下雨似的密集。
白芦扔掉枪,在窑壁上摸索着找到藏匿的手榴弹,朝外扔出去。一共扔了三颗,白芦不扔了。他侧耳听了听,好像另外两口窑里的战斗声也不那么激烈了。他想了想,决定把剩下的手榴弹都留着。他把那些东西一颗颗排着插到裤腰里,对白鸥说:“钻到烟道里去,快点。”
“你呢?”白鸥问。
“你别管我。必须有一个人活着。”白芦说。“出去后写份材料交给上面。”
白鸥钻进黑乎乎的烟道。她听到外面轰轰地响了好几声,又是一阵放枪的声音;子弹打在窑壁上,噗噗地响个不停。
最后一切都安静下来。半夜时分,白鸥听到外面有人走动的声音,她在烟道里面缩紧身体,不敢吭声。后来仔细听了听,是一只野猫。白鸥钻出烟道,站在窑门口四处看了看。那只野猫蹲在旁边一口窑的窑顶上,仰头看着天上半明半暗的月亮。整个窑场瞬间变成了坟场,将塌未塌的砖瓦窑像坟墓一样衰死着。
厨房也被打得不像样子,窗户上一块铁雨搭子落在地上,密密麻麻全都是弹孔。白鸥数了数,一共七十八个弹孔。看来日本人是花了大力气。锅里躺着一摊冰凉的玉米面粥。经费紧张,他们的粮食严重不足,只能经常煮粥喝。
“老钱是谁?”胡菰蒲问。
“特委有两处办公地点,一处是砖瓦厂,另一处在一个四合院里。老钱是四合院那里的负责人。不知怎么回事,跑交通的小钢被盯上了。警察局长派人佯装查门牌,去搜捕四合院。得到消息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老钱刚把文件点上火,还没烧多少字,就连人带文件给抓走了。动了刑,供出了砖瓦厂。”白鸥说。
“地下工作,谈何容易啊!”胡菰蒲叹道。
胡逊平时只管负责布店,其它事都不理不睬,听了这半天,心里生出些惭愧来;尤其想到自己为之烦恼的那些事,包括和秦腊八的婚事,就更惭愧了。
四
胡菰蒲蹲在厨房外面的院子里,喂地上的鸽子。哑巴在厨房里摘菜,不时抬头看看院子里的胡菰蒲。
胡菰蒲在观察一只鸽子。它有些忧郁,对地上的玉米粒不屑一顾。胡菰蒲家的鸽群以灰色为主,只有两只除外:一只是眼前这只母鸽子,脖子上和两只翅膀尖上各长了三圈砖红色羽毛,看起来像戴着围巾和披风。眼睛也是砖红色的。另外一只此刻不在鸽群里——它要强壮些,翅膀上微泛蓝光。蓝鸽子是公的,跟这只砖红色的母鸽子是一对。它们是十年前胡菰蒲从上海信鸽协会买来的,信鸽竞翔比赛的冠亚军。公的骁勇,母的灵巧。
“恐怕是回不来了。”胡菰蒲像是在对红鸽子说,又像是在对哑巴说。
哑巴厨子心里也隐隐不安。哑巴从父母那辈起就是胡家的厨子,父亲哑巴母亲聋子。轮到哑巴这辈,就决定不娶老婆不生孩子了。哑巴把胡家的鸽子当成孩子来养。
红鸽子闭目卧着,偶尔睁开眼,看看哑巴,看看胡菰蒲。它睁开眼的时候,眼圈上的裸皮皱纹就堆叠起来。胡菰蒲很久没这么仔细地看红鸽子了,他奇怪她的鼻瘤和嘴角两边的结痂,怎么会不经意间长到这么大。想起刚买回时,它还是一只青年鸽,脚趾鲜红,鳞片柔软。胡菰蒲知道,这些都说明了一件事:红鸽子老了。她和蓝鸽子生育哺喂的幼鸽太多了。
哑巴知道,好几天之前,红鸽子就病了,懒洋洋的没什么力气。否则,和蓝鸽子形影不离的她,也不会同意蓝鸽子独自外出。
蓝鸽子是外出送信的。胡菰蒲猜测它一定是遭到了不测。它死在哪里?是在去虹城的路上,还是返回风波镇的路上?是砖瓦厂,还是四合院?这个问题,胡菰蒲不知道答案。他只知道蓝鸽子八成是回不来了。
哑巴厨子把菜摘完,也蹲在地上看红鸽子。哑巴不会说话,但听力和感觉功能都高于常人。胡菰蒲不说话,他也能猜出他的心思。他们俩都知道,红鸽子也活不长了。因此胡菰蒲蹲在那里,就算是提前凭吊红鸽子了。
晚饭过后,胡菰蒲没叫任何人,独自穿过小胡同,去风波湖边看疯女人。疯女人听力十分了得,根本不用抬头就知道谁来了。她在拆渔网。胡菰蒲自己找个小马扎坐下,半天不说话。他依稀记得疯女人还叫小花梨的时候,脸上长了一些可爱的小雀斑。就是因为那些小雀斑,师傅才给她取了个艺名叫小花梨。但现在他看不到那些雀斑了,不知道是不是脸上的灰尘把它们挡住了。
胡菰蒲从小马扎上站起来,手伸到一个脸盆里,绞了块毛巾,过来给疯女人擦脸。他想看看那些雀斑还在不在。疯女人嘴角朝下弯了弯,看不出是嘲讽还是要哭。胡菰蒲擦了两把,没看到雀斑;又擦了两把,就放弃了。他把毛巾丢回脸盆里,一时间怀疑疯女人究竟是不是小花梨。
“那条船。”胡菰蒲把下巴朝外努了努。“会驾驶吧?”
疯女人对他的话置若罔闻,仍然埋头拆渔网,拆得又快又准。渔网线弯弯曲曲地从她手里长出来。
“有什么事的话,就跑到船上去,驾船离开这里。往南划。”胡菰蒲说。“恐怕要出事了。蓝鸽子死了,红鸽子也不行了。”他见疯女人还是不说话,只好自言自语。
“下了大雨,湖水就要涨了。”疯女人终于开口说话了。
“没关系。风波湖底下有泉眼,涨多高都没事。”胡菰蒲安慰疯女人。他觉得这女人像小花梨,又不像;像疯子,又像正常人。可他又明明知道她是小花梨。
“胡逊明天要成婚了。要是冲着秦六指,我不同意这门婚事。但秦腊八怀上身孕了。况且秦腊八这孩子不错,不像他爹。虽说这兵荒马乱的,可咱们也得过日子啊。胡谦给日本人做事,我是不指望他了。所以,我只能指望胡逊给胡家添丁进口了。”胡菰蒲觉得自己表达得有点混乱。疯女人还是没反应,仿佛胡逊跟她没什么关系似的。
又坐了一会儿,胡菰蒲起身离开了。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包,放在刚才坐过的小马扎上。“要是真出了事,拿着这些钱,也好到别处安个家。唉,这兵荒马乱的,哪儿也不是安家之地啊。”
疯女人看了一眼布包包,还是没什么反应。布包包是胡菰蒲当年在虹城和小花梨好的时候,小花梨送给他的一件绣品。这东西一直放在家里,初秋从不过问。现在送出去了,胡菰蒲觉得他把这块心事送还给滚滚红尘了。
返回的路上异常安静,让胡菰蒲觉得不安。刚穿过小胡同走到落霞街上,就听落日街上传来一声含混的炸响。凭这些日子的经验,胡菰蒲觉得那是地雷的响声。莫非鬼子又来夜袭了?胡菰蒲加快脚步穿过另一条小胡同,拐到落日街上。他奇怪地闻到一股浓烈的火药味,不像是从北边庄稼地那边飘过来的,倒像是从布店里窜出来的。胡菰蒲拄着阴沉木手杖,无奈两条腿不一样长,还是走不快。等他走到布店门口,韩角声已经在里面了。“胡逊兄弟没了。”韩角声说。他站在柜台前面,看着和一堆炸烂了的柜台倒在一起的胡逊。有一枚生锈的铁钉还插进了胡逊的手心,使他看起来就像被钉住了似的。
“应该是抽屉雷。拌线系在把手上。一拉抽屉,地雷爆炸了。”韩角声蹲下身仔细看了看炸掉的半个抽屉。里面还残留着几枚残缺不齐的大洋。
胡菰蒲没听到韩角声还说了些什么,只是盯着胡逊手心里的那枚铁钉。胡逊的脸炸掉了下巴,眉头还在,却皱着。胡菰蒲看着看着就出现了幻觉:胡逊越变越小,变成了一个婴儿,躺在蓝花布包袱里,手心里插着一枚铁钉。
胡逊变成了一个婴儿,胡菰蒲却觉得自己变老了。他蹒跚地转回身。在布店门外探头探脑的人主动分开一条路,让他走了出去。走到落日街上,胡菰蒲见到疯女人站在夜色里,一缕白头发随风飘摇。
“他从生下来,手心里就插着铁钉。是个受难者。”胡菰蒲说。他觉得自己的话莫名其妙。
走上胡宅高高的大门口,胡菰蒲回头看了看。疯女人站着的地方什么都没有,只有风。他疑心自己看到疯女人只是幻觉。
半夜时分,韩角声来到黑灯瞎火的厅堂。胡菰蒲坐在黑夜里。“老爷,查出来了,是徐二思干的。秦腊八喝砒霜了。怎么处置徐二思?”
“角声,你说呢?”胡菰蒲问道。他感到自己的声音特别无助。
“一枪崩了。”韩角声说。
胡菰蒲想了想。“算了,饶他一命。胡逊本就不该来到这个世上。都是孽缘。因孽缘而生,因孽缘而死。这是他的命。”
韩角声要退出去的时候,胡菰蒲又把他叫住了。“问问哑巴,红鸽子怎么样了。”
“死了。哑巴正在收拾棉槐篓,要把它带到念头岭埋掉。”
“一块儿,把胡逊也带到念头岭埋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