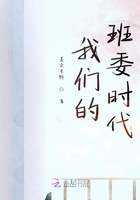正午的阳光很是毒辣,漫天的金色耀眼的似要将那蓝澄澄的天空生生撕裂。尽管只是跪在树下,可那斑驳透叶的金黄却丝毫烈度不减,挟着股腾腾而来的热浪,灼灼扑面。
稍稍挺了挺身子,酸痛的膝盖叫嚣着我满身的疲惫,一身淡白宫装因背脊不断沁出的汗蠕蠕黏上身,堪堪燥热的心绪愈添烦乱。
意识恍惚间,身旁的画扇似是递上了一把浸润着白芷香的锦帕,我稍稍迟疑了下终还是摇了摇头:“不用。”
画扇的手顿了顿便恭顺的退下了。我当然知她是为我好,但万事有因有果,强求不得,我既已在月前做下那样一场赌,如今便万万没有了反悔的余地,这些罪受着倒也不觉活该。
只是——月前中秋夜下的那一幕却时时如梦魇般在我脑海中盘旋,隐隐的刺痛,虽不至于撕心裂肺,却始终有些钝钝的茫然与荒凉。
“皇的美意末将心领,只是末将心中早已有至爱的女子,怕是消受不起公主这番美意。”
那晚他抱拳起身,低垂的头颅使得我看不清他的脸,只记得那黑的不掺杂丝毫杂色的发润着温淡稀疏的月色,凉凉的沉入我的心底。
吱——。
喧杂绵长的开门声将我的思绪打乱,翻起一片连绵不断的尘芥,我顺着光望去,却不料被一袭艳红如血的衣裳生生灼痛了眼。待回过神来才发现那门口立着的不过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艳红的丝袍松松散散,只用一条玉白的金丝软烟罗系出曼妙媚人的纤纤楚腰。胸口的衣襟敞开尚不自知,堪堪露出线条优美的颈项及清晰可见的锁骨,斜斜依靠在门边,肆意慵懒的将我望着,眼底里的放荡不羁很是让人生厌。
我知道,眼前的这位大约便是最近很得母亲欢心的新宠——花溪。花溪?我在心中暗暗冷笑,还真是够娘们的名字。
尊贵无比的公主却跪在一个男宠面前,这画面委实还是不妥的,伶俐的画扇适时的上前将我搀起,站起的过程中我却险些因膝盖的酸痛麻木而摔倒。至始至终,他都没说一句话,只是懒懒的站在门边,恣意的将我打量着,那目光中的毫无顾忌竟让我无以反驳,只能冷冷回视,半响道:“母亲既已醒了,可以麻烦你让让吗?”
他却只是笑笑,眉宇间透着股娇媚入骨的味道,也不答我,便转身步入殿中。我一愣,心下闪过一丝薄怒,深深吸气将它压下,我心中自然是无比的敞亮明白,现在可不是胡闹发火的时候。
初宸殿内很安静,看不到一个人影,空荡荡的殿宇内便只余我淡白的宫装逶迤拖地的‘呲呲’声,很是诡异。殿宇的尽头,是一张巨大的带幔帐床,帐幔富丽华贵,坠以彩穗装饰,朦朦胧胧的将人隔离在外。
我恭敬的在隔床十步有余的位置停下,低头行礼道:“儿臣给母皇请安。”
而花溪则甚是自然的越过我,步上玉阶,挑开帐幔,近乎无礼的坐到了虞水心床边,低下身子似是在耳语些什么。那漆黑如夜的发便顺势如绸布般披下,印着他光腻如玉的颈项,美的略带妖异。
这情景委实有些尴尬,我低下头,目光中闪过一丝微诧。不仅因这少年的无礼,更因母亲的平静安和,仿佛刚刚他这逾矩的行为是件再自然不过的事?
许久,两人终于停止了这‘耳鬓厮磨’,虞水心慢悠悠的将手搭上了花溪的肩膀,借着他的力道坐起身,仿佛才注意到床前站着的我,道:“哟,这不是锁情吗?这大热的天,在门外等很久了吧?”
我低着头,嘴角漫开抹不易察觉的冷笑,转瞬即逝。再抬首时便恢复成了一惯的静淡:“母皇休息要紧,儿臣不碍事的。”
“嗯……”,她淡淡的应了声,徐徐推开面前的幔帐,款款道:“这么着急的来找母后,是有什么要紧事吗?”
我低着头迟疑着该如何开口,半响方道:“是有关三月后儿臣与酹月王爷之间的婚事……。”
还未等我来得及说完,虞水心妆容精致的脸上便显现出十二万分忧愁哀伤的模样,保养得宜的葱葱五指轻握住我手,神情是满心的歉疚与不舍:“锁情,我知这件事很是对你不起,但你父皇生前便只有这一个兄弟,当真是放在心尖尖上来疼惜。如今你父皇驾崩,整个君式王朝便只剩下了你叔叔君墨舞这一个独苗,我又怎么能忍心眼睁睁的看着他断后呢?”
虞水心这番话的确是说的情深意切,恩义并重,若是其他人听了,恐是要感动的怅然泪下罢。可此刻进入我耳中,却只觉得可笑。
君式王朝?当年繁荣阜盛,盛极一时的东临国君式真的还存在吗?自从一年前我父皇君墨崖因病崩殂后,母亲虞水心便以父皇无后,酹月王爷病入膏肓为由,在众多早已买通好的官员拥护下,以女子之资登帝。
登帝第二年便改国号为倾,取吞并四海,倾尽天下之意。同年,东临国也在母亲的一手安排下改名为天虞王朝。对于百姓们来说只要能吃饱饭,一家人和和睦睦没有战乱,便是好的,至于国家到底由何人当政,其实是没甚关系的。而某些清流派官员虽私底下颇有微词,但碍于虞水心过于强大的政治力量与几乎称得上残暴的打压,即便是有意见也是不敢说出口的。于是整个天虞王朝便在一种看似祥和平静的状态下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但有时候,太过平静却并不是一件好事。就好比你永远也看不透一汪明净安宁的水面之下,会涌动着怎样尖锐刺眼的波纹?
而在这许许多多不安的涌动中,最让虞水心担忧的便是那从16岁开始便卧病在床不问世事,传说早已病入膏肓,行之将死的酹月王爷,先帝唯一的弟弟——君墨舞。
说起这个人物,京师里绝对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传说其三岁能诗五岁能文,诗词音律,阴阳八卦无一不通,当真无愧于‘鬼才’这一称号。虽说做文章做的行云流水,但他却也并不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据传其14岁便随先皇出征,曾使计以区区五万兵力力败南越国20万军队,漂漂亮亮的打了一回大胜仗,从此盛名远扬,名满京师。再加其姿容秀美,风华高雅,曾经一度是京师众女子倾心爱慕的对象。
只是造化弄人,奈何16岁那年汹涌而来一场大病,一夜之间便不能视人,曾经那般绝代风华的少年郎整日里便只能病卧床榻,苟延活命,形同死尸。帝念其兄弟情深,三年内先后择取五名貌美女子嫁进酹月府,却皆不出一月便暴毙而亡,其中一女子更是在新婚之夜便莫名没了气息。传说其死状惊恐,甚是可怖,似是看到了什么恐怖骇人的东西般惊惧的阖不上眼。一时间各种关于酹月王爷府闹鬼诸如此类的诡异猜测尘嚣而起……
如今,我便要做那第六个女子了么?我低头,倾覆住她手,眉眼含笑,凉薄如水,殷殷道:“母亲这是说的哪里话?且不说那酹月王爷本就是旷古奇才,天赐的玉润良人。即便他是个眼不能视、耳不能聪且不良于行的废人,锁情这样一个罪臣之女能嫁与他却当真是三生修来的福气,半分委屈都不曾有过的。”
没料到我会提及自己的亲身父母,虞水心愣了一愣,立时便恢复了常态,眼眸里淡淡朦胧似笼了层水雾,更添了几分离别哀伤:“我那个妹妹,也真是命苦,当年我那般苦苦的劝她,她却似带着破釜沉舟般的决心非要嫁与你父亲,最终却闹了个香消玉殒,家破人亡……可惜啊可惜……那样一个绝妙的人儿……。”
看着她一派哀伤至极的模样,我心略有些烦躁,微拢了拢青丝,却并不言语,直至她说完方切切开口:“母亲又何必如此自责,当年我父亲林瑞将军暗自与南越王私通书信,欲退让15座城池换得黄金十万,这般卖国投敌的行为本就很是令人不齿,即便后来遭受满门抄斩的重刑也是理所应当的。而母亲念及我那时年幼,将我从刀闸下救回,收为义女,授予公主这般尊贵的殊荣。这般重比千金的恩情,锁情是万万不敢忘怀的。”
说完我兀自屈膝,跪倒在地,“锁情此番前来并不是为了我自己。只是想到日后不能常侍母亲身侧,不能尽为人子女应尽的孝道,便心怀哀伤,食不知味夜不能寐……。”
远远传来一声机不可察的呲笑,那声音太过微小淡弱,使的我几乎要怀疑是这声音是否存在过?口里依然一刻不停的说着来时便烂熟于心的腹稿,低垂的眉目却不可自抑的微微上扬,眼底里便映上了一张似笑非笑的脸。
花溪依然一副闲适散淡的模样,好似全然没有将这殿内的众人放在眼里。淡淡笑望着的一切的眼底蕴着几分高深莫测,深深沉沉如一汪碧水,触手即凉却怎么也捉摸不透。
那漫懒中暗藏着隐隐犀利的目光让我骤然一惊,心下掠过一丝被人看透一切的慌乱,暗暗垂眸低头,硬着头皮将剩下的客套话说完整。
虞水心似乎很满意,曲身虚虚将我扶起,伸手探上我的脸道:“不愧是我虞家的女儿,如此的深明大义识大体,情儿你放心,既然你肯做如此牺牲,母亲定然不会亏待你。三个月后,我会以天元公主的级别替你置办嫁妆,保证让你风风光光的嫁进酹月府,决不让人小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