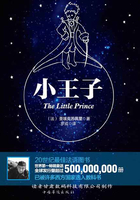[一三一]
蝴蝶在林野间化作冷艳的光火,带起一条蓝色的光线,在黑夜里幽幽地飞燃,所到的每一片地方都凝结起刺骨的寒冰。
喀啪喀啪薄冰狂覆。
天寸寸地黑下去。
酒店里一片嘈杂,人声鼎沸,空气全是浓重的酒味儿。
凉介隔着赤尾坐在安格附近,还没开饭就被人灌下四瓶清酒,脸上已经初见红晕,但头脑还算清醒。
关于一部《风信子》音乐文艺片的洽谈宴,据说是佐藤凉介父亲用重金签订的剧本,这次酒宴就是为了谈安格担任其中女主角的事。故事倒叙方式开头,讲述的是年少懵懂初恋的往事,非常质朴而又纯 真的感情,脱离物欲金钱,唯一亲密的镜头是两人在铁轨边牵手。可原本能在一起的两人,为了各自不同的梦想而最终踏上不同的归路,坚定而又满含泪水的决心,在挥手唱歌中结束一切。
安格觉得这部片子是多么亲切,一如当年的自己。
她拿起在面前摆了很久的酒杯,里面是满得快溢出来的清酒,赤尾劝阻了她一句,见她执意要喝没有再多说什么。
仰脖喝下,周围有人叫好,然而这次与以往不同的是,安格很快就醉了,并且醉得不省人事。
黑夜在冷光蝶翅下扑腾,最终在振翅中暴露一泓血腥,在空气中迸开溃裂。
睁开眼睛,在钟声里发黄的天花板,拉开又深又黑的阴影,在更远的地方缩向一个渺小的点。
头阵痛着,沉沉地无法动弹,身体一片瘫软,像被压了千斤重的棉花,把眼前所有的一切都白皑皑地覆盖,白色是柔软而又病态的色泽。
窗帘还拉着,窗户明亮的轮廓被清晰地印出来,看来时间已经不早了。这是一个陌生的房间,看样子是宾馆,洗手间传来哗哗的水声。
她斜眼看了看床边,被子被掀开一个角,床单起着层层褶皱,有躺过的痕迹。
出乎意料的,她只是浑身微微颤抖了一阵,便如死人般良久地盯着天花板,连拳头也无法用力握紧。
蝴蝶的翅膀被撕成两半,躺在干裂的土地上。
而曾经有人以为,蝴蝶的翅膀可以撼动整个世界。
KN79公司。
“这样做太过了吧?”叶子滴着水,落到水坑里,雨刚刚停。
“要迅速炒作人气,这是最快的方法。”
“可她对外公开的年龄也才二十岁啊,这么小就……搞不好会成负面新闻!总监!”
“放心好了, 一旦反应过头我会封锁消息的。”
“我还是觉得这样太过分了,名节对于一个女生很重要啊!”
“你能走到现在这样,你难道敢说你自己不是这样的吗。”提尖了嗓门,讽刺的反问,却以句号来结尾,是不容置疑的肯定。
明日香陡然跌在沙发上,像被人抽去了脊骨。
脊梁是一个人表现骄傲的外在——而你早就没了。
“我不希望她跟我一样……”
“哼,”赤尾皱起眉,“如果我们不抓住这机会炒作的话,别的公司就会抢去。对现在这两个人来说,不管对象是谁,结果都是一样的。”赤尾将烟头摁灭在灰缸里,“你认为一只小蚂蚁,不凭借任何 东西,它能爬上十米的高端吗?”
[一三二]
为什么不是力量扣杀了空虚。
而是梦想变成了毒药。
梦想变成了毒药。
提线木偶行走的名利场,背后操纵者勾心斗角的天堂。
[一三三]
洗手间的门呼啦一声被推开,洗完澡穿好衣服的佐藤凉介走过来,黯淡地坐在床边,背着安格的脸。兜里揣着一包烟,他掏出来又放回去,心里想到的是书上说吸“二手”烟的人受到的尼古丁更多。
“那个……”他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安格直直地睁着眼。
“早上一醒来就这样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安格很努力地呼吸,竭尽全力地呼吸着。
“到底有没有发生,我也不清楚,一点印象也没。”
安格没有哭,她从床上爬起来,下床时脚一软差点跌到了地上,大脑完全无法运转,真的是生锈了。她扶墙站稳,沉默得如同哑巴,两眼空洞仿佛失去瞳孔,她穿好衣服,手一直在抖,无法遏止。
佐藤凉介用力抹了下脸,沉重地从肺里唏嘘一口气:“我会对你负责的。”
安格往外走去。
“楼下全是媒体。”
开门的手顿了顿,然后用力地按下去,门锁咯哒一响,侧身出去。啪嗒啪嗒的高跟鞋在走廊里踩得响亮。
这个世界是多么的肮脏。
真他妈的肮脏。
我跟它是一样的东西。
安格边给明日香打电话边往下走,电话很快通了, 嘟了几声没人应。她烦闷地把手机挂了,一出楼梯间就看见在大厅里围得跟田野似的记者,一个个像是插在水里稻子挺在那儿,一看到目标人物就蜂拥 了上来。
安格心里堵得慌,把她挤得东倒西歪恨不得摔到地上的记者群机关枪似的发问,她蛮横地推开摄影机,从人群里强行往外走,可愈发激动的记者更加拼命地挡住了路,连脚都迈不开。
“听说有人看见你和一位新星一同进了宾馆?”想把话筒塞在我嘴里,是吧?
“请问你们什么时候开始交往的?”想把照相机贴在我脑门子上,是吧?
“粉丝们目前都还蒙在鼓里,能把这件事解释一番吗?”这根本不是你想要的娱乐圈,这根本与你想要的生活背道而驰,对不对你早就明白了。
佐藤凉介不停地按着关门键,电梯终于关上开始往下行。
白发少年从餐厅里出来边打着哈欠边往大厅走,才发现大厅塞满了人,原来水泄不通这个词儿形容得就是这个模样。
是哪个明星呢。少年退了几步又往右去了点,总算能看到那个人的样子了——
手中拎着的包裹突然就掉了。
连同心脏一起被重力狠狠扯下。
佐藤凉介往大厅跑去。
“请问对方叫什么呢?是前些天和你传绯闻的佐藤凉介吗?”真是本性,狗咬到块肉就不放了。
“你不回答是有什么需要隐瞒吗?”最讨厌有人刨根究底了。
“我们会如实报道这一切的,为了大众我们会找到那个人的。”最讨厌找人了。
安格努力平息心里的怒火,面红耳赤,终于体会到血液从爆破的动静脉涌进喉咙的感觉了。
她恶心得快要吐了。
“是我。”生疏的日语,非当地的口音,但安格没听出来。
“你们要找的人是我。”趋势越发明显了,但安格仍然麻木,耳里塞满相机的咔嚓声。
佐藤凉介刚要开口就被站在大厅另一角的少年打住,他先一步开口,记者们先是一愣,然后分拨似的往那人涌去,“Ray!是Ray——”
白发少年身后的保镖很快上前拦住媒体,白发少年走近呆若木鸡的女生,冷漠的神情很快淡化开,眼睛红了嗓子有些沙哑,所有记者在少年说了句话后安静了一阵子,是中文。
“你难道准备,就一直这样背对着我么?”
安格呼吸变得大而深,一股潮湿的雨风从大厅门口吹来,眼泪啪嗒一下就掉了。
“我还站在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步那里啊。”
少年微笑,唇钉还是两个,在阴暗的通风口璀璨地散出光亮。
“你不准备试着走一下?”可他马上就没笑了,因为安格哭得一塌糊涂,眼泪一直掉,却没有声音。
连高兴都没有时间。
“——你到底发生了什么?”
冷光蝶再怎么美丽,也是没有热度的,永远不可能像光芒一样又温暖又明媚。
只有蓝色的,孤寂的,短暂的冷光。
最后连自己也封冻在巨大的冰窖里。
心慌。意乱。措手。不及。
“Ray,请问你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吗?为什么现在才出现?”记者们一边狂拍照片一边发问。
“不要问他——”近乎是乞求的语气,但仍然无济于事。
“之前并没有你和あんかく的报道,是否属于一夜情的范畴呢?”尖锐地把美好撕裂开来。
忌司哑然地立在安格面前,刚才光想着帮她解围,什么都不知道就一头冲了过来。安格穿着令人无比怀念的黑色皮衣,零碎的黑发只够下巴的长度,素净没用任何化妆品的脸蛋,水汪汪的眼睛还是一如 从前的清澈,感觉没有太大的变化。
可是什么不对了呢,太久没见,所以觉得遥不可及?
保镖和负责人终于一点点地疏散了记者和围观者。
忌司虚起眼睛,注意到对面面容清秀的长发少年,或许该称之为男子,忌司眼眶越发地红了起来,银白的发色使他的面庞显得苍白又忧郁,他伸手替安格擦了擦脸上的泪痕,犹豫了好几次,小心翼翼地 问道:“对象是他吗?你们……在宾馆里……”
“嗯,我们睡了。”
话从安格嘴里咬字清楚地吐出来,像吐出五块碎冰。
“一年半,因为他所以不再给我们电话了吗?”语速变得飞快,他眼里充满了不可理喻。
安格想说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从来我们之间就要隔着个人呢?以前是尹,现在又来一个……”忌司强忍着眼泪,喉结上下翻动却再说不出话来。
“怎么样,嗯?”安格拿开忌司的手,两个人的手都是一样的冰冷,体内的血液似乎要停止循环快要干硬了,“我很令你讨厌、很恶心吧?这样的我终于可以说配不上你了吧,‘一坨屎还让我惦念这么 久’你心里肯定有这么想吧?我就是这么贱这么孬!找我还不如找AV女优!”
忌司的脸青一阵紫一阵,面色变得很难看。
佐藤凉介看了他们一会儿,转身踏出了宾馆大门,一边点燃一根烟。
“把第一次见面搞成这个样子,我干吗还活着呢,我期待了那么久的见面,到最后我却发现我得禁止想你禁止喜欢你……好笑吧?喂,是不是很好笑?你为什么不说话……”
其实在我生命里,本来可以拥有很多美好的东西,却每走一步失去一个。是那些不属于我吗?还是说我是被上帝领错了的孩子,本不该存在,却偏偏又存在,像弹球一样被打来打去,不过是他老人家错 念的玩具,没有任何东西属于我,我也不属于任何人。
不,是没有任何人,会长久地希望我在他身边。
那些曾经跟我说要永远在一起的人,早已散落天涯了。
缄默半晌。
忌司向前走了一步,把安格用力地拉进怀里:“好在我还是又见到你了。”
只要见到你就可以了。
“你不觉得我很脏吗……”
“对不起,你的一切,我没能保护……”
安格抱紧了身前的少年,她觉得自己的脸都快哭得扭曲了。
可是怀里,心里,全部是温暖而真实存在的少年。
唱歌的意义,我找到了。
[一三四]
如赤尾洪宇所想要的那般,登上报纸头条。
只不过不是赤尾洪宇所概定的对象。
为什么安格只喝了一杯酒就醉了呢,因为酒里下了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灌佐藤凉介呢,因为是事先串通好的。
“啊!!”
安格终于忍不住大叫了起来,她紧紧握着拳头使劲在桌子上捶打,心里面的怒气积蓄得满满从主动脉爆涨出去,在血液里急速地奔腾,血管快承受不住压力,整个人几乎要爆炸了。
“啊——!啊——!”那些消息全是雪乃和结衣偷听总监与明日香的对话知道的。
她紧闭双眼放开喉咙,空气从肺部吼出,在声带处发出大而低的呐喊,然后呛进一口凉气,剧烈地疼痛在喉间撕扯。
那一瞬间安格什么都不想做,只想把所见到的一切全部摔碎、破坏,好像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毁灭了心里才会痛快一些。
太压抑了,受不了了,竟只有这样的方式来发泄。
她随手拿起耳机塞到耳里,把声音开到最大,音乐震耳欲聋把其它所有声音全部殆尽,重金属的击打乐像轰鸣的火车碾过,汽笛声尖锐地叫嚣,扎得耳蜗深处硬生生的疼痛。
她觉得全身上下的力气从来没有来得这么汹涌过,那些一度很喜欢的音乐变得难听而嘈杂,她皱着眉头把耳机抽下,使出所有的力气将它砸向墙。
随着塑料壳在墙上痛苦地粉碎开来的声音,安格紧紧抓着发根再次尖叫起来,嗓音越喊越高越来越大,她从来没觉得自己的肺活量有这么好过。不知道过了多久,她终于瘫软下来,喉咙疼得无法咽下唾 沫。安格软绵绵地抬起手在额头挥了一把,终于靠在墙上,安静地流下泪来。
“你搞什么啊,这耳机可是限量版的,喂你有病啊?”公司里那个叫谁谁的艺人听到动静,跑过来看到地上的碎片就鼓着眼珠嚷嚷起来,然后赶紧叫来了总监。
鸡毛蒜皮大点的事,用得着么,嘁,要不你妈我再给你买一个。
“不小心摔碎了。”安格眨眨眼睛抬起头看向总监,话脱出口的时候还是软弱了下来,音色沙哑又低沉。散乱的刘海挡住眼睛所以赤尾洪宇没有看到她红红的眼眶。
“我靠,这叫不小心?我看你真的是有神经病吧,不就是稍微受了点委屈么,至于?再说跟你的那个人还搞错了,这帐我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