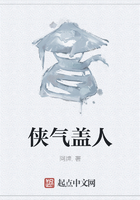“你以为老子不敢打你?”段昱浪挥起拳头当真狠狠地砸下一拳头,忌司被他摁在墙上,头差点撞上壁灯,“你把格格的梦想当什么了?你把乐队当成什么了!”
“段昱浪!”
“我要让他清醒点,他不值得你心疼!”
“——真正要单飞的人是我!”安格紧紧地闭上眼睛,不得不扯大嗓门吼叫,喉咙传来一股令人窒息的痛,她咳嗽了几声,睁开眼所有的人都维持着刚才的动作,如同录影机的画面突然被卡住,“是我 ……是我……背叛了大家……”
“你说什么?”夏天真几步扑上来,她拍拍安格的脸蛋,又拍拍自己耳朵,“是你说错话了还是我听错了?”
“安格。”忌司平静地说,“多谢你好意,别袒护我。要单飞的人是我,报纸上不都写着?连对话都有。对不起大家,如果有意见尽管冲我来。”
“……我就要去日本了。”心脏仿佛在喉间跳动,“咕咚咕咚”连着头骨穴位震颤,安格别过脸,不敢正视三人。
“是我的话也会这么做。同伴单飞,不抓紧时间签约可是会落后的。”忌司居然在这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冲她狡黠一笑,“安格,加油哦。”
段昱浪离开忌司走进洗手间,拧开水龙头往脸上扑了扑水。他盯着镜子里的自己,初三退学以后第一次发现自己又有了黑眼圈。
“你们……都决定好了?”段昱浪抹了一把脸走出洗手间。夏天真茫然地立在床尾,两手抱臂,或许是因为空调温度开得太低,所以恨不得钻进被窝里沉沉地睡去,再也不想醒来。
“嗯。”两声同时响起的不同嗓音。
“那就下去跟媒体宣布吧。”段昱浪心烦意乱却又不得不强打起精神,“走吧走吧,反正我和天真两个都是陪衬而已,大众焦点在你们俩主唱身上,谁管我们将去哪儿啊。”他打开门,楼道里铺的一长 条红地毯光是看着就惹人心烦,颜色那么跳那么燥,大清早的还让不让人有点好情绪。
夏天真阴沉着脸跟着段昱浪走,从安格身边路过时她短暂地停了下脚步,脸冲着忌司,一字一顿地说:“以后乐队这种事,你们别再找我了……我要回学校!”
房间空荡荡地只剩下两个人,烟雾仍然在房间里缭绕,隔着这层稀薄的青烟安格无法将忌司的表情看得透彻。忌司连气都没叹一下,径直走向窗边把窗户拉开,新鲜的空气不断地涌动进来,带着夏的燥 热。
楼下呐喊声越来越大,几乎要震破耳膜。
忌司掏出手机,翻出昨夜打进的号码,接通。
“喂?你好,是陈南村先生么。”忌司靠在墙上,眼睛望着一米外的安格。
“嗯,今天的头条是怎么回事?……你说有人偷听了我们的谈话?篡改?签约的事我现在还没想清楚……报纸上的事就不管了吧……嗯,那麻烦你了,再见。”
忌司舒了口气,走近拍了拍安格的头,“唉,看来就算是我走了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步,剩下那一步你也不会走来吧……”
忌司站在安格左肩的位置,两人面朝的是相反的方向。
“左边,又是左边。”安格仰起脸,雕刻天使图案的天花板周围内墙镶嵌着如同钻石般的圆形灯,如同从各个方向爬升上去希望之火。忌司的脸庞就在左侧的视角,只要再往那边偏一点点,就可以看见 所想看的全部,“你为什么总喜欢‘左边’呢?跟我走的时候也是,牵手的时候也是,从来都是左边——”
“因为左边离心,更近一些。”忌司毫不迟疑地回答。
“天,”安格像是耳聋什么都没听到一般,望着天花板出神,“为什么我看不到天呢?”她伸出手向上伸去,想要抓住什么。
忌司拉过女生的肩膀,握住女生向上伸去的手,这次力道很小,“去日本是你本意吗?”
“嗯。”
“我不相信。”忌司说。窗外的阳光在身上停得太久而烘热一片,简单而色泽鲜艳的太阳花在背后热烈地盛开,风从窗外鼓进来,膨胀的气流在手间缠绕,窗帘被掀得老高,像水底翻腾的暗流。
“如果你觉得很难开口或是有不得已的苦衷,你不讲,也没关系。”
“……”
“我不难过,所以你尽管可以走得潇洒一些。”忌司不知为什么揉了揉眼睛,“走吧。”嘴上这么说着,可没有踏出一步。
“去哪儿?”安格问,眼睛睁得更大了,大得令眼球发酸,“我们去哪儿?”
“是啊,”忌司眼神比安格更加迷茫,空洞洞地只有瞳孔随着光线不断推移而放缩着,琥珀色的瞳彩更淡了,在逐渐变亮变热的房间里更加透明,像刚泡好的茶的颜色,“我们要去哪儿。”
“呐。”安格隔了很长一会儿才又开口,她像是明白什么而郑重地点点头,“学会做自己的力量吧。”
忌司在喉咙里卡住一口气,看向安格。
“你也要学会做自己的力量啊。”安格说着掉下眼泪。
门外飘过一团又一团冉冉而升的轻烟。
段昱浪靠在门外的墙上,正一根又一根地抽着烟,吸一口香烟就飞快地短去一截。
全部都明白了。
[一一五]
地球的表面积约有5.1亿平方公里。
一个人站立时大概需35平方厘米的土地。
世界这么大,未来在无数个地方存在着。
然而,哪儿才是我们容身的地方?
我们去哪儿?
[一一六]
忌司决定一个人出面解决这次小小的“暴动”。他刚一走出别墅,就被迎面而来的鸡蛋正中额心。粘稠的蛋黄色液体顺着鼻梁往下滴,蛋壳没有完全破碎而是裂开一个很大的口,从额头上滑到了地上, 被砸过的地方正微微刺痛着皮肤。
“Flight!Flight!Flight!”Fans们自发形成整齐的呐喊,连站在屋内看着的段昱浪都觉得鼻子一酸。
“还我们Flight!”有人厉声喊着,打乱了整齐的阵脚,然后喧哗一片。
“忌司,亏我们以前还那么喜欢你!”女粉丝忿忿地从人群里探出头来,奋力挥舞着写有“安格”的牌子。
镁光灯无声地在眼前闪烁,记者们冲向前面,无数个各式各样的话筒一起朝忌司嘴边伸来。
“请问你要单飞的事是真的吗?你是否觉得Flight太过限制你的发展?”
“有人猜想你和队内成员不合,所以才决定单飞,是这样吗?”
“请问是否你一退出Flight就解散?那其他三人是怎样打算的,大家各奔东西,是吗?”
忌司用手背擦了擦脸上的鸡蛋,呼吸变得有些急促,他迅速地在脑里整编思路,缓口气才慢慢地开口回答道:“首先,我向大家道歉。”忌司往后退一步,深深地鞠了一躬,“Flight要解散的事,是真 的。”
相机一直闪烁不停。
“如果有必要的话,Flight将会在下一个记者招待会上正式宣布解散。至于大家所提到的对内成员不合,我想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笑话,我们都很喜欢对方,对这个乐队也非常珍惜,但为什么会走到这 一步……对不起,我无可奉告。”
一个牌子忽然飞来,忌司刚直起腰来不及完全躲开,牌子的一个角戳到丘脑右侧的皮肤,疼得忌司本能地眯起一只眼睛。
“啪!”随着一声惊呼牌子在地上被摔成两半,忌司扭头一看,上面写着“忌司我们爱你”。
正好从“我们”之间的地方裂开,仿佛是白骨铮铮的伤口。
接着又有菜叶子和鸡蛋飞过来。有的歌迷甚至哭了。工作人员和保安连忙疏散人群。
安格在屋内倒抽一口凉气,正要冲出去却被夏天真一拉,她面无表情地说:
“别去,你现在去帮他,会让他死得更难看。”
[一一七]
第二天。依旧是报纸头条。
“Flight承认解散,F迷轰动!”“主办方考虑取消Flight参赛资格”“最难过的人是安格?”Flight解散的事件几乎占了娱乐版的全部版面,上面附着各色相片,最令安格觉得毛骨悚然的是:自己看到 忌司回来猛地哭出来的那一刹那、忌司冷冰冰的脸不知被谁抓拍下来,而那个时间别墅大门已经完全关闭,房间里只有Flight和正处理事物的工作人员。
那些狗仔队技术真是高明。
——晚上沉默一天的段昱浪终于说了一句话。
——大家一起去吃散伙饭吧,我们要热热闹闹地吃一场,安格,你是主角哦。
武汉真的很热,初夏就已经够人受的了。聒噪的蝉鸣从早叫到晚,此起彼伏。满街的香樟树弥漫着清幽的香味,结出的黑色小果饱满得像黑珍珠,细小的叶纹在深夜里爬升到浮云之上,一轮红色满月铺 洒下皎洁的光。
一切看起来很美好,感觉像是大团圆。安格苦笑一下,自斟自饮一小杯白酒,辛辣的滋味呛得她眼圈都红了,喉咙如同烧起一团熊熊烈焰,啪啦啪啦地在胸口间跳着火花。
“以前我在救助站,到了上小学的年龄,才交到第一个朋友。”安格玩着手中的酒杯说,“她的样子和名字我都忘了。但那天我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我们俩一起玩跳房子,一个女生带着班上其他的 女生来到我们面前,那是个楼梯口,她们站在上面齐刷刷地望着我。领头的女生对我的朋友说,喂,你要么跟我们玩,要么跟她一个人玩——否则,我们都不会理你了。就那样,我不明所以地失去了第 一个朋友,那时我还不知道寂寞怎么写,只是觉得一个人很无聊,独自坐在楼梯阶上,望着以前和她玩过的地方发呆,然后一个人偷偷地哭。”安格笑笑。夏天真和段昱浪放下手中的筷子,目不转睛地 盯着她,而忌司看上去比任何时候胃口都好,也不说话,默不作声地往碗里夹菜。
“后来还发生了很多,那个时候我还很单纯,什么都不懂,不懂为什么被讨厌、被针锋相对、被背叛——只有你,天真。”安格抬眼和夏天真四目相视,夏天真意外地撩起刘海,隐隐绰绰的瞳人淡淡地 一笑,“对我真心,不会背叛,在我整个生命里面,你都是第一个。”
安格揉揉眼睛,吸吸鼻子,喉咙像硬生生卡进一个巨大的话梅,又酸又苦,无法下咽,又舍不得吐出。
“那我咧?我也对你很真心啊,我也没有背叛你真是的,你怎么可以忘记我呢?”段昱浪别过脸看着墙,眉毛向下弯曲,说话时一直在笑着,一如既往调侃的口吻,最后一句却捅破了篓子,气氛又重新 掉回低音线。垂直下落。
“当然啦,谁敢忘记你啊”安格咧开嘴笑着“嗔怪”道,轻轻推了他一把,耳边却听见水砸在桌上发出微微的声响,没分清是几声,“平常就属你最搞笑,好像从来都不会难过,别人看你都觉得你太无 厘头,其实……你在关键时刻总会正经起来,一副大哥哥的样子。说真的,虽然你总说你文化不高,但我觉得你说的话都蛮有道理的,你告诉我很多,遗憾的是我总是太没勇气去做……总之,非常非常 感谢你,格格怎么会舍得忘记你这么好的哥哥呢,是吧?”
“那当然啦,我是谁啊!”段昱浪冲着墙挥挥拳头,“哼哼哈兮”地手舞足蹈了一番,他突然扭过头来看向安格,一串银亮的线条顺着少年已经成熟硬朗的脸庞落到碗里,“只是有一句话你说错了,我 并没有‘从来不会那么难过’那么强悍,不好意思让你失望了。”
“大傻瓜!”安格伸手点了下段昱浪的额头,又安静下来。视线一点点地往那边移去,那张碗已经夹了满碗的菜,忌司夹了最后一筷子,然后放下。他端起碗,递向安格,微微偏着脑袋没有往这边看, 仍然是一句话都不说。
沉甸甸的,满满一碗,安格挑了几筷子,全都是自己喜欢吃的。
“忌司……”安格添了添嘴唇,有点干。她想了想,也许这是最后一次见面了。桌上的白布单被光照成米黄色,如此素淡的颜色她却觉得耀眼得有些眩晕了。安格在心里默念一二三,鼓起勇气说:“其 实我也有话想跟你说……很重要——”
“大家吃饭吧。”忌司重新拾起筷子,目光从另外两人脸上扫过,最后在安格脸上顿了顿,眼里的瞳光黯淡下去,琥珀色这时看起来反而像深黑色,黑幽幽的一汪秋天的深潭。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忌司闭上眼:“已经够了。”
安格想哭出声来,但往嘴里塞去的菜止住即将爆发出来的呜咽声,她整个吞下去:“你不知道。”她放下筷子,正要说出口的时候,墙角沙发上坐着的一个人引起她的注意:夏天里居然穿着黑色高领衬 衣,在餐厅里竟还戴着墨镜,桌上只点了一杯咖啡,没有半点动过的痕迹。
再在周围扫视一圈,她发觉,整个餐厅都很不对劲,从刚开始起就没有半点嘈杂的声音。
安格深吸一口气,猛地拍桌而起,声音骤然提高:“为什么要解散乐队!难道单飞真的那么重要吗?Flight能走到今天,都是大家一起的努力啊!你怎么会变成这样?以后,我绝对不会理你——不,我 们根本就没有认识过!”
一瞬间,镁光灯剧烈而频繁地在身上闪起,目不暇接,白色世界病态得令人想闭上眼睛,宁愿陷入自己的黑暗里。
安格内心打起了无法言语的绝望阵鼓,但她握紧了拳头,扳回局势让忌司重新恢复人气就只能靠这赌博般的一局了——只要他否认一切,只要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揭开事实,反问一句“要单飞的人是安 格你自己”,那么她就会一败涂地,粉丝们将大倒戈,力挺他们。
忌司眼底闪过一丝错愕,四只手指在桌面敲了一遍。他站起来,昂起下巴,邪气而冷淡地一笑,趾高气扬的神情:“是啊,我很抱歉。但是人各有志,作为曾经的伙伴我不得不奉劝一句,如果有签约找 上你,可要努力啊。”他吊儿郎当地走向安格身边,镁光灯仍在背后闪耀,随着声微弱的叹气他黯淡下神色,手搭在安格肩上,用极其微小的声音悄悄地说:“你想当作不认识我,随你。但我还是会笑 着对你说,好啊!……安格!”
忌司擦肩而过,安格支持不住把手撑在饭桌上,视线里只看得见脸边的头发,像槎桎般将自己锁在灰色空间,只有一个声道在回响。
不是“你还好吗”,而是如同肯定回答地,你很好。
安格用两只胳膊挡住自己的脸,肩膀抖动。
远处。忌司走向蜂拥而至的记者群,Flight另外两人紧随其后,向媒体宣布:
“——Fate Light到此为止了。”
[一一八]
如果。如果。
我没有坐在那条巷子里哭泣。
你也没有向我伸出温暖的手,说——把手给我,跟我回家。
流年。河水。青春之墓。
像是一首闭幕曲,在黑屏里缓慢地放出白色字幕,没有多少人愿意坐在那听着忧伤的音乐,只有电视默默地在屋子里播放,默默地在生命长河里流淌过一个个难以忘怀的名字,跳出最后的特别鸣谢,在 倒记时中自动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