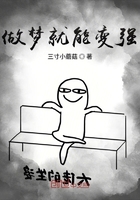第 32 章
苏月大胆,比一般的女子都要大胆的多得多。凌云当然知道。
从认识她的那天起,他便不断的领教她的大胆和主动。
回头想想,似乎他们之间的每一步,都是由她的大胆明示或暗示开始的。自己就算偶尔有些贼心,也没有那贼胆,最多只是在心里想想也就罢了。而她不同。似乎对她来讲,但凡“想到了”,那便离“做到了”也不太远了。
她可以主动请他收留,主动想要和他结为假夫妻,主动让他睡上她的床,更主动牵了他的手,主动要他跟她走,主动说她想和他成为真的夫妻,更主动教会了他情人间的那些亲密……
不管她最初的想法如何,他都不能否认,若是没有她那些惊世骇俗的大胆,二人也绝走不到现在。
现在,她又在用她的大胆在征服着他。
他被动的躺在床上,看着身上那个美到极致的女人。
她很美。他一直知道。
只是,此刻的她,更是美到惊人,就像一块让人无法亵想和染指的无暇美玉。
平素的她,若是一株端庄高贵的牡丹,那么,此刻,她却是比世上最妖娆的曼陀罗还要妖娆几分的花中之妖。
此刻,她已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无时无刻不在人前令人无法直视的安平公主,她只是一个在床笫间主动取悦着自己丈夫的普通妻子。
她凝脂般的肌肤,早已因情动而泛红。那泛红的肌肤上,渗透出点点晶莹的亮泽,合着她隐隐的喘息,就算是再理智的男人,都会因眼前的女人而难以自持。
她的唇舌勾缠着他的,容不得他还有一丝的理智说出不合时宜的拒绝的话。
她的手早已灵巧的褪去了他的衣衫,她的手指正穿过他的发丝,挑拨着他灵魂深处的每一根神经。
凌云自然是难耐的。从未经历过如此惊心动魄的情动的男人,无法不混乱而无措。他明知道这样是不对的,却又发了疯似的完全无法控制自己心底的火焰和身体的热烫。
“娘子……”她的唇刚略微离开了他的唇,他便不自觉的叫起了她。他也说不清自己想说什么。或许,就是想这么叫叫罢了。
“嗯?”她梦呓一般的在他耳畔低语,“怎么了?”
“娘子……”他实在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他想提醒她不必为了证明什么而非要这么做,他想跟她说医书有云这时虽也可以同房却需要慎之又慎,他怕自己会莽莽撞撞的伤害到了她,他甚至想跟她说他什么都不需要,请她就此住手……
可惜他说不出口。身体里的火焰让他说不出口。因为,这些话,实在太虚伪。虚伪的让人脸红。
苏月笑了。她没有再理会他,而是伸手往自己背后轻轻的一勾,一拉,她上身仅着的一件湖绿色贴身亵衣便随着这动作翩然而落……
情·欲二字,对凌云来讲当然是陌生的。而对苏月来讲,却不是。
她毕竟当过慕容轩两年多的妻子。床笫之间,该知道的,她当然都知道,甚至,比一般的妻子知道的还要更多。
她此刻只想给他一个终生难忘的洞房花烛夜,让他将来不管和谁白头到老都会清晰的记得他的第一任妻子曾经带给他的一切。
当然她这么做不止为了这样,更为了她自己。她想要和他在一起。和自己所爱的男人缱绻缠绵,本就天经地义。夫妻本是一体,她想要和他成为真正的夫妻,能不分,就不分。
她的唇缠绵而下,扫过他的下巴,直到他汗湿而颤抖的喉结。
他此刻隐忍的就像是个禁欲了一辈子的老和尚,让她觉得实在有些好笑。不知怎么的,捉弄之心竟瞬间乍起。笑了一下,她身子便微微向下,在舌尖扫过他的喉结的同时,她的手也已经径直而下……
凌云觉得自己怕是要疯了,刹那之间大汗涔涔。
他不是不想动,只是一看到她的肚子,他便什么都做不了了。
她的肚子并不算大,或许天生与她身形有关。又因孕期还六个月不满,所以并不显得沉重和臃肿,但那里面毕竟住着一个孩子。他越是看着便越是紧张,岂料反倒应该紧张的她,却主动的不像是个女人。
是她真的情动还是真的想要证明些什么?
这个念头在他头脑里只是一闪。还没闪过去,他的意识便已经全然涣散了。
任谁被人制住那要害之处,都会意识涣散到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
他粗重的喘着气,然后听见她在他的耳畔低低的坏笑着问:“相公,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凌云感受着她喘息起伏的柔软的胸膛,结结巴巴的只能吐出一个单调的字:“我……我……”
她吃吃的笑着加快了手上的动作,闲下来的一只手则轻轻搔了搔他的耳朵,娇笑道:“你什么?”
这个女人简直是专门来要他的命的!凌云咬紧了牙关,闭着眼睛,任由额头上的涔涔大汗越发淋漓。
她笑得更是得意,低头轻咬了他的唇,含糊道:“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你当然更知道,只是你不好意思说而已。没关系,就算你不说,我也知道。……从这点上讲,我也是个贤妻,你不得不承认……”
“娘子,我……你……”他拼命的想要组织语言,却偏偏像个刚学会说话的孩子一样,只能一个字一个的往外蹦。
“我知道你在顾虑什么……”她的唇舌又绕上了他的耳垂。她知道那处也是他的致命要害之一。她喜欢感受他那因她而来的难以自控的颤栗,“你乖乖的听我的,就一点事都不会有……尽管放心便是……”
……【经鉴定此处不河蟹,改吃虾……】
世人都说,人生在世,四大乐事而已。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凌云尚年轻,又第一次出远门,所以此生他原本唯一感受过的乐事便是“久旱逢甘霖”,本以为其他三大乐事只有在金榜题名之时才有可能降临,却不曾想,他的洞房花烛夜,居然来的这么突然。
他不再难受,不再纠结,神智不再迷醉。他现在清醒的很,也舒爽的很,只是有些疲累而已。
看着帐顶浅色的流苏,他在微微的喘息着,胸口依然有些汗湿。
就在刚才这件事之前,他满脑子还会时不时的跳出来薛青说过的那番话,也会时不时在想自己和她之间在隐瞒了这么许多之后到底心与心的距离还有多远。
然而,现在,他不想了。
他现在清楚的很。
不管别的那些闲人怎么看,怎么想,他们两个,才是这世上最亲密的两个人。
她愿意把她自己交给他,纯粹的交给他,而没有附带着那些乱七八糟的身外之物。——这就已足够了。
此刻,他的怀里,紧抱着的,不是什么出身高贵不能让人直视的大周公主,而只是他的妻子,大胆而泼辣的凌苏氏。她此刻没有了一切一切身份赋予她的骄傲,只是柔顺的伏在他的胸膛上,手里懒懒的把玩着他胸前的碧绿玉佩,跟着他一起等待喘息平息。
只是这么想着,他的心便格外的踏实。这便是他想要的,最简单最温暖的东西。
因为他要的一向简单,所以现在,他格外的满足,格外的快乐。乃至,从眼睛到心底,都止不住有些潮潮的满涨之感。
“你在想什么?”她突然握紧了粉拳捶了捶他的胸膛,轻问道。
凌云笑了笑,更拥紧了她些,轻吻了一下她的发顶,笑道:“我在想,我好像做了一场梦。”
“梦?好梦还是噩梦?……哦,我知道,春·梦!”
凌云脸上一红,下面的话全被堵在了喉间,说不出来。
苏月轻笑。顿了一会儿,她又柔声问道:“你可觉得还好?”
凌云当然知道她问的“还好”,指的是哪方面的,所以他只是动了动唇,却还是开不了口。这种事做出来比说出来,似乎更加容易一些。尴尬了好半天,他才总算憋出了一句话,“娘子……也还好?”
与他的羞涩完全不同的是,苏月竟毫不犹豫的点点头,大方的回答,“很好。我很舒服。你能这么温柔小心,实属不易……多谢你,卓凡。”
说着,她抬起头笑盈盈的想要看看他,却被他一脸的通红给逗得噗嗤笑出声来,忍不住身子向上了些,伸手便轻捏了捏他的大红脸,笑着逗道:“这是谁家的小公子呀,这么害羞?早知如此,是不是该给你喝点酒壮壮胆?”
凌云有些不太好意思。他知道她这是在说起当日他借酒耍无赖之事。但他更知道他是个大男人,在床笫之间被自己的娘子这么逗弄,似乎实在有些损了大丈夫的威严,因忙干咳了声,佯做正色道:“时间不早了,娘子早些睡。所谓食不言,寝不语。睡觉!我明日还要早起去书院……”
苏月见状,更是笑得难以自已,从他身上慢慢翻下,双手放在肚子上,一边笑一边还不忘踹了他两脚,“呆子!”
凌云发觉自己最近还真是好命。
本着“以道义相切磨,共人圣贤之域”的目的,淮左书院时常会延请一些名师来此传道授业解惑,与学子们教学相长,以昭彰义理。他这刚进书院没有几天,便遇上了大名鼎鼎的大儒,堂堂的国子祭酒陆元思来书院讲授《孝经》,实是激动的他一大早便兴奋异常。
说起这陆元思,可是读书人中少有不知者。他出身世代书香的仕宦之家,自幼聪明颖悟,谙熟礼乐,少年之时,便已英才秀发,舌战群儒。出仕之后,一路升至国子祭酒,编修儒家经典,堪称一代大儒,毫不为过。
陆元思到书院来,那自然是一件大事。书院招待的周到自不必说,当然是崔玄礼事事亲自陪同。
人人都夸赞着崔山长的面子大,能千里迢迢的请来这么一名名师来书院授业,岂不知,崔玄礼本人却对此有些纳闷。
陆元思和他,算是前后几年的进士,后来又同在朝为官,认识自然是认识的,只是说起熟识来,却未必了。一个忙于政务,一个钻研于儒学,平素极少有共事。自从那次谋反案之后,二人之间的生疏更是几乎连点头都未必做到了,毕竟,一个是皇帝所猜测的人,一个是皇帝最心腹的人。那种时候若能说的上话,才是怪事。
陆元思是大儒,满腹经纶,这点当然不错。他时任国子祭酒,能走出洛阳,来到扬州时顺道拜拜老朋友,自然也是不错的。当然,他愿意开堂授业,更是让人求之不得。
只是,崔玄礼奇怪的是,他陆元思真的只是来扬州过路一下么?要知道,此人一向清高,且安于书斋,又极受皇帝重用,这样一个书生,这么长途跋涉辛辛苦苦的来到这江南之地,难道,真的只是奉命巡查一下各州府的官学么?
他不信。无论如何,他都觉得,这事,绝没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