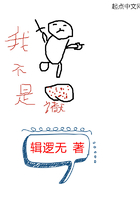这世上什么多了都不是好事,钱多了怕贼想着贼惦着,女人多了身体又吃不消,过去人家皇帝有山珍海味供养着,还有什么十全大补汤跟着,陈九有什么?顶多多吃两个西瓜,几块红烧肘子,这和他付出的劳动远远不成正比。陈九知道照这样下去迟早要完蛋。为了细水长流,在一个风高星稀的日子里陈九悄悄溜到县城,他要在这里静养几日,好好调养一下,他在原来保安室附近租了个小旅馆,闲着没事就和保安们打打扑克下下棋,保安们都劝他过了年还是回来吧,在乡下有啥意思?谁知道陈九在这一年里有多潇洒。给个乡长都不换。先不说陈九在县城里休养,单说村子里的媳妇们忽然发现陈九人间蒸发了,连个人影都找不到,她们从村东头找到村西头,连地窖和耗子洞都翻了,也没发现陈九的任何踪迹。生子媳妇认为,自己和陈九到底比其他媳妇们要近一层,陈九离开起码应该和她打个招呼,媳妇们在寻找陈九的同时,发现三刚媳妇也不见了。大家一致认为这俩人私奔了。陈九本来应该是大家共享的,现在偏偏让三刚媳妇窃为己有,你霸占了他的钱不说,现在还独吞他这个人,大家把所有的愤怒都集中到三刚媳妇身上,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到她身上。
这事三刚媳妇窦娥冤了,这女人和村里的那些媳妇不一样,她有思想有头脑。眼下她正为自己下一步的人生着手准备呢!她很清楚三刚和四刚在城里清洗抽油烟机挣不了几个钱,指望那俩人脱贫致富是白日梦。她更清楚,男人们一旦离开女人的视线,鼠胆都能变成虎胆,他们嫖妓,滥赌,偷盗,尤其偷盗最盛行,他们偷自行车摩托车下水道盖子,他们偷东西有点业余爱好的意思,有点调剂生活的意思。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村里好几个男人都被抓进了局子。跟陈九干了这么久,种西瓜那点事她已经烂熟于心,还有那些西瓜贩子,她也掌握了他们的联络方式,她和三刚四刚经营一块西瓜田,收成肯定没问题。
原来那个语文老师,现在成了邻乡的乡长,找他帮忙,在什么地方包一块沙土地,她要种西瓜。她自信,如果有相同的土壤,她一定能种出“冰糖罐”来,甚至比“冰糖罐”还可口。那以前的语文老师现在的乡长正陪着她寻找宝地呢。山不转水转,无论欠了情还是欠了钱,一生早晚都能还上的。乡下的沙土地一般都没人稀罕,如果能包出去换两个钱,也是乡长给大家办了件好事,他们在花村看好一块沙土地,方位大致和陈九的差不多,边上也是一条小河,只是面积要比陈九的大。三刚媳妇马上签下三年合同,连定金都交了。这女人办事干净利索。在回村的路上正巧碰上了从县城回来的陈九。在村口,人们看见了三轮车上精神饱满的陈九和喜气洋洋的三刚媳妇。人们朝他俩投去愤怒的目光,这二位一点感觉都没有,还喜滋滋地和大家招手致意呢。
已经农闲,陈九的身子骨调养得差不多了,他去找三刚媳妇。三刚媳妇手绢里包着从陈九的“冰糖罐”里掏出来的西瓜子,正忙于在各种子站奔波遴选,她哪有工夫搭理陈九?陈九去找生子媳妇、明友媳妇,人家也对他爱搭不理的。陈九搞不明白,离开区区数日,媳妇们没来由就变了嘴脸。是没有西瓜吃了的缘故?总不会现实到这个份上吧?陈九躺在炕上进行深入思考,忽然茅塞顿开,眼看快年根了,家家的男人就要返乡,媳妇们都准备迎接男人呢!谁还能顾得上他陈九?归根结底也是人家的媳妇,反正今年他是够本了。铁蛋和陈九一起分享着他从县城带回来的年货。他的心情还是愉快的,他知道这些男人待不了太久,剩下的好日子又归他了。陈九想,生活真是美好的,你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就得到想要的东西,当然会有一点点代价,对于陈九来讲,几个西瓜根本算不上代价。
男人们开始大包小裹往家赶,今年村长回来得最早。村长开着一辆丰田吉普,他没直接回家,而是三转两转到了陈九的瓜田上。他得到了一个可靠消息,明年春天政府要在他们村里架高铁,必经之路就是陈九那块沙土地。那可是一笔不菲的赔偿金,村长认真研究了一下政策,还找几个高人讨论过,应该比他这几年在城里奔钱的总数还多,奶奶的,想当初那可是一块猫不闻狗不啃的烂地。谁想到这山水轮流转,鸿运转到这块烂地上。让那个老光棍陈九就这么发达了?!这个打击村长实在承受不了。
红娟正在院子里喂麻雀,好多麻雀都愿意在红娟的院子里蹦蹦跳跳,红娟在地上撒了好多小米供养它们,这些麻雀一年四季都胖得像乒乓球,一群快乐的乒乓球。它们是那么肥胖那么快乐。村长问,陈九怎么放着县城的保安不当,偏偏回村里种西瓜,这个老光棍搞什么名堂。红娟心里一紧,难道村长听见什么口风了?红娟告诫自己一定要镇定,机会来了,于是她把陈九的滔滔罪行罗列了一大车出来,掘人家坟,敲寡妇门,把村里女人通通睡了一遍,坏得拉出去枪毙都算便宜他。红娟心里愤愤的,谁让你个老光棍单拣鲜桃啃,不敬我这朵昨日的红花。村长知道红娟和陈九年轻时好过,但现在看红娟这态度,村长也就明白了,这娘们是个老醋坛子。村长说通通都睡了?红娟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口误,腮帮子立刻冒出一朵红,红娟马上把脸挤出一丝皮笑肉不笑,说他敢,我们家熊熊咬死他。村长是个多老的江湖,他心里暗骂,他奶奶的,老子不在家,你小子上房揭瓦了。
村长又跑到陈九家里问寒问暖的,把陈九弄得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村长从来没对他这样温和过,村长越是谦和,陈九越是紧张。村长看见板柜上放着个玻璃瓶子,玻璃瓶是透明的,里边装的应该是酒。酒里边还泡着一根像木棍一样的东西。村长什么没见过?那是根鹿鞭。村长骂道,你他奶奶的都喝上这东西了啊?啊!此时陈九的脸已经红成了大灯笼。陈九磕磕巴巴,喝、喝了一点。
村长联系了几个乡上派出所的哥们儿,一起去走访那些“受害”的媳妇们。媳妇们被“大盖帽”吓得直哆嗦,有人号啕大哭有人捶胸顿足,有人把脑袋朝墙上撞。她们在用这种简单的方式来表达此时的复杂心情,媳妇们自虐自残,但心底始终坚持着自己的底线,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护自己,维护家庭。这也是人之常情,哪个女人会在这个时候承认是自己投怀送抱!古人说什么来着?人之初,哼,性本恶。到什么时候自我保护都是硬道理,于是警察的本子上就有了陈九施暴的各种模式,有跳窗而入的,有利用卖西瓜强行拉进苞米地的,有下半夜躲在茅房里的……明友媳妇说,陈九没占到她便宜,因为有婆婆保护着呢,明友妈很自豪,她拍着儿子的肩膀,有老妈在,陈九连根头发丝都不敢动咱。咱还在他瓜地里挣了钱了,打农药。问到生子媳妇时,这女人只是哭,眼泪像瀑布一样哗哗往下流。警察说这是受了太多的委屈,连话都说不成句了,看看这陈九已经把妇女们欺压到什么程度了?比恶霸地主还恶霸。问三刚媳妇,人家说我就是替他打工卖西瓜,别的一概不知道。因为有乡长的后台,也就没谁再多问。现在罪状足足的,不差她一个了。陈九被带走那天,他正和铁蛋啃一只烧鸡,警察把逮捕令拿给他时,陈九当时就晕菜了,流氓罪。陈九辩解,我流的什么氓?我那是救苦救难,学雷锋做好事。警察上去一脚,有跑女人床上学雷锋的吗?简直是恬不知耻的谬论。陈九要求和媳妇们当面对质,警察拿出了有媳妇们证言证词的签字。这帮狗娘们,当时怎么没日死你们。女人这东西实在太可怕了!
陈九疯子一样跑到仓房,警察还以为他要畏罪潜逃,就见他用手铐把一个留着年三十儿分给大家吃的特大号西瓜砸了个脑浆崩裂。天上飘起了鹅毛大雪,几个受害者家属把陈九打成了血葫芦。警察在一边抽烟没理这份胡子,是铁蛋拼了命地在保护它的主人,凡是对陈九有暴力行为的,铁蛋就会扑上去和他们撕咬,如果没有铁蛋,陈九的脑袋说不准要搬家了。铁蛋跟着警车跑出去老远老远,妈的,现在人的操守都赶不上条狗了。陈九眼含泪水扬起手铐朝铁蛋摆了摆,意思是在说,回吧,回家去吧!
后面的事情就简单了,人们依然过着和从前一样的日子,吃饭劳动睡觉。没有谁因为陈九的离开而改变了日子的原生态。转眼夏天到了,工人们在村长的那块沙土地上打起了地基,两年后媳妇们的头顶上就会有高铁的轰鸣了。三刚媳妇在花村的瓜田里忙碌着,明友媳妇负责给打农药,一天给五十块钱。一次生子媳妇刚好路过陈九的破房子,拄着房子的那根木头倒了,房子也跟着木头一起坍塌了,铁蛋在一堆碎砖烂瓦里趴着。生子媳妇掏出一个热乎乎的肉包子扔过去,铁蛋叼起包子朝生子媳妇甩回去,然后合上双眼。一片树叶飘飘摇摇落到生子媳妇脚面上,叶子上滴有一颗黄豆粒大的水珠,那应该不是露水吧!
本刊责任编辑 李昌鹏
【作者简介】 张鲁镭:女,曾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青年文学》《北京文学》《十月》《山花》等杂志发表作品,有小说集入选“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