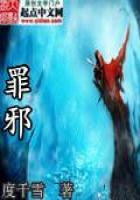一只手钻入被里,搂上她的腰,温热而清新的气息弥漫而来。他将薄而凉的唇贴上她的颈项,舌尖一舔那颗小巧的耳坠。一阵酥酥麻麻的感觉透遍全身,落苒笑着躲避,心里却虚着呢!也不知他来了多久,有没有听到什么?
“你在想什么?”嗓音秋波如水,软软地荡漾着温柔。落苒转身望着他,月色下,黑暗中,那双以往清明高远的眸子蒙上一层媚色,显得有些迷蒙。
微微蹙眉,她抬起温暖的指尖拂上他的脸,清浅的问道:“喝酒了?”
“嗯。”卫玠咕哝一声,展臂将她搂的紧些,唇微低,向下寻去,叼住她的唇细细舔吻,缓缓道:“渴了。”
呢喃完,他灵巧的舌尖便撬开她的唇齿,寻到她的舌含进嘴里,大手更是顺着那敞开的衣襟往下伸去。落苒一惊,正要推拒,他却停止了动作,只是伏在她的肩头,不一会,细细的呼吸声传来,竟是睡着了?他这些日子都在做什么?竟是这么累么?落苒在他眉心一吻,调整了下位置,缩在他怀里缓缓睡去。
这一觉,她睡得安好,唇边始终挂着浅淡的笑容。
醒来时,天也大亮,一阵欢快的鸟语伴着花香而来。
下意识的,落苒伸手往旁边摸去。
人不在,榻已凉。
落苒缓缓拥被坐直身子,这时卫玠派来伺候她的婢子步来,立在门前问了句,“女郎,可是醒了?”揉了揉眼,掀背而起,踏上木屐,吱呀一声打开木门,望着门前的婢女问道:“郎君呢?”那婢女的垂首,两手交叉放于腹前,恭敬的道:“郎君一早便出门了,出门前,郎君吩咐过,若女郎闷了,可装扮一番出去走走,不过必须带上护卫。”
落苒点了点头,即便他不说,她今日也是打算出去的。落苒由那婢女伺候着换上一身布衣,戴上斗笠,随意的吃了些东西,带上三名护卫,出门而去。
他们所乘的马车是很简陋那种,为了不引人主意,三名护卫都装扮了一番。现在已是阳春三月,草木抽丝发了嫩芽。建康里的儿女们,一个个着上了薄薄的春衫。薄粉敷面,颜如渥丹,倒成了这建康的一景。落苒掀开窗帘一角,淡淡的感受着这繁华。
就在她怡然自得时,前方的一辆豪华马车忽地停了下来,紧接着便见一名宽衣大袍的男子跳下马车,对着挡在路间的一块大石伏地痛哭,惹得不少人望来。
落苒望着此人举动大奇,不禁向驱使马车的护卫问道:“此人是谁?怎的对着一块石头哭。”她想,卫玠这些护卫都是常驻建康的,比起自己定是所知甚多。
果然,那护卫嘿嘿一笑,边驾车边回头说道:“这人是安平张氏的张亢,是个痴人。”
“那他为什么伏地痛哭?”落苒越发疑惑了。
“不为什么,只是因为前面的大石挡住了他的去路,车过不去。”说到这里,他又补充道:“这人说来也怪,其母逝时,本应忌酒忌荤,他却依旧下棋吃饭,喝得酩酊大醉。”
落苒愣了,不过也就是仅仅一秒便也想通了。
她放下车帘,喃喃的道:“痴到无望才是狂,其实他并不是不痛苦,而是痛苦到一定程度心已僵硬麻木。否则也不会在下棋时迟疑,吃饭时只顾饮酒。借酒消愁愁更愁,因为愁得太重,伤得太深。”张亢悲伤绝望的是这个世道,战争摧毁了一切,而依然屹立于文士心目中的不倒山峰,是信念,这个世道终将清平的信念。
他们时常回忆或向往一些美好的生活,便是求而无望才是痴,所以他们宁愿醉生梦死,夜眠花柳。人总会有迷茫的时候,如同困坐于黑夜,不知时光的流转,年华消逝。蓦然回首,细数往日的种种不如意,无法尽言委屈,于是扪心自问:倘若人的灵魂似莲花般纤尘不染,是否就不会有悲怒无奈;如能像莲花般无欲无求,是否就不会有爱恨情仇。佛从不会有这种困惑。
落苒轻轻一叹,“都是痴人。”那护卫显然未料到她一个小姑子竟有这番见解,惊讶过后便是满满的赞赏,他想:这个姑子与时下的姑子确实有些不同的,难怪郎君喜爱于她。
就在马车就要拐入一条窄巷中时,忽地,车身一阵摇晃,闭目兀自想心事的落苒一惊,赶忙扶住车缘,以免自己掉下车去。马车渐渐平稳后,那驭车的护卫惊慌的问道:“女郎,你可有事?”
落苒唰一声掀开车帘,道了句无事,正想跃下马车捡回落地的斗笠,却是一道马鞭呼啸声风的挥来,落苒一惊,身子向后倚去,险险的躲过一鞭。这时,三名护卫齐刷刷抽刀,跃下马车,将落苒护在身后。那挥鞭之人似是没想到这看上去并不怎么样的马车,竟跳出这么三个精勇的护卫,只是稍稍一疑,只见他高高的翘起头,傲慢的吼道:“好个不长眼的东西,竟然连王府的马车也敢撞,快些上前给我们家贵人赔礼,否则,要你们好看!”
落苒惊魂未定的胸口上下起伏着,她狠狠一挑眸,嗖的转首望去,在对上她那双阴森的目光时,方才嚣张的男人吓得咽了咽口水,往后退了一步。
这是一个莫约三十的中年男人,矮矮胖胖的身子,一脸的不屑傲慢。
听到那胖子的话,卫玠的护卫怒了,只见三人齐刷刷的往前跨步,喝道:“好大的胆子……”
只是说到这里便被落苒拦住了,她转首去望马车的标志,却是车帘一掀,钻出一名妇人。此人方才露面,落苒瞳孔便是猛地一缩,她狠狠的盯着眼前之人。杏面桃腮,淡扫蛾眉,眸含秋水,那纤纤弱弱的身姿丰满了些,改梳妇人发鬓的她,多了些韵味与风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