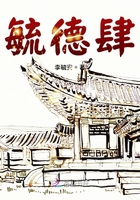我沉下脸,质问:“你这话什么意思?”
薛彩衣止住了笑,却还是浅笑着,略有嘲讽之色,缓缓道:“你还记得那日我赠你的红枣桂花羹吗?”
我点头。
“羹里置了你爱的酸梅。”
我复点头。
她慢慢道:“你可知那并不是酸梅,而是胭脂果。”
胭脂果?是了,同是酸食,况且碾压了也看不出,只是胭脂果并无害。
“他给你吃的,也都是胭脂果!”她忽然提高了声音,双眼瞪着我,脸上有一抹诡异的笑容,令我看不透。
他?
必是赫连墨了。
可是胭脂果究竟有何用意。
薛彩衣似并没有继续说下去的意思,只捡起来一旁的帕子放进手里,继续绣着,再为抬头瞧我一眼。
见她再无用意同我说话,我便离去。
出了她的寝宫,我站在殿门口,伫立良久。
仔细琢磨薛彩衣说过的话,却久久未能有个定论,只能一路猜测着回了莞宠殿。
后来,我问过暗香,他二人在外久了,也是见多识广,我便将彩衣同我说过的话一字不落的讲给他二人听。
胭脂果,乃是一种酸果,旁人吃些倒也无妨,只是吃的过多有伤脾性。这些都不碍事。
但我却是有身孕之人。
胭脂果,孕妇常食用,便会导致小产。
况且常以酸梅诱之,太医令自也查不出缘由。
听了暗香的话,我长长吁了一口气,难怪彩衣会有那样的神色和反应,难怪…
小桌上给暗香备了两盏茶,也给我自己备了一盏,我吩咐他们说完话便以茶润口。我伸手探了一杯茶,端在手上,竟未察觉茶已凉透。
赫连墨呵赫连墨,我竟未料到你的心思如此深远,嘴角上扬出一抹笑,大抵带着微微嘲讽的神色。思前想后,出了赫连墨,有这样心思的,必然还有西烽了。
他二人都以酸梅置在我药汤中,酸梅皆是胭脂果。
西烽也曾想,不要越国。
正如今日,赫连墨害我失去了他第二个孩子。
这一生未想过要负任何人,唯一负了的便是子期了。可身旁人却一一负我,先是若素,再是安姑姑,再到西烽,甚至是赫连墨。
我将凉了的茶一饮而尽,发觉竟是那样的苦口,这雪地白毫,再没了先甜后苦的一味,从入口只下喉,竟是苦涩。
可到了腹里,竟又生出暖意来。倒也有些奇怪。
将空了的茶盏狠狠摔到地上,碎了一地零散,也险些扎到了自己,我望着一地的碎渣,心中也有了决意。
“暗香,先前说过的计划,今日便开始吧。”我蹙着双眸,凌厉的望着他二人,这一日我自己怕也等了许久了。
不足一月,朝中便又有了大变动。
先前薛凡被禁足,倒避了不少嫌,矛头皆指向了吴安王。原本他是藩王,当年拥立赫连墨登基,原本便是功高震主了,朝中大臣多对他不满。
几次削藩也被打压。
前几日,有人从吴安王府邸搜出了他与旁人私通的信函,更是污蔑他私通西景,有意覆灭我南桀王朝,白纸黑字,亦有他的玺印为证,既是想赖也赖不掉的。
我亲自书信一两封,叫人偷偷递给了吴安王。
其一,我的字迹本就与赫连墨相像,刻意为之,更是瞧不出破绽来。
二则,书信中称我有意表明身份,重夺女帝之位,愿吴安王相助。而我模仿赫连墨的字迹,向吴安王表述的,却是明目张胆的要除了他。
这两封信,便叫吴安王自乱了阵脚。
薛凡隐忍待发,吴安王蠢蠢欲动之事带兵入了宫,薛凡便带兵包围了王府,左右牵制。一举将吴安王拿下。
其间细节我无从得知,也不想花费太多心思去知道,只知赫连墨运筹帷幄多日,也不枉他费尽心思,听了我的,扳倒了吴安王。
夕日情分,不复在。
得知吴安王被押人大牢,兵符更是不翼而飞,赫连墨恼怒,和月更是得了消息,急急的跑到了我宫里来,一进殿便跪下,哭喊着求我:“请王妃解救家父!”
要除掉吴安王,本就是我的意思,如今和月这样巴巴的来求我,倒叫我有几分为难,我曾允诺护她周全,却为允诺要护着她父亲。
我扶起她,屏退了左右,拉着她倒塌边坐着,慢慢道:“你可知你父王犯了什么罪?”
“父王怎会!”她立刻反驳,随后又垂了头,懦懦道:“父王当真不轨?”
我点头,缓缓道:“他不轨,早在三年前便有了,否则又岂会扶持赫连墨而颠覆我?于情于理,我才是继承南桀最佳的人选,亦是先帝的嘱托,可他仍是拥护了赫连墨。”
“和月,其实你何尝不知道?吴安王将你嫁给赫连墨,不过是为了表示彼此一心,可事实上,他未曾考虑过你这个女儿的感受,你不过是颗棋子罢了!”
和月低了头,暗暗咬着唇,不说话。
“其实今日的情景,你早该预料到了,功高震主,何况最近吴安王确有不轨之心…”我顿了顿,复道:“他必不能保了。”
和月听了我的话,身子一颤,忙站起身,又重重的跪了下去,仰头瞧着我,满脸的泪痕苦楚,凄凄道:“妾身只求能保父王一命!”
我正了正身子,低眉瞧着跪在地上的和月,便也不去扶她,任由她跪着。
“你若能跪上两个时辰,我兴许能帮你。”我浅浅一笑,起身向内殿去,缓缓上了床榻小憩着。
原本,赫连墨顾念以往的情意,也会留着吴安王一命,遣回封地颐养天年。可只要他活着,便会是祸害,难保会东山再起。
可这样的话,我是断不能同和月明说。
也顾忌她曾帮过我。
也未曾想她真的会跪上两个时辰,我小憩醒来,正好浣儿端了一碗温热的粥来给我饱腹。最近食欲不振,也吃不下什么,只能吃些粥,许是小产之后身子不爽的缘故。
我吃了几口粥,才发觉和月仍跪在那儿,卑贱谦恭的模样,没有半分王妃的样子。一时有些不忍和心软。
我挥了挥手,叫浣儿去将和月扶起来坐着,又叫倒了一盏茶给她。
“你倒真在这儿跪了两个时辰!”
许是因为跪的久了,她脸色有些苍白。虽说我殿内炭火充足,但地面冰冷,她跪了这样久必定伤了膝盖。寒气入体。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低声问我,声音也是有气无力的,“王妃可愿救爹爹一命?”
我微眯了眼,缓缓道:“我自会护你周全,至于你爹爹,我尽力而为。”
“多谢王妃!”她说着,捧着茶盏,又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踉跄着险些摔倒了,好在浣儿扶着她。
我的话,左不过也是敷衍她,既是赫连墨留吴安王一命,我亦不会。
“今晚我便去大牢看望吴安王,也顺道想了法子如何救他,你赶紧回宫去吧,免得叫人说闲话。”
和月果真信了我话。匆匆回了自个的寝宫,也是怕旁人以为她和我有嫌隙,故而能够救助吴安王。
薛凡官复原职,禁足亦被撤销,恢复了以往的声誉地位,更甚于从前,只经此一役却也对赫连墨心生芥蒂了。薛凡复位,自然薛彩衣也恢复了玉王妃的封号,一切封赏依旧。
赫连墨特地叫伯安来向我说明一切,怕我心有不忿,气他不为我们未能出生的孩子报仇。我只淡淡一笑。既已知道这个孩子不能降生,皆是因为他赫连墨,我又何故再做样子。
便叫伯安回了赫连墨,我懂他的心思。
我若善解人意,他心中必定更加愧疚。
面上的功夫还是要做足了才好。
因应了和月,也要做做样子,隔了几日,我便前往王宫大牢,自然是得了赫连墨的许可。
吴安王被囚在单独的暗室里,与旁人都隔开来,我是自个进去的,叫浣儿守在门口,也免得隔墙有耳。
虽落魄至此,但吴安王好歹曾是一方藩王,即便是落魄,却仍有将王风范,他坐在草席上,不卑不亢的,就连他的服侍,也还是他身为王爷的服侍,并没有换下。
见我来了,他的神色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淡淡的瞥了我一眼,又阖上眼养神,看样子并不想搭理我。
狱卒搬了一张椅子给我,叫我好生坐着,随后便退了出去。
我坐在椅上,垂着手,神情无异,也当是寻常的聊天一般,淡淡道:“王爷这几日过的可还好?”
“托王妃的福,老夫好的很。”
我微微挑眉,他话里的意思,大抵是知道此事与我脱不了干系。想必自太妃薨逝,他早已断定太妃之死必有我的原因,只苦苦寻不着证据。
况且他与薛凡正是水火不容之时,他为大局着想,只能先将个人恩怨抛诸一边。只是不曾料到,赫连墨竟这么急着要扳倒他吧。
“你和阿墨的心思,左不过都是私心,今日之景,早该有所预料。”
吴安王缓缓睁开眼,脸色有一抹悲戚的神色,却又立刻换上一副淡然的表情,似不愿让我看到他不甘的神色,只淡淡道:“你既看得如此通透,怎会甘心屈居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