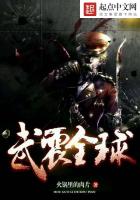现在来说拉美文学。具体地说是拉美文学中的“黄金爆炸时期”,是拉美文学中的“魔幻现实主义”。对于古典的拉美文学,中国最早熟知的就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和流浪汉小说《小赖子》。准确地说,对于我个人,拉美文学最早让我有所了解的是以上两部一个巨大、一个较小的长篇,其他可以说基本空白,完全无法和你所知的俄罗斯文学与欧洲的法国文学相提并论。但是,从上世纪的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到今天的当代中国文学,二十几年来,拉美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或强或弱,或浓或烈,一直持续不断,仿佛铁轨伴引着轮子前行一样。在影响最为强烈的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期,拉美文学在世界上的爆炸,轰鸣声在中国文坛的巨响可为振聋发聩,令中国作家头晕目眩。其影响之剧,可能超出世界上任何一个时期的任何一个流派、主义和文学团体,对中国文学造成的振动基本和地震或火山爆发一样。这儿,最有代表性的作家自然是马尔克斯,对中国文坛影响最大的作品自然是《百年孤独》。随之其后的,是他的《霍乱时期的爱情》、《一件事先张扬的谋杀案》,巴尔加斯·略萨的《绿房子》、《胡利亚姨妈与作家》、《城市与狗》、《潘达雷昂上尉与****女郎》,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阿斯图里亚斯的《玉米人》,卡洛斯·富恩特斯的《最明净的地区》,伊沙贝尔·阿连德的《幽灵之家》,还有博尔赫斯那些精妙的短篇和散文,聂鲁达那些情感如火山一样的诗,卡彭铁尔那些关于“神奇的现实”的理论和小说。
以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为例,因为这部小说的开头是充满着时间跳跃的叙述:“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就这样的一句叙述,在当时的中国作家中,不下十人的十部小说的开头,也同样一字不差地用“许多年之后——”如何如何,去作为自己小说的开头。一些聪明的作家,即便不把“许多年之后——”或“多年之后——”用在小说的开头,也会用在小说故事的中间地带。直到今天,我们读一些富有探索意味的小说,仍然可以读到这样的句式和叙述模式来。就今天看来,这样的借鉴与学习,似乎有些幼稚,有些可笑,但也正说明了拉美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之巨。而在当时,这样生搬硬套《百年孤独》的叙述模式,却不是肤浅之举,而是一种创新的时尚,是一种探索的标志。从现在回忆的角度去看那时的文学,我们虽然有些把别人的果子摘来直接挂在自己文学之树上的嫌疑,而不是借来人家的种子,埋入自己的土壤,长成自己的树木,但经过二十几年对拉美文学的进一步融合、贯通、消化和转化,已经可以说,无论是俄罗斯文学还是欧美文学,比起拉美文学来,都没有中国作家更容易理解、消化和那么巧妙地本土化、个人化的借鉴与整合,并使之完全的中国化、个性化地成为中国土地中的种子与花果。
第三,几个对中国当代文学影响深远的外国作家。说到对中国当代文学最有影响的外国作家,大约每个当代作家都能说那么一个、几个自己最喜欢的作家和一部或几部自己最喜欢的作品,但就广泛性和深刻性而言,我以为当推以下作家他们的作品:卡夫卡《变形记》、《城堡》和《审判》。尤其是《变形记》和《城堡》很少有当代作家没有阅读过,如很少有当代作家没有读过《红楼梦》一样。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集《小径交叉的花园》。凡喜欢博尔赫斯的作家,大约对其代表作《小径交叉的花园》等精巧之作,都会如数家珍,爱不释手,甚至把其当做“床头书”,寝前必读。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这是中国作家在谈其文学和国外作家时,必谈必言的一部书,如同当年“**********”时,我们只要讲话,都必须引用毛主席语录一样。接下来,就是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八月之光》和《我弥留之际》。在这一行列中的作家,我们还能说出一串作家的名字和作品,如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凯鲁亚克的《在路上》、罗伯格里耶的《嫉妒》、杜拉斯的《情人》和伍尔夫的《海滩》等等。但论影响之甚之巨的,还是前几位。
先说卡夫卡。卡夫卡的写作和在全世界的影响,在二十世纪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伟大的作家并不需要太多作品,重要的是你那少量的作品是否确实伟大,确实在世界范围内,有其真正的独创性。卡夫卡以其有限的作品,给二十********带来的影响,可说至今无人能比。在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中国当代文学,随着一场政治浩劫的结束,进入了黄金发展时期,什么伤痕文学、知青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新探索小说等,这样的文学波浪一个接着一个,一波接着一波。然而,在时过境迁的三十年后,我们重新来回顾这些时,会发现伤痕文学、知青文学、改革文学,也包括那一时期与中越自卫反击战相关的军事文学,其实完全是文学史的意义,而没有太多的文学意义。但其间的寻根文学和新探索小说,却给后来二十年的中国当代文学注入了很大的活力,尤其是从八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代初的新探索小说,几乎可以说改变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根本面貌。这一阶段的代表作家是人所共知的余华、苏童、格非、孙甘露、叶兆言等。就这批可敬的作家而言,他们受影响更大的是博尔赫斯,但最初点燃了他们探索之火的,应该是卡夫卡。对他们和许多作家影响深远的,也同样是卡夫卡。其中以余华为例,最早给他带来广泛影响的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仔细阅读这篇小说,会发现它和卡夫卡的荒诞性有着完全的因果联系。小说中刚满十八岁就要出门闯荡的孩子,所遇到的荒诞世界和荒诞事件,让我们想到《变形记》和《城堡》这样的小说。二十年之后,在余华写了许多小说,在他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已经确立了在当代文学中的经典之后,余华的新作《兄弟》,在市场上大获成功,但却在文学圈内,毁誉参半。无论别人如何评价这部小说,但其中的荒诞性,却让我们再次看到他和卡夫卡的某种关系。由余华作为这批作家最具代表意义的作家,我们不难看出卡夫卡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之深、之广、之久。这也包括莫言小说中的荒诞性与卡夫卡的某种关系。说到卡夫卡,我想当代作家,其实都乐意接受他和自己的写作有某种联系的判断,因为卡夫卡影响的不光是中国当代文学和作家,他还影响了拉美文学中的马尔克斯那样的大作家,所以,中国作家其实是以自己的写作受到了卡夫卡的影响为荣的。
再说博尔赫斯。博尔赫斯其实比起卡夫卡和马尔克斯,我以为,并没有那么伟大,但是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却丝毫不逊于他们。因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开端,是要从八十年代说起的。而八十年代之初的文学黄金时期,从根本上说是受制于中国的意识形态,为了尽快摆脱政治对文学的影响,那时候以李陀为代表的批评家和年轻的作家们,不期而遇地掀起了一场所谓的文学革命。在小说的形式和语言上,开始了大胆的借鉴与学习。而博尔赫斯的小说语言,恰恰充满了诗意和神秘,没有丝毫的社会意识的影响,完全是个人化的文学情思和语言叙述,这正契合了当时中国文学急求变化的需要。因此,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那时中国新探索小说的模本。我们去看那时余华的《现实一种》、《世事如烟》、《鲜血梅花》等,去看格非的《褐色鸟群》、《青黄》,去看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和《罂粟之家》,去看孙甘露的《信使之函》、《访问梦境》等,就是文学发展到了今天,已经千变万化,丰富多彩,他们那时的小说,仍然给我们在语言上带来一种神秘和美,带来如梦境般的诗意,犹如我们阅读博尔赫斯的小说,也许我们不明白他迷宫般的情境设置,不懂他镜子的那种意象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但他语言的魅力,却依旧使我们可以痴迷和沉醉。
文学就是这样一代影响着一代,他人影响着他人,在发展和变化。当年那么多的作家,痴迷于博尔赫斯,这位阿根廷的盲眼老人,但今天,博尔赫斯似乎已经没有往日在中国作家那么光辉,没有如卡夫卡、福克纳、马尔克斯那么深远持久的影响,就连当时倡导并推动了这一文学思潮的李陀先生,说起博尔赫斯,也说他是世界上的二、三流作家。但由于格非、苏童、余华们的写作,在中国当代文坛持续的变化和影响,从而也使博尔赫斯的影响,虽然声细音微,但却依然存在,依然在影响着一些年轻作家的写作。
回头我们来谈马尔克斯。马尔克斯是与博尔赫斯同时走入中国新时期文学的。马尔克斯在中国文学中的登场,是伴随着“拉美文学爆炸”这一巨响的概念而在中国产生了巨大的轰鸣。在八十年代中期,马尔克斯没有博尔赫斯在中国文坛那么“细雨润物”,没有那么多和广泛的追随者,但凡接受马尔克斯的那种“魔幻”理念者,在之后都有很大的文学造化。现在,来回头观望这一有趣的文学现象,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值得玩味的一个事实,那就是拉美文学的这两位作家:博尔赫斯和马尔克斯。前者出生于1899年,年长于后者整整三十岁,但前者给中国文坛带来影响的却是年轻一些的作家们,主要是集中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群;而后者出生于1928年,给中国文坛带来影响的却是年龄较大一些的作家,主要集中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们和1950年前出生的个别作家们。受其前者影响的作家,不仅年龄小,而且也少有乡村的生活背景,主要文学成就,中短篇较为明显,这和博尔赫斯一生不仅不写长篇,而且还压根瞧不起长篇有一定的关系。而后者,受其影响的作家不仅年龄偏大,而且都有其鲜明的乡村生活背景,主要成就,在长篇上较为突出,和马尔克斯有其相似之处。比如张炜早期的《古船》、近期的《刺猬歌》,陈忠实的《白鹿原》,李锐的《旧址》、《万里无云》,莫言的《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山南水北》,贾平凹的《高老庄》、《怀念狼》、《秦腔》,等等,我们不能说这些每一个我都十分尊敬的作家,他们和马尔克斯有什么关系,但他们的这些作品中,都或多或少地呈现着“魔幻现实主义”中那种“神奇的现实”,却是一个事实。而在这一批顶天立地的作家中,对“神奇的现实”最有领悟的作家自然是莫言。甚至我们可以说,是莫言让拉美文学与中国本土文学最早发生了联系,而且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
早在八十年代中期,莫言誉满天下的《透明的红萝卜》和《红高粱》,如让大家感受文学爆炸样,感受到了一种往日文学中没有的文学元素,他的那片“高密”土地,让人感到神奇、有力而不可琢磨,其中所充蕴的不可磨灭的生命的活力,给当时的中国文学带来的不是惊喜,而是不知发生了什么的震撼。而带来震撼的原爆力,自然是莫言的创作,但给莫言的写作带来启悟的,正是拉美文学,正是马尔克斯和他的《百年孤独》及他的一系列创作。在之后的许多年里,无论是莫言的创作,无论是拉美文学,一直对中国文学,保持着旺盛的影响。直到今天,我们从任何一位优秀的当代作家中,无论是正当年轻力壮的中年作家,还是风头强劲的青年作家,几乎我们从任何一个人的口中,都可以听到大家对马尔克斯和他的《百年孤独》的尊重和崇敬,这种情况颇似于我们大家对《红楼梦》和曹雪芹的敬重样。
这其中,也包括我自己。
第四,今后中外文学关系的趋向。中外文学的关系,绝不会如国际外交关系一样千变万化,瞬息不定。这是一个稳定的,平衡的互动关系。外国文学影响着中国文学,中国文学也或多或少、也许是微乎其微地影响着外国文学。也许,我们在今后,可以在世界上做一个经济大国,军事强国,但我们的文学,却很难同经济同步发展,成为世界上的文学大国。文学如果可以随着经济发展而发展,那文学就不再是文学了。文学的特殊性,就在于它的文化性、连续性、传统性,不会在一夜间突然崛起,更不会在一夜间突然消失。中国文学要想在世界文学中有显著的地位,还需要很长时间,还需要那么几代作家的写作努力。还需要我们写出真正伟大的作品,需要每个作家把自己的写作个性和潜能,彻底地释放出来,发挥出来。在这个写作过程中,还需要真正从外国文学中汲取营养,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从中国的现实与历史中打捞文学精神的骨髓。
说到进一步从外国文学中汲取营养,我认为我们应该重新认识俄罗斯文学的价值和拉美文学的价值。为什么说把鲁迅和托尔斯泰比较时,会有一些批评家感到鲁迅的伟大没有托尔斯泰的伟大那么宽广和仁厚?没有托尔斯泰那样仁慈和充满无比的爱?就是因为俄罗斯文学是一种伟大的情怀文学,他们在那个年代的每一位作家,几乎都对他们的民族和俄罗斯大地充满着细腻而伟大的爱。我们去看《静静的顿河》,去看屠格涅夫的小说,去看托翁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对他们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片土地,每一寸山脉的森林与河流,都是那样的呵护和关爱,悲悯和同情。而鲁迅不是这样,鲁迅爱润土,同情祥林嫂,但他也多少有些对阿Q的冷笑和嘲讽。我们梳理鲁迅笔下的人物,他可怜他们,也恨他们,但给人的总的感觉是,恨大于爱。就文学而言,最深刻的恨是一种爱,但最深刻的爱,决然不是恨。三十年代文学,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辉煌时期,我们必须承认,那一时期的文学,还无法和俄罗斯文学相提并论。这不是说我们那一时期没有伟大的鸿篇巨制,最好的作品大都是中短篇和散文,而是说我们那一时期的前辈、大师们固然伟大,但从作品之情怀而言,没有俄罗斯文学那么伟大的充满爱和情怀的文学。
情怀是不可以借鉴的,但它是可以培养的。所以,我想,伟大的作家应该有伟大的情怀。应该去重新认识俄罗斯文学和他们的文学情怀,以培养我们可以超越前辈的文学情怀和爱人、爱土地的那种诗性的情思。
重新认识拉美文学,是基于二十世纪的欧美文学,太过讲究技术和技巧,甚至某些文学流派,完全是在讲究技巧、个性的基础上兜圈子,而这时的拉美文学,在个性、技巧的基础上,却始终没有脱离拉美那块土地的现实和历史。无论是魔幻现实主义,还是神奇的现实,他们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也都绝不脱离作家生存的土地、社会和现实。兴起于中国文学八十年代中期那一浪潮的新探索小说,无论是作为文学史的意义,还是作为每个作家的文学意义,都是有着相当的价值,但之后余华、格非、苏童的写作转向,大约与他们所处的现实的思考不无关系。拉美文学,既不丧失每个作家个性的追求,又都有其鲜明的探索和创新,比如巴尔加斯·略萨对结构的不懈努力和创造,比如卡彭铁尔在小说中的时间观等,但他们的小说,自始至终,都没有脱离现实这块土壤。如何让文学更为个性地、深刻地抵达现实的心脏,这是当前中国文学最致命的软肋,也是我自己在每部小说的写作中,最为痛苦的所在。
所以,我想,我们的写作,至少是我的写作,在今后与外国文学的关系这一点上,应该重新认识俄罗斯文学和拉美文学这两大世界文学的重镇之地,双脚踏在自己脚下的土地上,大地上,但其目光,要越过这块土地,多看、多思外国文学,重看重思俄罗斯和拉美文学。
2008年3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