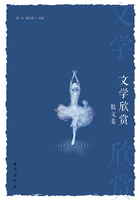因为,自己少年时期满脑子都是个人的乌托邦理想,和同类易聚,同根易亲一样,待我长大之后,尤其是经过了十年“****”,忽然之间,又跨入了三十年的中国的改革和开放,这就让你能更切实、亲近的体会到了,中国社会的乌托邦性。
原来,新中国的现实和历史,也是一个乌托邦接着一个乌托邦。
关于新中国历史,从1949年至1978年的这三十年时间,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思想家和哲学家,可以从各种角度去解读、剖析和述说,但我作为一个从小就充满乌托邦理想的小说家,其感受就是一句话,那三十年里,我从出生到长大,充满着理想乌托邦,而我的亲爱的祖国,也和我一样,和一个幼年的孩子样,充满着理想的乌托邦。我的理想是当皇帝,可这个民族的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和我当不了皇帝一样,共产主义也不会那么容易就实现。我为了当“皇帝”,在部队做过了各样的事情,荒诞的,可笑的,令人作呕的。比如,在学雷锋运动中,我为了获得领导的表扬,曾经在晚上睡觉时,把连队的扫把藏在被窝中,这样第二天军号一响,我就可以扫地了;而没有扫把的战士,就只能站在边上看我扫地了。其结果,就是在晚上连长、指导员的评比中,我受到了表扬。受到了表扬,我就“积极”了,就距离提干、入党近了那么一点点。别忘了,入党和提干是一个开始,是万里长征中的第一步。还必须知道,“学雷锋”并不单单是“好人好事”,他是社会主义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道德积累,是共产主义的道德建设。这就是说,你个人乌托邦的实现之路,必须在新中国乌托邦的实践中实践和进行。可是社会的乌托邦,前三十年是实现共产主义,为了实现共产主义,中国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革命、斗争、批判、运动,这中间不知中国死过多少人,流过多少血。然而,中国终于从那个乌托邦的梦境中醒了过来,开始了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今天,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了三十年,经济上确实蓬蓬勃勃、发展迅速,有钱的人确实过上了好生活,没钱的人,也确实不会再像“************”时期样活活饿死。关于中国的富裕,关于中国经济的强大,关于中国的未来,因为我儿时对当“皇帝”的乌托邦理想没有实现,没当上“皇帝”,就没有能力把握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可是,经过了这三十年,我目睹了这个国家的变化。我为这样的变化而欣慰。然而,在这种变化中,我隐隐地感觉到,中国是从一个“乌托邦”中醒来,又走进了另外一个“乌托邦”。
这个新的乌托邦所带来的灾难,我以为已经开始在中国社会中显出端倪。比如近年中国的沙尘暴、大台风,冬天时南方的大雪灾,而北方却少有飘雪。九十年代连续出现的大洪水,新世纪频繁出现的矿难和“黑砖窑”事件,还有什么非典、禽流感、口蹄疫、手足口病……关于这些,我已经谈了很多,举了很多事例。这些事例,从表面看,有许多的“偶然”成分,但把这些“偶然”合起来时,有没有必然呢?这种必然和今天中国当下的唯经济论,和十三亿人口的“致富”乌托邦梦境,有没有关系呢?是不是一种新乌托邦梦的病症,在一个民族身上发作的开始呢?
还有人心。可怕的人心。现在,在新的富裕强大的乌托邦的梦境里,我们似乎只剩下了个人私欲主义。
关于新的乌托邦梦境,我想有两种情况,一是我是杞人忧天;二是大家都还在梦中没有醒来。在生活中,我愿意是前者。在写作中,我注重后者,哪怕我看到的是片面的、错误的、偏激的,但它是我个人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是我个人面对现实,需要在自己的作品中发出的声音。这个“个人的”,是写作中最为重要的。所以,我的写作,就一直是在乌托邦笼罩下的个人写作。我的语言、结构、叙述、故事、人物、形式等等,包括我对现实的认识和写作态度、写作立场及文学的表达与追求,其实也就是一句话:乌托邦笼罩下的个人书写。
2008年2月6日五、当代文学中的中外关系(原为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文学社的
演讲。)
阎连科
同学们:
今天我们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就当代文学中的中外关系这一话题,进行一次漫无边际、随遇而安的漫谈,大家有兴趣者可以坐而听之,无兴趣者可以起身走之,似乎有兴趣但又兴趣不浓者,可以在这儿开小会、发短信、打电话。言而总之,自由高过一切。文学只是民主与自由这棵大树上的一枝一叶,有则绿之,无则依然绿之。
第一,先谈一下文学之源。树有根,水有源,谁都知道文学是虚构的,但它不是空穴来风,不是空中楼阁。文学是写作者生活经验体悟的个性的情感式表达,是来自写作者对阅读启悟的补充和修正,是建立在生活经验和阅读经验之上的想象的叙述。一部好的文学作品,比如一部伟大的小说,如果没有生活经验、阅读经验和建立在二者之上的文学想象,就如同高楼没有根基,三者中缺一不可。缺一就无法三足鼎立,无法平衡和稳固,由此可见阅读在文学中的三角一柱之作用。
由此也就可以论断,没有阅读,事实上也就没有今天的当代文学。
就阅读而言,从文学作品的阅读上说,阅读也有三个来源:一是古典文学;二是现当代文学;三是外国文学。
就中国当代作家来说,没有人不阅读古典文学,没有人不阅读现当代文学,没有人不阅读外国文学。就中国目前站在最前沿的作家来看,有人没看过《红楼梦》,没看过《三国演义》,但他不会没看过外国文学。外国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最重要的阅读之源。
三十年代那些群星灿烂的作家们,他们几乎个个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在“五四”时代,是外国文学的种子,在中国土地上的播撒,才开出了那一时期光芒四射的文学之花。如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巴金、老舍、茅盾、曹禺、郭沫若、冰心等,这些被我们的文学史尊为大师的前辈,在他们的作品中,无不散发着外国文学本土化之后的芳香和气味。在他们本土化的写作过程中,无不显示着国外大家、大师对其光照的温暖和痕迹。所以,我曾经一再地说,没有中国古典文学,就没有中国现当代文学,可没有外国文学,也依然没有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是中国现、当代文学阅读的两翼,二者缺一不可。缺一就会使中国文学失去平衡,并且下落和****。
第二,我们谈谈能够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种子的外国文学。从对中国当代文学影响的大小、深浅来讲,可以把世界文学分为三大部分或地域三块来说:一是俄罗斯文学;二是欧美文学;三是拉美文学。
俄罗斯文学,包括我们说的苏联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关系可说源远流长,盘根错节。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因为俄罗斯文学的伟大,因为俄罗斯和中国的地缘关系,因为俄罗斯进入社会主义时期的苏联之后和中国的社会体制、意识形态的那种相通、相同的关系。因为这些复杂的地缘和社会、文化、政治因素,这些因素在俄罗斯文学和当代中国文学的关系中,是占有着种子与土壤那种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在俄罗斯的早期鼎盛文学中,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果戈理、契诃夫,以及后来的肖洛霍夫、高尔基、普宁、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和再晚之后的艾特玛托夫及《鱼王》的作者维阿斯塔菲耶夫等等,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在世界范围内,就是连法国这样伟大得令世人翘首的文化大国,也没有像俄罗斯这样众多的作家在中国深入人心,近乎家喻户晓地影响着中国当代的文学和作家。甚至到了上世纪中期,苏联的“二战文学”,也可以如坦克一般,隆隆地驶入中国文学的土地,辗轧着中国文学的土壤,播撒着他们已经失去的昔日的文学光辉。但这种失去,却因为社会和社会意识的作用,照旧光亮无比,灼人耳目,是能够烧毁中国作家纸笔的滚烫的文学火种。如这一时期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未列入名册》、《后来发生了战争》和《遭遇战》,康德拉季耶夫的《萨什卡》,拉普斯京的《活着就要记住》,拉甫涅夫的《第四十一个》,还有《热的雪》、《方尖碑》、《最后的炮轰》、《一寸土》、《岸》等等,这一时期的“二战文学”,如果累积起来,可以拼满一个书架。就这一时期的苏联文学而言,之所以能够如此影响中国文学,是因为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中国百废待兴,文学也急要建立、修整自己的高楼大厦。因为中国和越南的那场南线战争,使这批作品有机会单刀直入、生吞活剥地进入了中国文学空白的中心,成为种子肆无忌惮开花结果。比如当年在中国文坛影响最大的徐怀中先生的《西线轶事》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种子与果实的那种关系。比如当年领“改革文学”之先的《乔厂长上任记》和苏联小说《机电厂长的一天》,比如因为今天获得广泛影响的电视剧《亮剑》和《历史的天空》而广获读者的同名小说,其中他们在人物塑造方面的那种“英雄必然缺失”、“豪杰必然理短”的方法和苏联二战文学中广泛积累的人物塑造的经验——“英雄必然有人性之弱”、“豪杰必显人道之亏”的方法,几乎如出一辙,一奶同胞,或者说血肉相连,是父子之根,母女之花。只可惜,苏联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与这一时期有突出成就的二战文学,比起他们的古典文学,本就有了艺术和格局上的巨大滑落,就连曾经在社会主义的领空,无比辉煌耀眼的那批“战壕文学”成果之和,也无法同《战争与和平》和《静静的顿河》等单部作品同日而语、相提并论。然而,我们借鉴学习这样的作品已经数十年,直到今天,还以这样的作品为种子和榜样,却还没有达到和超越人家作品的水准和高度,这就非常值得我们深思和反省。
就俄罗斯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可以分为早期和近期两个阶段。早期之时,以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代表的作家和作品,是一种伟大的民族情怀文学,作家们怀有对他们民族和土地深厚的情感和忧虑,有着一种伟大的爱和爱憎交加的矛盾内心,因此,他们写出了一大批不朽之作。就近期作品而言,是以艾特玛托夫和瓦西里耶夫为代表的社会情感文学,他们关注社会,也关注人的心灵,但缺少对俄罗斯大地如肖洛霍夫那样的宽厚与仁爱,所以他们的作品只能从伟大的平台上,下降到优秀的行列,如巍峨的山脉,因为时间和地壳的运动,而成为了丘陵一样。但是,就借鉴与学习而言,借种子移植而培育新果新花而言,因为中国与苏联社会意识的相近性,相通性,和政策的要求与必然,而对中国当代文学参生深远影响的是后者,而非前者。
这是中国文学的遗憾。
是一个农人在选择种子时,因为自己,也因为他人不得不把饱满的种子丢到了一边,而选择了次之的种子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播撒。另一方面,也说明一个问题:即伟大的不可学习性。因为真正的伟大,其实是一种文学情怀,恰恰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的借鉴与学习,最不能借鉴的就是这种文学情怀。其他的一切写作经验,都是可以转移和转化的。唯伟大的情怀无法借鉴与学习,也难以转移和转化。
欧美文学,也可以分为古典和现代。而欧美的古典文学,从十八、十九世纪说起来,中国有些年龄的作家,都能说出一长串的名字:莎士比亚的戏剧,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司汤达的《红与黑》、《巴马修道院》,雨果的《九三年》、《悲惨世界》,左拉的《金钱》,莫泊桑、梅里美和都德的中、短篇小说,还有英国哈代的《还乡》,奥斯汀的《情感与理智》、《傲慢与偏见》以及美国十九世纪的马克·吐温、爱伦·坡、杰克·伦敦等等,他们的作品,都对中国的传统现实主义产生过直接的影响,甚至直到今天,我们许多作家的写作,仍然无法摆脱这些作家和作品的影子和方式。
当然,回到中国当代文学上来,就对今天活跃在文坛的一大批中年和年轻作家来说,对其影响更大的欧美文学和作家,是二十世纪的那些作家和作品。如在中国尽人皆知的美国的福克纳、海明威,凯鲁亚克的《在路上》,索尔·贝娄的《雨王汉德逊》、《洪堡的礼物》,艾伦·金斯堡的《嚎叫》和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南回归线》,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以及不知算为美国作家,还是把他归为俄罗斯作家更为合适的纳博科夫的《洛丽塔》。除了美国这一大批作家之外,还有英国作家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动物庄园》,伍尔夫的意识流小说,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以及法国的加缪和普鲁斯特,还有他们那些作品格局甚小、在中国影响甚大的新小说。说到欧洲的德国语小说,我们不能忽略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获得广泛影响的茨威格的三大卷、上百万字的中短篇和聚斯金德的《香水》及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除此之外,为欧洲文学和世界文学增添了灼目光辉的作家还有大名鼎鼎的奥地利的卡夫卡、意大利的卡尔维诺、捷克的昆德拉。他们作为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和推动,以及引起中国文学质的变化,在二十世纪末端的九十年代,完全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动机或者助推器。尤其是卡夫卡和拉美文学中的博尔赫斯和马尔克斯,没有他们,就没有中国当代文学今天这个样子,或者说没有他们,中国当代文学就是另外的格局或模样,也许不算过分,甚或说恰如其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