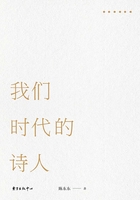中国古代与西方相比,一直没有宗教的救赎精神。所以董仲舒通过天人感应论来弥补这种不足之处,使汉武帝的教化之说建构在本体论的基础之上,为性命之说找到终极的依据。董仲舒一再强调天意好生不好杀、任德不任刑,也是为了使帝王的威权得到控制。他从儒家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精神出发,严厉批评了秦朝好刑滥杀的****,指出教化之根本在于爱民厚生,然后人民才能知礼义。以人为本的观念在他的思想中是十分明显的,也是孔孟人道主义思想在汉武帝时期的重张。
董仲舒与武帝对话中另一个重要的地方,在于探讨了道的延续性问题。法家思想强调创变,否认历史传统的连续性。所谓法后王与法先王,是先秦思想界中法家与儒家激烈争论的要点。(墨家推崇先王是基于对当时社会政治的不满。孟子继承孔子思想,崇尚三代,强调法先王。荀子批评子思、孟子一派“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他主张“法后王”。韩非子继承荀子法后王的观点,以历史进化论来批判法先王观点。韩非子法后王思想有合理因素,他承认历史的进步与改革的必要性。以庄子和孟子相比较:孟子认为六经乃先王所以成为先王的道理,庄子以为六经不过先王成为先王的事迹。《孟子·离娄下》:“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庄子·天运》:“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庄子·天道》:“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轮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汉武帝对此问题是心存疑虑的。同时他作为一代雄主,更看重的是当世利益与成功,其政策的急功近利是非常明显的。因此,他一再提出,如何变易古人之道,既效法前人同时又有所创新。董仲舒针对他的心理,提出治道在历史上从来是既有所创新,又有共通的地方。与武帝相比,董仲舒更强调的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著名论断,从而为儒学之道取得合法性地位而张目,为儒学之道在思想上“立法”。他在第三次奏对中提出:册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臣闻夫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道者万世之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眊而不行,举其偏者以补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故孔子曰:“亡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余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繇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董仲舒提出历代政治之道虽然有所损益,但是内在精神却是不变的。因为道的本体是天,而天是至正无偏、永远存在的,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句话强调了道的永恒性,是为了打消汉武帝的疑虑,同时也昭示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与政治之道的连续性,最终为道的本体性立法。能够理直气壮地将道说得那么透彻的,非董仲舒莫属。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家的通变观,与此是一脉相通的,观《文心雕龙》的《通变》即可见一斑。文道论是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的关键词,与董仲舒的这种思想是有着直接关系的。董仲舒最后提出:
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以大治,上下和睦,习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奸邪,民亡盗贼,囹圄空虚,德润草木,泽被四海,凤皇来集,麒麟来游,以古准今,壹何不相逮之远也!安所缪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与?有所诡于天之理与?试迹之于古,返之于天,党可得见乎。
董仲舒一方面承认汉代与上古相比,宜有所更易,但是另一方面更强调古代与现代的一致性,强调历史传统与现实的结合。这一点显然是儒者的主张,而与帝王的重视变易有所不同。这些主张显然有些是矫枉过正,显见得是为了纠正秦代对上古文化传统的毁灭而言的,但是客观上也促成了复古文化传统的形成。古今对话,从此以后成为一个永恒的主题。汉代儒生与崇尚法后王思想的人物,在当时发生过激烈的争执。比如《盐铁论》中文学与贤良的对话与交锋,很大程度上表现在是古非今与是今非古上面。这是对话中的热点与焦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复古与新变的对话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董仲舒为了树立儒学的地位,不惜用儒学与帝王权势相结盟的方式来鼓吹思想文化上的一统。这是颇为耐人寻味的。儒学本是一种自由的学术,孔孟之学当时均以私学的身份出现在春秋战国年代,在秦代还受到过迫害,思想对话被焚书坑儒所取代,造成了中国历史上读书人最大的悲剧,由此也酝酿了秦朝的灭亡。应当说,这对士人与统治者来说,都是没有胜者的悲剧。然而,一种学术一旦为了维护自己的意识形态的地位,为了使帝王采纳,拒绝对话而实行专断的话,就会走向反面。董仲舒在与汉武帝对话的最后提出: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董仲舒将自己改造过的春秋公羊学说,打扮成天人感应论,作为一种统一的儒学意识形态,并且建议汉武帝动用权力来推广,同时罢黜百家之说只允许儒学与帝王对话,而不许别家之存在。这种思想实际上又与李斯之类的建议相同了。(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第三章《董仲舒公羊春秋学的中世纪神学正宗思想》的第一节《中世纪神学的形成与董仲舒的神学》中说:董仲舒不仅是中世纪神学思想的创建者,而且是封建制思想统治的发动者;不仅是中世纪正宗思想的理论家,而且是封建政治的实行家。他的理论,通过了武帝的雄才大略的钦定,实质上确立为神学的正宗,因此他对古代“子学作出了否定,为中世纪“经学”开拓了地基。本传所说“学士皆师尊之”,本传赞所说“为群儒首”,五行志所说“为儒者宗”,皆以此故。)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之后,对于中国古代社会思想对话产生了许多排斥异己的作用,在文艺批评上产生了许多清规戒律。这是不争的事实。尽管董仲舒后来因推断灾异差点被杀,做官也并不如公孙弘这类儒学官僚会做,但是他的思想建议还是为朝廷所重视。《汉书·董仲舒传》上说:“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年老,以寿终于家,家徙茂陵,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可见董仲舒的主张因为深契于帝王的独断话语权力的心理,得到当时与后世统治者的重视,这并非偶然。他通过对话,使皇帝接受儒学的思想,对于汉代人才培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从而纠正了秦代与汉初对儒学的轻视做法。中国古代的文官选举采用儒学思想,应当是从董仲舒对话之后开始的。这一点上,董仲舒是功不可没的。但他的思想对话迎合帝王,与早期儒学之士有明显不同。《汉书·董仲舒传》班固赞中引用刘歆的话指出:“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然考其师友渊源所渐,犹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吕不加,过矣。”这应当说是比较公正的评价。
§§§第三节对话中所见士人与帝王的对弈
在两汉士人与****帝王的思想对话中,对弈的意味很深长。从思想对弈的角度去认识两汉士人与帝王之关系,进而把握这一时代的思想史特点,是很重要的。近人徐复观先生研究两汉思想史,着力于此而收获颇丰,即是明证。(参见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一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所谓思想对弈,犹如下棋一般,充满着角逐对抗的意味,同时又是在一盘棋的天地中进行的。两汉年代的士人与帝王之关系,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更是如此。在两汉封建****社会中,士与帝王的关系已经丧失了春秋战国时代君臣、师友、同道诸多关系的内涵,而变成了单一的君臣关系,甚至如同主仆。帝王对臣下操生杀予夺大权。汉武帝选举人才不拘一格,选用了许多士人。他曾对别人说:“方今公孙(弘)丞相、兒(宽)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马相如、吾丘寿王、主父偃、朱买臣、严助、汲黯、胶仓、终军、严安、徐乐、司马迁之伦,皆辩知闳达,溢于文辞。”言外之意,武帝颇为自己善于擢拔人才而得意。班固《汉书·武帝纪》赞曰:“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这段话指出了武帝在传承上古文化、制礼作乐方面的贡献。班固又从史家的角度对于武帝在人才选拔方面作出了客观的评价:赞曰:
公孙弘、卜式、兒宽皆以鸿渐之翼困于燕爵,远迹羊豕之间,非遇其时,焉能致此位乎?是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已。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
这里全面地胪列了武帝在文武方面对于人才的擢用是史无前例的,其气魄之大,令人感佩。
当然,具有自我精神追求的士与社会的和谐,尤其是与高高在上的****帝王的和谐相处总是相对的。从本质上来说,在孔孟、老庄人生理想熏陶下形成的士,与社会总是落落不合的。这也是社会道德价值的均衡所必需的格局与态势。西汉建立了经学取士的选举制度,使得士能够凭借经术和其他才能进入各级政权组织中去。但两汉时代的士,多为经学利禄所束缚。经学入仕制度实际上是“在下者视为利禄之途,在上者视为挟持之具”(刘师培:《国粹学报·乙巳年丛谈》。)。后来唐太宗那句著名的“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也是看到了科举制度与汉代的察举征辟制度一样,对于网罗知识分子竟有如此简捷而奇妙的功用。在两汉大一统的封建****帝国中,士失去了战国时代纵横捭阖、自由选择的机会,成为严密的帝国机器内部的一个零件。君王既然可以凭自己的意志和决断擢拔士人,也可以因个人喜怒无常和一时的过错而杀戮大臣。主父偃、终军、严助、朱买臣等人的命运无不如此。司马迁也因为几句话而受腐刑。所以当时的直臣汲黯曾面谏汉武帝不要滥杀大臣,要爱惜人才:“陛下爱才乐士,求之无倦,比得一个,劳心苦神未尽其用,辄已杀之,以有限之士,资无已之诛,陛下欲谁与为治乎?”(《艺文类聚》卷二十四引。)所以,两汉士人同样面临着理想与现实相冲突、苦心孤诣不被理解的心态。汉武帝有时还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眼光去要求臣下应对。这样无形中束缚了士人的精神世界。至于东汉光武帝对于臣下的思想钳束就更明显了。大臣桓谭因为在朝堂上批评谶纬,被他说成“非圣无法”,差点被杀掉,令后人至今读此而感到心寒。这也成为光武帝刘秀身上永远无法抹去的历史污渍。
汉文帝时贾谊的遭际就说明了这一点。年少的贾谊在汉文帝时积极为朝廷出谋划策,为汉初统治的长治久安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但是却引起了许多朝廷老臣的嫉恨,遭到了如同屈原一样的命运:“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雒阳之人,年少初,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那些倚老卖老的如周勃、灌婴等汉初元老,不满贾谊的奋发锐进。他们保守成性,嫉妒贾谊的年少天才,于是在汉文帝面前诽谤贾谊。汉文帝对这帮老臣的话也不得不听信,作出一些让步,于是慢慢疏远了贾谊。贾谊遭受了打击后,深深感到宦海凶险,人心叵测。即令是汉文帝这样比较开明的天子,也难免听信谗言。周勃、灌婴、冯敬这些朝廷老臣,固然为西汉王朝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可是一旦官位显赫,就很自然地居功自傲,堵塞言路,压抑后进。可见,封建官僚体制从本质上说,是与贾谊这样的天才相抵牾的。在渡湘水赴长沙就任时,贾谊凭吊屈原,借景生情,写成著名的《吊屈原赋》,抒发了自己的孤独心态与忧愤之情。他在赋中痛陈世道不公,方正倒植,英才遭贬,奸佞张翅。贾谊后来又遭“为傅无状”,即梁怀王堕马而死之事,在郁郁寡欢、孤独悔罪的心境下早亡。
贾谊的遭遇并非偶然。尽管西汉帝王招纳贤才,但贤才的理想曲高和寡,难以和帝王的实用功利相契合。所以许多士可以受用于一时,最终还是陷于孤独失望的心境中。像董仲舒这样的一代儒宗,虽然也曾受到汉武帝的青睐,但是这位虔诚的大儒所向往的三代之治与“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汉武帝格格不入,因而不免失望、气馁。他在著名的《士不遇赋》中就展现了内心的苦闷:
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末俗以辩诈而期通兮,负士以耿介而自束,虽日三省于吾身兮,由怀进退之惟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