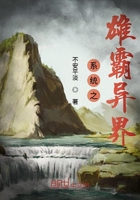睁开眼睛,映入眼帘的是夫人一袭素白的裙,她背对着自己弹奏,没有一丝波澜,也听不出琴声里有着怎样的起伏,就像一株昙花,遗世的开着。夫人很少出门,就连若雾也很少能见到她,不知她今天为何会在此。若雾起身却发现腿上没有一丝力气,只得用手双手撑起身体,勉强坐了起来,箜篌声住,夫人依旧未转身,只低低的问了一句:“你醒了?”,若雾本想起身行礼,无奈身体不听使唤,摔了下去。她到此刻才发觉,自己的腿真的是毫无知觉了,心里莫名其妙的慌张起来,难道自己瘸了吗?就这么思量间,夫人便已走到自己的身边,冷冷的问道:“你没事吧?”
“回夫人…。若雾没事,多谢夫人一直照顾。”看她惶恐的模样,好像很怕自己,她却不知道,若雾表情里的慌张有一半是对自己的腿。篱落看着眼前的小女孩,怯懦的不堪,她不仅从心底发出一声冷笑:“你不用谢我,一直都是夜氏在照顾你的,今日是夜铭出殡,他身为长子,自去处理了。”
夜铭出殡,这冷冰冰的话语竟是从自己的亲生母亲嘴里说出,没有一丝的伤心和难过,然若雾也不禁怀疑自己是否听错了,想要再确认一下:“夜铭?出殡,夫人在说笑吗?”篱落忽然笑了起来,大笑着,依然美丽的脸,依然的毫无表情,只是不知怎么的眼睛里也笑出了泪花,“开玩笑吗?我自己的儿子,也只不过是凡夫俗子罢了,难免一死,早死晚死又有何区别,这次也只不过是解脱了罢了。”她笑着,伸出手抹去眼角的泪水。“又下雪了,没想到,这里的雪,竟也与韩地的芒花相似。”她说,小声的,温柔的,苦涩的。像多年前一样,她原也是汉人,很普通的一个孤女,家在韩地。若不是那场战争,她依旧是普通人,有着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若不是她执意救了一个人,她也愿堕入一番轮回,选择重新做人,而如今不知是哪一世的萋萋芳草,竟还牵绊着自己舍不得这一世的无望等待。
她开了门,站在光影里,有雪花飘来,空气中的清冷弥漫开来,她也不关门,温柔的扶起依旧躺在地上的孩子:“你的腿,大夫瞧过了,并没什么大碍,许是在雪里冻久了,才会毫无气力。只是可怜了我那孩子,他想让你早些好起来,非要去找什么草药,他偷偷地去,等发现时,已在湖边冻僵了。”她依旧不动声色,好像说着,那眼光竟然比不上看雪花时的半分温柔,若雾的心里翻滚起的热浪好像能把自己融化掉,却溶不干眼泪,她声嘶力竭,她嚎啕大哭,想要冲出门去,又害怕面对,她趴在地上,又如那日漫天的雪,冷的让她开始胡言乱语。说来,她对篱落本没什么指责,只是心寒她的态度,夜铭是她的儿子,城主的嫡子,抛却这珍贵的身份不顾,单单是身为普通人,亲生儿子过世,本不是应当生不如死,祈求上苍宁愿拿自己一命换儿子几载光阴的吗?是她的冷淡,不,冷漠,激怒了若雾,她不理解,她要看到她伤心欲绝,像自己一样,若雾疯了样的撕扯着她素白的裙,恨不得用力气温暖她那颗冰冷坚硬的心。
她累了,倚在篱落的怀里,啜泣着,她很伤心吧,篱落想,不仅仅是失去了儿时的玩伴,几乎一夜之间,她失去了所有,她最爱的姐姐,她并不温暖的家,对夜铭,她自责愧疚,对姐姐,她愤恨想念。她本拥有的不多,却都视如珍宝,她或许不明白生离死别,却天生就懂得自怜自护,此刻她除了对夜铭的愧疚与惊恐外,必然觉得自己就是世上最可怜可悲的人,绝不会想姐姐会有什么苦衷,更加不会明白篱落的心。她毕竟只是个孩子,需要保护,需要自己一件一件的去明白这个世界,现在她累了,蜷缩在篱落的怀里,像含苞的黄玫瑰,紧紧的包裹着一颗心,不肯轻易开放,眼前的女子忽然对她怜惜起来,抱抱她,明知她不会懂,依旧说着:“生死的事,不是悲喜就能勘透的,就算伤心难过,甚至于赔了性命,他还是回不来了,一个人,安安静静的来,安安静静的走,夜铭他死的安心,我想如果要他再选一次,他依然会去的,他遵从自己的心,不会遗憾什么,倒是你,是真的难过他死了,还是难过因为自己他死了,亦或者两者都有?恐怕后者远远大于前者吧,生而为人,往往下意识想到的,也只有自己的苦痛罢了。”像是对她说着,也像是对曾经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