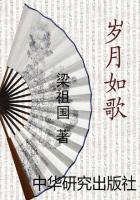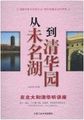警察走过来:“你很难过,可这样不但不利于你自己,对别人也有危险,回家去吧。”
“你是不是来帮助我的?”
人们都摇着头叹息着走开了。
他挖了八个小时……十二个小时……他满脸灰尘,双眼布满血丝,衣服上沾满了血迹。在第三十八小时,他忽然听见底下传出一个孩子的声音:“爸爸,是你吗?”
是儿子的声音!父亲大喊:“是我,我的儿子!”
“爸爸,真的是你吗?”
“是我,是爸爸。儿子!”
“我告诉同学们不要害怕,说只要我爸爸活着就一定会来救我,也能救出大家。你说过无论发生什么,你总会跟我在一起!”
父亲大声向四周呼喊:“这里有孩子,都活着!快来人!”
路过的人闻声赶来帮忙。
几个小时后,一个安全的小出口开辟出来了。
父亲用颤抖的声音说:“出来吧,儿子!”
“不!爸爸,先让别的同学出去吧。你会跟我在一起的,我不怕。”
终于,这一对了不起的父子在经历了巨大的灾难后,无比幸福地紧紧地拥抱了在一起。
父爱,不须用什么华丽的语言来形容,因为父爱就如同父亲那有力的大手,宽厚的肩膀。虽然话语不多却坚实有力,无论你遇到什么困难,他都会毫不犹豫地挡在你面前,保护着你。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来诠释父爱的内涵,那么这句“不论发生什么事,我总会跟你在一起”就够了。
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都十分清楚,生活里这种危难之中展露不平凡的父子之情的机会少之又少,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常常是感动于故事的可歌可泣而感慨于自己经历的平淡无奇。
我们自己的生活真的就那么平淡,那么无奇吗?
当我的目光不经意地掠过书架上一排排的教科书、参考书、美文经典、益智读物时,仿佛从书后那不菲的价目上也感受到了父爱的深沉和期盼的殷切。
是的,仔细想来,还不仅如此,初学外语时的录音机,一部又一部的“步步高学习机”,为播放外语盘片购置的VCD影碟机,几天前,最不追赶时尚的父亲又为我买了一部最新出品的“全能手写王”。
还有,每当寒暑假结束,开学伊始,家里的那台电视就准时准点地进入了休眠,原因只有一个,不能让那缤纷的节目成为挡不住的诱惑而扰乱我学习中专注的心境。
还有……
噢,原来爱是需要感悟和体味的。
也许,当时光的流水用它几十年的冲刷将今天鲜明的记忆变得朦胧与模糊,也许,当岁月用他温柔的双手在不知不觉间染白了我如丝的黑发,让我对生活和感情的理解不再这么浅表和简单,但这个故事给我的影响却将像融入到大海中的一滴水一样,既不见踪影又无所不在,对父母恩德的感念、对亲人全身心的依赖,不需要自我提醒自我告诫而变得像呼吸一样自然。
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来诠释父爱的内涵,那么,我想这山一般厚重的父爱是无法用语言来诠释的。
如山父爱载不动
宇原
多年的梦里,这炮声犹在耳际,诉说着我与父亲一起走过的岁月。父亲是在用一种仪式为我壮行,那一声声冲天的梦想,时时唤醒我:人活着,不能、不仅仅只为了自己!
冬夜,山高月小。我摸进采石场,跟父亲直白,爸,我不想读书了,这事,我想了好久了。
父亲听后只问了一声,肯定了吗?是担心没钱供你上大学吧?爸这条命还健!
我捡起地上的行李,执意转身。
“呼”!父亲狠狠地将羊角镐砸在一堆石上,火星四溅,他瘦小的身子渐渐地矮了下去。
走了好久,山谷里仍可听到父亲如狼一般的嚎叫。我的家乡,贫瘠而苍凉,山连山,石挨石。我亲眼看见父亲的采石作业。随着火药吼过,石雨落尽,父亲戴着安全帽,从一叶岩石下钻出来,硝烟远未散尽,父亲就冲进了“战场”,抢着搬运石块。一天下来,父亲仿佛是从石灰坑里跳出来的,浑身白霜。多年积劳成疾,使父亲患上了严重的哮喘、风湿、静脉曲张等疾病,为了给我们挣学费生活费,每次回到家中,我最不愿面对的是那双手。那双手,在与石头的对撞中,早已伤痕累累。一到冬天,就绽开一道道血网。
父亲每一次将血汗钱交给我手中时,我的心就会隐痛好几天。
高三上学期,我决定放弃上大学的机会。尽管,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在全校名列前茅,学校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可考出去,父亲怎么办?弟妹们怎么办?最后,这如山的沉重,使我选择了放弃。
一个人到外地打工。离家乡几千公里,梦里,尽是父亲佝偻的背影。想到此,我拼命地挣钱,只要能挣钱的活我都干,往往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但每一次睡下,我都有一种虚脱的踏实。我想,父亲迟早有一天会理解我的。
哪知,就在我赚钱正欢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彻底粉碎了我的梦想。由于过度劳累,再加上营养严重不良,一个雨夜,我天昏地暗地加班到凌晨,最后起身时,眼前一黑,“咚”地栽倒在水泥地上。同事送我去医院,一检查,我得了急性肝炎,并伴有腹水。那些恐怖的夜晚,我睁着失神的眼睛,望着病房惨白的墙。辛苦赚来的钱,像流水一样漂去。我才知道,“贫穷”这两个字眼,在穷人的眼里是多么的可怕!
多想,在死之前与父亲见上最后一面,看一看他苍老的脸庞,然后,怀着一种麻木的刺痛,在父亲怀瑞安静地死去。可是,我不能。我不想告诉父亲,我不能让他承受这一打击。医院渐渐减少了用药,我只想挨一天是一天。
一天清晨醒来,我看到了父亲。几月不见,他显得更加瘦小。胡楂,像山上的松针恣意地伸进我的眼睛。原来,父亲接到了公司打给他的病危电话,带了几个叔父,扒了一辆货车,几天几夜没合眼马不停蹄地赶来的。
几天过去,父亲带来的钱将尽,我的病情仍得不到好转。父亲的哮喘病却复发了,为了怕吵醒我,实在忍不住咳嗽时,就捂着嘴,跑到医院的黑暗的角落咳嗽。尽管声音掩饰得很小,却更能揪起我一种撕心裂肺的疼。
父亲与叔父们商议,租一辆出租车,将我接回去继续治疗。当父亲背着我出院时,我能清晰地感觉到父亲明显突出的肩胛骨,如两只铁蝶,坚硬如刀。可是,这么多人共乘一辆车,显然坐不了。而父亲显然不想再花钱租车。
他围着车转了好几圈,最后指着车尾厢对司机说,师傅,我就躺这儿吧。
司机呆了,在他眼里,尾厢只能装一些物品,人可从来没有载过。见司机犹豫,父亲猫着腰,就进去了。他将自己蜷缩在里面,如一只干虾。
司机见此情况,也就不再说什么,只让父亲注意安全,实在憋不住就喊一声。
几个叔父都争着要去,父亲对他们说,我矮小,就我吧,你们照顾好孩子就行了。叔父们实在不忍再见,难过地别过脸去。
临行前,父亲趴着出来,走到我跟前,伸出他粗糙的手,握住我,说,活着回去,孩子!以后的路,你要走好啊!
我知道这句话的分量,我坚定地回答他,爸,咱们要一起回家,好好的!爸,我这就回去复读,你要看着我考大学,你要答应我!保重,爸!
父亲棱角分明的脸上,掠过一丝苍凉的微笑。
德州的冬天很干冷。即便是坐在车厢里,也感觉到外面的冰寒。
为了保证父亲的呼吸,司机将车尾向上掀开一条缝。叔父一路告诉我,孩子,回去好好读书吧,你不在的这些日子,你父亲总是一个人在山上抹泪,他不稀罕你的钱,只在乎你为他争光。
车,静默地,剪开如水的月色。北风,蹭着车窗尖厉而过。司机显然拼尽了全力,他也是在为父亲争取时间。
整整两天三夜,冷风像一只只无形的怪兽,无孔不钻。连坐在车里面,几个人相依取暖,都觉得寒冷。我不知道病痛的父亲,会不会挺得住?我与他只隔一层钢板,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不能翻身、不能动弹、不能叫痛,强忍着孤寂、病痛与颠簸。他是在用他的生命抢救我的生命,用他的时间换取我的时间啊!
我才知道,这世上有一类父亲,子女永远是他们的希望、信仰、寄托、主宰、力量之源、奋斗之根、生命的全部意义。
黎明时分,天色如墨。在一个出站口,警灯闪烁一片。一辆辆车被次第拦下,检查、问证、放行。轮到我们时,警察看车上每一个人的证件。最后,让司机打开尾厢。在警察惊讶的注视下,司机颤抖地打开车盖,父亲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仿佛睡着了一般。一个警察用戴着白色手套的手,摸了摸父亲。父亲呻吟了一声,警察吓得跳了起来,旋即大怒,怎么能这样载人呢?这不是草菅人命吗?
我这才得知,路上不断有司机与乘客,透过那条“生死缝”,看见了一动不动的父亲,记下了车牌号,并报了警:有人偷运尸体!
警察要罚款。这时父亲清醒了过来,想出来却又不能,在叔父们帮助下,将他一点一点拖出,患了风湿与静脉曲张的他,双脚不能沾地,只有靠两个叔父的手勉强搀起。陡然,父亲自胸间传来一声猛咳,穿透喉间,脸色青紫,唇色焦白,如雷袭来,刺入耳膜,听之让人心颤。
显然,父亲不能动弹的原因,是昏过去了,失去了知觉!
父亲凝望着我,嘴唇直哆嗦,第一句话就是:“求求你们放行吧!只要救活我儿子,我死不死无关紧要,这事与司机没有干系,我给你们跪下啦!求求你们这些好人了!”
一阵刺痛袭击了我,我大叫一声:爸!人僵在原地,灵魂早已走远。
天色渐明,许多人背过脸去抹泪,女人们感动得哭泣起来。一个人都没有动。
闪道!出发!
一名警官高亢地命令。
他亲自出动了一辆警车,载上我的父亲,“嗖”的一声,风驰电掣地将一切抛远。透过反光镜,我看着那些晨风里的警察们,伫立在那里举起了手臂,为父亲行注目礼。司机红了眼,狠踩油门,车子发出阵阵嘶吼。泪水,早已在他脸上垦出两道河。
我与父亲,没有违背从德州出发前的约定,都活了下来。几个月后,父亲扛着他的那一套家什走进了大山深处,如一枚坚果落进了疏秋。第二年,我考上了一所名牌大学。走时,山中开山炮仗一声一声直插云霄。群山,淹没在我的泪水里。从这一天起,我开始了一种真正的生活。
多年的梦里,这炮声犹在耳际,诉说着我与父亲一起走过的岁月。父亲是在用一种仪式为我壮行,那一声声冲天的梦想,时时唤醒我:人活着,不能、不仅仅只为了自己!
爱的符号
佚名
无须语言,甚至无须何种方式,父爱,只默默生成,慢慢积淀,静静流淌……
父爱中蕴藏着的,是太阳的光泽,是莽莽苍苍山林的气息。无须语言,甚至无须何种方式,父爱,只默默生成,慢慢积淀,静静流淌……
入狱改造几年了,对家人的思念与日俱增。同监犯人之间常传阅家信,算是分享亲情吧。我也因此看过很多别人的家信,常使我感慨心酸。
最让我感动的,还是一名皖北籍犯人的家信。他家人称他为狗伢。
狗伢家住几千里外的一个偏远山村,父母都是聋哑人。因为穷,村里几乎没有人读过书,能把一封信念出大概的也没几个。而要动笔写信,只有求离家几里外的那所学校的惟一一名老师。他父母一个大字不识,想求人写吧,儿子坐牢实在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所以给他写信,便是家中一件大难事了。
狗伢刚入监时,看到别人捧读家书时那种陶醉的神情,羡慕得不得了。可他知道家里的情况,只好深夜蜷在床板上暗自垂泪。
就在那年冬天,狗伢那思子心切的聋哑父亲,卖掉家中仅有的一头年猪,从几千里外风尘仆仆赶来广东探望他。当时别人喊他有人探望,他死也不信,直到值班干部亲自来喊,狗伢才相信这是真的。
一个心焦难语的山里老人,一个思亲欲疯的囚子,我实在想不出这样一对久不见面的父子,会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心情。
狗伢接受探望回来时,带回一包焦黄喷香的小咸鱼干,这是他聋哑的父亲千里迢迢送来的惟一一点东西。好长一段时间,狗伢都舍不得吃。听他讲,这种比小拇指还小的鱼是他家乡的特产,每年只有秋天才会出现,而想要逮住它,只有垂钓。不知道他父亲钓了多久,才能攒上这么一大包。
一天晚上收工后,狗伢照例拿出那包放了好久的鱼干,坐那儿发呆。有个广东犯人嘲笑他说:“这不是我家喂热带鱼的鱼食吗?难道你爸是卖鱼食的,卖不完才拿给你!”气得狗伢要跟他拼命,大家劝说了好半天,直到广东犯人道歉,才平息了狗伢的怒气。
事隔不久,狗伢拿了封信神秘地找我说:“喂,给你看我的信。”
展信一看,我呆住了!一张千皱百褶沾满汗渍的三十二开田字格的背面,竟没有一个字,只画满了千奇百怪的图案。看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狗伢说这是他爸上次探望时与他约定好的交谈方式。
原来,探望那天,哑父比划着家里太穷,以后不能常来看他,想他时就会给他写信。狗伢吃惊父亲什么时候会写字了。哑父忙“解释”:画个“小狗”就是喊他狗伢;画个“o”就是家中一切安好;画个“△”就是家中有事……狗伢不忍扫父亲认真欢喜的兴致,忙从政府发的零用钱账户上买了五十个信封邮票,写上自己的名字和监狱的地址。这样,只要他父亲在纸上画上一些相关的图案,往里一装就行了。
看着那满页似像非像的图案,我实在不忍想象一个白日在田里劳累了一天的老人,晚上佝偻着身子,借着昏黄的灯光,用那双握惯了锄杆的龟裂的大手,笨拙地捏着笔,吃力地一笔一笔划着……那是一幅怎样的景象啊!
我禁不住流泪了,这是我第一次为不相干的人流泪。
从那以后,每隔一个月,狗伢总能收到一封哑父寄来的别人无法看懂的家书。后来,信中又多了些新内容:比如春天,信里还会夹了一朵桃花或一片油菜叶——狗伢就知道家里的桃花开了,油菜也长高了;秋天,信封里会装进几粒饱满黄灿的稻谷——他就知道家里的收成很好;在寒冬到来时,父亲常常会画上一件肥大的棉袄——那是父亲在叮嘱他:天冷了,别忘了加衣。
年复一年,一封又一封家书源源寄来,没有一封是画“△”的。
可是这期间,狗伢的母亲去世了、父亲抱病在床、房子被洪水冲倒……是父亲用一双有力的大手,把一个个“△”抻成一个个“o”,用宽宏深沉的爱,为狗伢撑起一片亲情的晴空。
良知一点点被唤醒,灵魂一点点被净化,那年五月,狗伢立功减刑提前出狱了。
临别前夕,狗伢对我说:“志坚,把我爸这几年写的信留给你作个纪念吧!别忘了,不论在哪里,都有一个牵挂我们的家。你也要早点回家呀。”
捧着这被狗伢视为命根子的沉甸甸的父爱,我久久无语。是啊,我也该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