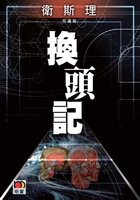“瓦尔特”这个外国名字,连同他那花格上装,一头绵羊似的卷卷毛和美丽的髯毛胡子,便渐渐地从人们的视线中销声匿迹。
二十多年过去了。
“瓦尔特”刑满释放,回到了曾经让他名噪一时的义渡城。
当年头绵羊卷卷毛和那满脸黑得发亮,甚至让人嫉妒的髯毛胡子已经看不见了,留下的只有光头上苍白的发粧和毫无生机的两髯。
他不甘心这样无声无息地生活在义渡,他要恢复人们的“记忆”,唤回那逝去的青春年华。
他在家里静养了半年,头发和胡子长得还真快。不过,这次长出的长发、长须却夹杂着许多的白色。好在这不是问题,染发在现代已经不是什么高科技,只要找个理发店就能解决,更何况现在不是单纯的理发时代了,而进入头部造型、美发、美髯的时代。
“瓦尔特”蓬头垢面、长须乱髯地在街上四处张望,为的是寻找一个比较满意的发廊。如今这个城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个店面和店主都让他十分陌生。他边走边想,到底上哪儿去做头才合适?正当他无所选择时,抬头看见,前面出现一个别致的店名——“第一美”造型发屋。这个店名正对他的胃口,听起来就不一般,既然夸下海口是“第一美”,想必会有两下子。
常言道:“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没那个本事绝不敢夸下海口。这可不像游摊,打一枪换个地方,它是常年店,跑得了初一,跑不了十五。
“瓦尔特”径直走近店门,隔着玻璃幕墙东看看西瞅瞅,发现这个造型屋还很正规,里面的发型师一个个都青春焕发,活力四射,各人头上顶着不同的颜色、不同的造型。
店门口两位年轻时尚的小妹主动迎上来:“先生,做发型还是洗头?我们‘第一美’的技术是一流的哟。”
“吔?”看来我老“瓦”魅力不减,都这么大岁数了,一出门,居然有这么漂亮的妹妹主动迎上前来打招呼。
其实,那哪是人家主动,而是时下商人们招揽生意的一种技巧,两位小妹儿是“迎宾”。
“弄头发。”“瓦尔特”边说边朝店内走。
其中一位小妹立即推开店门,跟着他,热情而礼貌地询问有无随身物品需要存放,同时周到地替他脱去外衣,放人存物柜,并将柜钥匙链轻轻套在“瓦尔特”的手腕上,还为他穿上了类似浴袍但质地轻薄的理发服,系上腰带。
“瓦尔特”感觉到这二十多年来,整个世道都变化了,变得他分不清东南西北。
人们的素质普遍提高了,人与人之间和谐了,人们的火气小了,连说话的分贝也小了,用个新词儿,叫什么?对,想起来了,叫“以人为本”。
接下来,位小妹询问他是水洗还是干洗?
“瓦尔特”问:“什么是水洗?什么是干洗?”
“干洗是先洗头后剪发,水洗就是先理发后洗头,”小妹说。
“我还从来没体验过干洗的滋味”,于是他果断地选择了干洗。
顶着满头泡沫的“瓦尔特”,一边享受小妹娴熟的抓洗手法,一边观察店内的状况,想为自己物色一位最好的造型师。
店里的造型师们都穿着统一的特色服装,上面是修身的纯白衬衫,下面则裹着一条说不清是裤子还是裙子的刺绣黑布,布的边角随着他们的步伐摆来摆去,别有一番风情。这种另类又抢眼的衣着,让他“瓦尔特”都感到新奇。再看看其他客人,有的在翻看时尚杂志,有的在观看座位前液晶电视里播放的情景喜剧,或者干脆闭目养神、懒得动弹,让思想去“争斗”。
“瓦尔特”也随手拿起坐椅旁边的一本时尚杂志,他要既享受头皮的按摩,还要享受精神的抚慰。
他随意翻到一页,是写一位女作家的海上旅行生活。文章写到,女作家创作之余,乘海船赶海散心。海船载着她来到一望无根、辽阔的大海。她非常兴奋,出于职业习惯,记起了海上日记:
第一天,遇上船长,船长很亲切,非常热情,要与我交朋友,我答。
第二天,船长出于礼节请我吃饭,上了许多过去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尝所未尝的海鲜,很好吃,我吃了不少。席间,船长讲了很多幽默的笑话和黄段子,让我非常开心。
第三天,船长又请我吃饭,饭后,他提出要与我那个。我很愤怒,坚决不与他那个。他也很=尬,这顿饭吃得不欢而散。
第四天,一大早,船长就来向我赔礼道歉,说对不起,今后不会再有非分之想,提出一定要与我共进晚餐。结果,晚餐后,他又提出要与我那个,还威胁我,如果不与他那个,他就把船整翻。妈呀!船上有七百多人啦。为了救人,迫于无奈,我只好与他那个了。
第五天,船长找我还要救人,我不敢推辞,又与他那个了。
第六天,我主动找到船长,希望继续救人。船长不干了,他说,希望我救命……
嘻嘻,我终于把他制服了!
“瓦尔特”看到这里,觉得现在的出版物办得太好了,很有可读性,不禁哈哈大笑,笑得摇头晃脑。那小妹用指腹在他头上使劲按了一下,“先生,看把你乐得,泡沬都掉到身上了!”“瓦尔特”回过神来,他觉得自己有些失态,便不太情愿地把时尚杂志扔在一边,静静地配合小妹“干洗”。
这时,一位年纪稍长的造型师走到面前,猫腰恭敬地说:“先生,今天打算做个什么样的头型啊……您应该是头一次到我们店吧!需要为您介绍几款发型吗?”
洗发的小妹反应快,赶紧给“瓦尔特”介绍:“这是我们老板、张师傅,‘第一美’的首席发型设计师。”
“瓦尔特”一听“首席”二字,高兴起来:“好,就是你,快给我做个发型!”
“不急,先生,您头还没洗完呢,”张老板不紧不慢道,“我们小妹儿的手法还过得去吧,待会儿,让她再给您捏几下,舒缓舒缓神经。我那边还有一位客人,就快好了”。说完吩咐其他店员千万不可怠慢“瓦尔特”。
继续按摩的时候,“瓦尔特”不时从镜子里搜索老板张洪利的身影,发现他正在给一位很有个性的年轻人做头,便琢磨着,“嗯,活儿做得不错,能给这样的新潮青年做头,一定能给我做好!”他更加坚信自己的选择,幻想着重拾风采的模样,嘴角不由得扬起一丝得意的笑。
张老板为那位顾客做完发型,这边正好洗完头。“瓦尔特”毫不犹豫地往张老板的理发椅上一坐,然后告诉张老板他的发型髯胡应该怎么怎么处理。他知道,这荒草滩似的头发和胡须,没个形状,别人是无所适从的。
他在家整整待了半年未出门,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光头和髯胡长出些基础来。真要恢复那一头绵羊似的卷卷发,还得等到头发足够长了才能伺弄。
他简短而干脆地告诉张洪利:“留长发,留髯胡。”
张洪利听着,一声不吭地打开电剪,开始工作。
呜呜呜……
这时,工作服左边的兜不停地跳动,尽管电剪在呜呜呜地响,张洪利还是能够清楚地感觉到是有人在打兜里的手机。他的手机是调到“振动”键,发出的声音轻微,但跳动却不影响他的直觉。张洪利停下手里的活,说了声“对不起”,挂了电剪,掏出手机,走向大门,边走边接电话。
电话是王孝祖打来的。
张洪利知道,王孝祖轻易不给他打电话,打电话就不可能是一般的事情,他小心谨慎地应付着,不敢大包大揽。
当王孝祖说妹妹王孝玲不愿继续读书,想找“张哥”给个面子,让她到“第一美”造型发屋当徒弟时,张洪利,喜出望外,如释重负,心底的石头落下了,踏实了,满心高兴,不觉得提高嗓子:“那好哇!那好哇!孝玲的事情包在我身上。”他激动的声音让许多造型师和顾客都情不自禁地往这边看。
上次回凉风村,成熟丰满的王孝玲给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回城的路上,他还有些想人非非,碍于同乡好友的分上,未敢造次。“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只好打消了歪念头。
现在王孝祖居然主动把如花似玉的妹妹送上门来,这意外的收获,求之不得,能让张洪利这样的人不高兴吗?
他与王孝祖约好时间,怕他们迷路,还交代了郊区公交车到城进站后,乘市内公交的路线和公交下车后步行的方位。然后美滋滋地收了手机,走进工作台,取下电推剪,重新为“瓦尔特”侍弄头发。直到这时,他还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回想着那次见到王孝玲的情景。
张洪利接了半天电话,把“瓦尔特”晾在一边。“瓦尔特”也耐不住寂寞,在发屋其他师傅呜呜的电剪声中没精打采地闭上了眼睛,昏昏欲睡。
问题出现了。
张洪利有些志得意满,只顾心里高兴,早把眼前这位顾客“留长发,留髯胡”的嘱咐抛到九霄云外。
这一分神,“呜——”
手起毛落,左边的髯毛掉在地上。
在张洪利的印象中,这么短的头发留这么长的髯胡是很难看的。他根本不知道,在这座城市里曾经有一个叫“瓦尔特”的风云人物,甚至怀疑眼前这位顾客是否真的嘱咐过“留长发,留髯胡”。
潜意识唤醒了“瓦尔特”,他微微睁开眼睛,瞄了瞄镜子,忽然睁大眼睛:“我的髯胡呢?”
他直直地盯着镜子里自己的脸,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问张。
“呜——”右边的髯胡又被撮了一推子,一堆毛发落在地上。
“呜,呜,呜——”连续决速的几推子,动作就像风卷残云,干净利索,让人没有思索,没有争执,右边的髯毛就全部躺在地上爬不起了。
张洪利并不是没有听到“瓦尔特”的质疑,他之所以这样,恰恰是因为质疑提醒了他,才使他决定迅速收拾残局。
试想,如果剃去了一个人的半边髯胡,留半边,这样不阴不阳,合适吗?人们是忌讳“阴阳头”的,那是“文化大革命”中给“牛鬼蛇神”留下的特殊标志,更没听说过“阴阳脸”。因此,不管事后怎样扯皮,剩下的半边髯胡还得被推掉。
“瓦尔特”火了,“我的髯胡怎么办?”脸红脖子粗地从座位上弹了。
“对不起,对不起!”张洪利连连道歉,他已经彻底从幻想的幸福中了。
“混账,对不起,一个对不起就打发了?”
“兄弟,交个朋友,这个造型作为友情馈赠,免收造型费。”张洪利一边下矮粧道歉,一边赔着笑脸,非常无奈。只要看看这斗鸡公一样的“瓦尔特”就心知肚明,理这个头还敢收费吗?
“免收理发费,你以为老子是来讨饭的?”“瓦尔特”越看越气,越气越激动,“你要是我,我来给你理发,我把你的头割下来,我免收你的理发费?你干不干?”
“这和割头不一样,割头就没命了,髯胡剃了,可以长出来。”张洪利低三下四地解释。
“什么不一样,我看就一样,你以为我这髯胡就是韭菜啊?”“瓦尔特”的肝火升到了极点,简直就要爆炸了,“我明明告诉过你,要留长发,留髯胡,你耳朵聋了吗?你分明就是存心所为,还要狡辩!我今天跟你没完。”
他像放连珠炮,旁若无人地训斥。
整个店堂的人都傻眼了,有个顾客想息事宁人,主动站出来做调解工作,劝张洪利不要再解释,说得越多,顾客火气越大。他回头又劝“瓦尔特”消消气。也有人小心翼翼地问“瓦尔特”:“这事你觉得要怎样处理才满意?”让他把握主动权。
“怎么处理?还原呗!不还原,老子跟他没完!”“瓦尔特”负气说。
调解人没了言语,推去的髯胡不是不能还原,如今的科学技术那么先进,只是要采用植人术,将整个髯胡重新种植一遍就还原了。
问题是有这个必要吗?完全没有这个必要。植毛术不但要打麻药,在植毛过程中多多少少对人体的自然机能会有损害,并且植毛不能在一天之内就植完,反反复复要植许多遍。另外,植一脸髯胡,价格也不菲。而自然的髯胡两三个月就会长到剃除前的长度。
“瓦尔特”这么要求,显然是为了出口恶气,故意刁难人。
既然这样不依不饶,张洪利便耍起横来。他知道,今天是自己的过错,加上“秀才遇了兵,有理说不清”,他不吵不闹也不理睬,两手一抱,站到一边,任凭“瓦尔特”怎样地发火,怎样地咒骂。
整个店堂的人好像统一了认识似的,都不再搭话。
“瓦尔特”越吵越气,分明是自己占理,造型发屋的过错,却没人出面主持正义,他肺都气炸了,气势汹汹,冷不丁儿猛地抛出一句话来:“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当年的‘瓦尔特’,我坐了二十年牢,刚从那地方出来,我连坐牢都不怕,还怕你个小剃头匠?”
“瓦尔特!”这个名字使在场一些年龄大点的人吃惊不。年轻人虽然没有亲眼看见过那个一头绵羊毛卷卷发,两髯美胡须,穿着花格子衣服的“年轻人”,但是也时不时地听到过这个城市一些人说起过。虽未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每当有些人在年轻人面前吹到当年的“瓦尔特”时,年轻人就会这么回答。
年纪稍大些的人们不禁想起了当年那个鹤立鸡群,以异域风情的形式,穿行于一大群清一色中山装人群中的“年轻人”。
年轻一点儿的人们也觉得自己今天有幸一睹“瓦尔特”的尊容,没算白来。
没有想到的是,这位被先辈们讲得神乎其神的当年社会混混,小流氓,如今竟然以这样的形式重出江湖,来到现在的“第一美”。
他掷地有声,还真有震撼力。
张洪利用惊奇的眼光看着他:“对不起,前辈,晚辈有眼无珠,冒犯了前辈,您大人大量,不要与晚辈一般见识。请您原谅晚辈吧,从此交个朋友,今后有用得上的时候,言语一声,晚辈绝不推辞。”
他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再不保持着与顾客僵硬的态度了。
关于“瓦尔特”的故事,张洪利在来义渡城后,也曾经听人活灵讲。
他真有些后悔,为啥早不知道眼前这位顾客就是当年的“瓦尔特”,对待这样一个维护自己髯胡的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记得有一次,张洪利遇到过一件类似的令人遗憾的事。
那时他还、,与父亲从邻村回家,路过一个村落,村尾有一棵偌大的“拐子”树(生长在南方山区,果实“拐子”味香甜,可入药,泡酒或生吃),上面结满了紫红色的“拐子”,阳光照射下,小风轻吹,那树摇曳着树枝,就像是招呼人们快去摘它的“拐子”吃,以解除路途的饥渴一样。他当时就要去爬树摘“拐子”,被父亲制止了。一是母亲病危,不能耽误时间,要赶回去见母亲一面二是别人的东西是不能随便乱动的。他带着遗憾随父亲回了家。
几天后,母亲病情稳定下来,他便约了几个小伙伴,一路满怀信心,满怀希望地跑到邻村,他们要去摘“拐子”,拿回来给家人尝鲜,要泡酒孝敬长辈,要……结果,那树“拐子”一个果实也没有了,只剩下光光的树杈,凄惨地向着天空。满怀希望而去,落空而回,还邀约了么多伙伴,当时他羞愧得恨不能找个地缝钻下去。那感受,心情,降到了极低点。
今天,这“瓦尔特”来到“第一美”进行发髯造型,想必也是满怀希望,满怀信心,结果让他张洪利不经意中失手弄成这般模样,他肯定生气,他生气也是人之常情,情理之中。
许多顾客看老板转变了态度,跟着打圆场。说张老板如何厚道,为人如何诚恳,手艺如何精良,刚才一时是耳朵出了毛病,才怠慢顾客,弄成眼下这个样子,希望顾客原谅。有个年纪稍大的人对“瓦尔特”说,他们那一代是如何佩服“瓦尔特”当年的反叛精神,在那样的环境下,不掩饰自己对美的向往和追求,烫绵羊毛一样的卷卷发,留美丽的髯毛胡子,穿花格子衣服。人还转过脸来对大伙说,他是区人民医院五官科医生,前几天曾经给张老板作过检查,发现他耳骨二级损伤,影响听力,要不然是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尽管他说这话是临时编出来的,但看上去和听起来还真不像瞎说。
接着人又介绍说他老婆跟“瓦尔特”是一个街区。经他这么一提,“瓦尔特”便想起来了,那女人是社区的副书记。他从牢里出来后,是她给安排、收拾的住处,为他上的户口。那女人热情大方,不歧视劳改人员,“瓦尔特”对她印象很好,比较尊重。
“瓦尔特”便与人寒暄起来,谈得也比较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