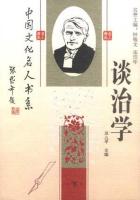东原以孟子举犬性、牛性、人性驳告子,故谓孟子“性善”之说,据人与禽兽比较而为言。余谓此非孟子本旨,但一时口给耳。后人视告子如外道,或曰异端,或曰异学。其实儒家论性,各有不同。赵邠卿注《孟子》,言告子兼治儒、墨之学。邠卿见《墨子》书亦载告子(《墨子》书中之告子与孟子所见未必为一人,以既与墨子同时,不得复与孟子同时也),故为是言。不知《墨子》书中之告子,本与墨子异趣,不得云兼治儒、墨之学也。宋儒以告子为异端,东原亦目之为异端,此其疏也。
《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唯说“理气”语不谬(大旨取罗整庵),论理与欲亦当。至阐发“性善”之言,均属难信。其后承东原之学者,皆善小学、说经、地理诸学,唯焦里堂(循)作《孟子正义》,不得不采《字义疏证》之说(近黄式三亦有发挥东原之言)。要之东原之说,在清儒中自可卓然成家,若谓可以推倒宋儒(段若膺作挽词有“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语,太过),则未敢信也。
道咸间方植之(东树)作《汉学商兑》,纠弹东原最力。近胡适尊信东原之说,假之以申唯物主义。然“理在事物而不在心”一语,实东原之大谬也。
道家
数道家当以老子为首。《汉书?艺文志》“道家”首举伊尹、太公。然其书真伪不可知,或出后人依托。《管子》之书,可以征信,唯其词意繁富,杂糅儒家、道家,难寻其指归。太史公言其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盖《管子》之大用在此。黄、老并称,始于周末,盛行于汉初。如史称环渊学黄老道德之术,陈丞相少时,好黄帝、老子之术,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王生处土善为黄老言。然黄帝论道之书,今不可见。《儒林传》:“黄生与辕固争论汤武革命,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贯于足。”其语见《太公六韬》。然今所传《六韬》不可信,故数道家当以老子为首。
《庄子?天下篇》,自言与老聘、关尹不同道。老子多政治语,庄子无之。庄子多超人语,老子则罕言。虽大旨相同,而各有偏重,所以异也。《老子》书八十一章,或论政治,或出政治之外,前后似无系统。今先论其关于政治之语。
老子论政,不出“因”字。所谓“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是也。严几道(复)附会其说,以为老子倡民主政治。以余观之,老子亦有极端专制语,其云“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非极端专制而何?凡尚论古人,必审其时世。老子生春秋之世,其时政权操于贵族,不但民主政治未易言,即专制政治亦未易言。故其书有民主语,亦有专制语。即孔子亦然。在贵族用事之时,唯恐国君之不能专制耳。国君苟能专制,其必有愈于世卿专政之局,故曰:“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然此二语,法家所以为根本。
太史公以老子、韩非同传,于学术源流最为明了。韩非解老、喻老而成法家,然则法家者,道家之别子耳。余谓老子譬之大医,医方众品并列,指事施用,都可疗病。五千言所包亦广矣,得其一术,即可以君人南面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