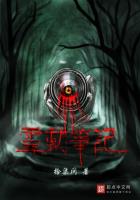凌书南再回来时,身后已跟着郦天霄和君由绛。郦天霄看了一眼脑袋歪在椅背上的孙玉钦,轻笑道:“到底还是旧情人出马,事半功倍。”
“那也得有太子爷的蒙汗药才行。”凌书南淡淡道,那蒙汗药就被她洒在帕子上,用帕子擦菜刀,再削起桂花糕来,自然就神不知鬼不觉地带了上去。郦天霄不愧是用毒用药高手,孙玉钦服了药只是微微有了困意,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被下了药。她从他身上搜出密函,小心取出来递给郦天霄看后,又重新将那密函封好,放回原处。
等药效一过,孙玉钦只当自己是倦了累了,不小心睡着了,根本不会猜到自己是被她下了药。
凌书南将密函放妥帖后,深深看了他一眼,转而对郦天霄道:“既然太子爷已从密函知晓孙聚堂儿媳下落,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上路吧!”
对于凌书南的积极,郦天霄若有所悟,她对孙玉钦存着相护之心呢!
君由绛上前来,小声道:“主子,可要卑职去打发了这茶馆老板?”
郦天霄心念一动,“何必打草惊蛇?我去同他说两句便是。”
那茶馆老板远远躲在厨房里,多年生意经,他自是认定了少听少看生意才能做得长久。眼见那英气逼人的贵公子朝自己走来,将一袋沉甸甸的钱囊扔给自己,老板连忙道:“公子放心,小的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不知道。”
“错,他若问起,你据实相告就对了!”郦天霄回望,天色渐暗,昏暗中,只看见那女人站在门口,仍旧望着孙玉钦的方向,他的唇边已起了一丝笑意。
孙玉钦悠悠转转地醒过来,惊觉天都已经黑了。
他唤来老板,问道:“怎么不叫醒我?”
“见公子睡得香,不敢打搅。”老板赔笑道,“小的去为公子提壶热茶来。”
孙玉钦点点头,觉得身上微微有些凉意,他伸展了下筋骨,正要拢拢身上的袍子,忽然觉察出一丝不对劲,伸手就翻出了藏于袖中的密函,他明明记得这密函是放在右手袖筒口袋的,怎么此时却到左边来了?
孙玉钦心里一凛,狐疑又警惕地打量起老板,“我睡着后,可有人靠近?”
“这……”老板微微迟疑,正对上孙玉钦探究的目光,他只得据实说道,“公子小睡时,与公子一同来的那位姑娘领了两位公子来,小的不便在场,就进了厨房,也不知他们是何时走的。”
“领了两位公子?”孙玉钦神色一变,心下已是一冷,“是什么样的两位公子?”
“像是一主一仆。”老板小心翼翼地描述着那两人的模样,孙玉钦的面色越来越差,到最后突然像发了狂似的,将那一碟桂花糕使劲地往地上摔去。
“好啊!好一个借尸还魂!”孙玉钦只觉得齿间酸冷,什么不是阿南,借尸还魂这样的鬼话都编得出来,她根本就是为了那封密信而来!他不懂,那郦天霄就有那么好?能让她如此心甘情愿地为他驱使,连他与她往日的情分都成了她利用的筹码?
他的拳头越捏越紧,双目中火光迸发,好啊,你既认为郦天霄是你的良人,那我倒要拭目以待!
君由绛眼见郦天霄换了一身粗布衣裳,又把自己的脸涂成了灰黄色,不禁有些忧心道:“主子,就我们三个人去武昌城,会不会太危险了?”
“大张旗鼓地去,才最危险。”郦天霄又取了些女子敷面的粉涂了涂自己的嘴唇,“生怕武昌城的人不知道本太子去了吗?”
“可是,卑职有一事不明,殿下为何要让孙玉钦发现我们已知密函内容?他若是向皇上告发,那皇上不就知晓殿下有意龙珠?”
“孙玉钦不会告发的,真正偷看密函的人可是那女人,若是追究起来,她才是第一个该死的。”郦天霄成竹在胸,“别看孙玉钦表面上好像放下了,其实心里恨着呢,他对本王越是恨,说明对那女人越是爱,他不会舍得让她死的。”
君由绛越发不懂了,“可他如此恨主子,不知会生出什么事端来暗害主子。”
“本王要的就是他的暗害!”郦天霄笑道,“皇叔探子那么多,必定知道本王与他因一个女人结仇,只怕就算他向皇叔告发些什么,皇叔也未必信他。最好他能拿把刀来捅我,我迫于无奈,只好取了他的性命,报到皇叔那,也只不过是为了个女人争执,一时失手杀了他而已。皇叔顶多训斥我两句,又能如何?”
君由绛这才恍然大悟,他就说他的主子品味一向很正常,怎么独独为了这么个质素一般的女人失了方寸,原来一切都只是在演戏而已。
门外响起敲门声,君由绛一打开,就瞧见一个妇人站在门口,颇有些不满道:“你怎么还没换衣裳?”
君由绛茫然地看着她,不知这个皮肤黝黑的妇人从哪里来,警惕道:“你是何人?”
那妇人顿时哈哈大笑起来,君由绛这才意识到眼前的妇人正是凌书南。
郦天霄不由赞道,“看不出来,易容术倒是不赖。”
凌书南不过是往脸上糊点面粉,稍稍改变一下鼻尖、下巴与额头的形状,再调点颜料改变肤色,对她而言,这实在是再简单不过的技艺。她斜了郦天霄一眼,饶是他已经将自己装扮成一个肤色暗沉的寻常百姓,那双眼睛还是能轻易地出卖他。
“太子爷,要不你就扮成一个重病的人好了。”只要闭眼装死,就不容易惹人怀疑。
郦天霄觉得这个主意还算不错,扬了扬眉,道:“还叫我太子爷?”
凌书南点头,“那怎么称呼呢?”
郦天霄道:“自然是扮成寻常夫妻入城。”
“夫妻?我和你?”凌书南眼睛瞪得大大的,一脸的不情愿。
郦天霄面色一冷,把手里头的脂粉盒往镜前一扔,冷笑道:“就你也配与本王假扮夫妻?自然是你们二人。”
君由绛颇有几分不情愿,但是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也只有忍了。
凌书南倒是面色一松,老实说,只要不和郦天霄扮夫妻,其他人她倒是不太在意。
郦天霄忽然就心情不佳了,斥责君由绛道:“杵着做什么?还不去换装?”
君由绛驾着马车,忽然轻咳一声,低声提示道:“马上要入城了。”
原本坐直身子的郦天霄,只得扯过被子,把腿一伸,乖乖躺下。
只听外头有人大声问道:“什么人?进城干什么?”
君由绛赔笑道:“二位军爷好,我大舅子生重病,我们乡下的赤脚大夫不中用,一直不见好,所以想到城里来寻个好大夫瞧瞧,还望军爷通融。”
守城的军爷立马挑起车帘往车内探,只见一个满面愁容的妇人守在一个脸色蜡黄的男子,便问道:“他是你什么人?得了什么病?”
凌书南抬眼,见是一蓝甲护军,虽然他问得紧迫,却并不凶悍,就说道:“他是我母家兄长,姓任单名一个渣字,那大夫说,他得了肺痨,只怕……只怕是活不成了。”
平躺着的郦天霄心里一垮,肺痨?这女人当真说得出口,竟然诅咒自己得这种病!虽然他不知道“任渣”这个名字有什么寓意,可是听起来,就不是什么好名字!他恨不得使劲踹那女人一脚,可偏偏自己现在“重病垂危”,他只好隐忍着。非但如此,他还得配合地咳嗽着,喘息着。
蓝甲护军一听是肺痨,下意识地就往后退了一步,担忧道:“娘子,这肺痨极易传染,你自己可别染上了!”
凌书南愁苦道:“到底是我亲哥哥,难道要我置之不理吗?”
蓝甲护军不禁动容,“娘子真是仁孝至极。”他朝她抱了抱拳,“城东头有一家回春堂,那堂中大夫是黄昏大侠的嫡传弟子,医术十分高超,定能治好你大哥。娘子只消往城东去,随处问便是,无人不知那家医馆。”
另一护军也道:“赶紧放行吧,别耽误他们看病。”
马车竟这样轻轻松松地进了武昌城。
入城后,外头的君由绛不禁低声朝里边道:“到底是些不正规的护军,如此盘查,只怕早已是满城奸细。”
郦天霄稍稍打起窗帘向外张望,叹息道:“可偏偏就是这五百不正规护军,却能将偌大个武昌城管理得井井有条。”
“五百?整个武昌城里就只有五百守军?”
“应该说,所有的衙役、守城与巡逻士兵合起来不过五百人。”郦天霄的话顿时让凌书南震动,自入城时,她便已觉十分蹊跷,原本她以为武昌是旧朝废都,定然十分凋敝,可万万没有想到,武昌城却是一派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商铺栉比如鳞,往来的贩夫走卒不断,喧闹却极有秩序,沿着主街一路走下来,一个乞丐都没有。
凌书南啧啧称奇,以她在现代的经验,除非碰到奥运、世博,否则就算城管再给力,乞讨的总还是能瞧见一两个,现在这里那么繁荣,要不是这五百个护军能力太强,那就只能说武昌城太富庶。
她不禁好奇道:“这武昌城的太守是什么人,竟能让所有人都丰衣足食?”
“太守?武昌城并无太守。”郦天霄苦笑道,“整个武昌城只设一个衙门,由各里长推选出二十一名德高望重之人共同决断城中事务。护军则是城中成年男子轮值,两年一换。至于监管者,听说是一个名唤无谋的西山弟子。因他是黄昏的高徒,武昌城内无人不服。武昌城的人是不是丰衣足食倒不可知,不过此处因受黄昏感召,佛学盛行,人们不独亲其亲,鳏寡孤独皆有所养,是以看起来,倒是一派祥和,当真是百闻不如一见。”想来郦天霄也为武昌城中的所见所闻而叹服。
凌书南自是动容,可又有些不解,“过了武昌城就是曾境,既然武昌城只有五百护军,为何皇上不派兵占了武昌,却由得他们繁盛起来?而且,我瞧着这武昌城地处平原,完全无山势可依,想来是极易攻克吧?”
郦天霄冷哼道:“你当他不想?只不过离武昌城不远的乌林城有一位旧吴国的常胜将军郭开。当初郭开遭人诬陷,没有兵权,是以轩辕季南下时,整个吴国都没有人可以与他抗衡。直到攻入京城,郭开临危受命,竟和轩辕季对峙近一月,双方输赢各占一半,足可见其本事。若不是他,只怕当初整个吴国皇族都要覆灭了。不过,想必那郭开对吴末帝还是心存怨愤,拒不出兵收回失地。轩辕季退兵后,各藩王大将各自为政,吴末帝身死,郭开便率了五千铁甲兵入乌林城固守,直到如今。乌林城易守难攻,离武昌城不过百里,他的铁骑兵一个时辰便可来回一趟。皇叔对他很是忌惮,如何敢在他眼皮子底下攻占武昌?”
原来如此,凌书南听着外边的吆喝声、叫卖声不断,倒是由衷希望这声音能够长久下去。
“请留步!”背后传来一声叫唤,君由绛回转头,却是之前守城门的蓝甲护军跟了来,他心下一紧,赔笑道:“军爷还有什么事吗?”
蓝甲护军道:“我想了想,你们对这里不熟,还是我带你们抄近路去医馆好了。”
“这……军爷守城军务繁重,这个,怎么敢劳烦?不妨事的,我们自己寻去就好了!”君由绛万万没想到这护军如此好心,可殿下原本就没病,若是去了医馆一搭脉,不就穿帮了?
“不妨事,有其他人在那儿。”蓝甲护军小跑着就要在前边开路。
君由绛僵在那里,“我们也不是那么急,我们还是先找个客栈安顿下来,歇息片刻。”
那护军顿时就急了,“救人如救火,怎么可能不急?”
车内,郦天霄有些按捺不住,连忙朝凌书南使了个眼色,再这样僵持下去,那护军势必会怀疑他们的身份,那可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凌书南连忙打起帘子对君由绛道:“当家的,连军爷都知道救人如救火,我哥哥都这副模样了,我们还安顿些什么?赶紧去找大夫啊!”
护军连连点头道:“娘子放心,无求大夫定能治好任渣大哥。”
郦天霄听了这名字再度抽了抽。
那蓝甲护军十分热心,领着三人很快便到了回春堂,凌书南从车上下来,一面千恩万谢,一面劝他早些回去。
蓝甲护军却非要送佛送到西,“我替你进去瞧瞧,若是没有紧急的病人,好教无求大师先诊治任渣大哥。”不等凌书南回答,他就一溜小跑地进了回春堂,只剩下凌书南和君由绛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
不一会儿,就见一慈眉善目五十来岁的长者跟着护军出来,此人正是回春堂的大夫无求。君由绛刚把郦天霄从车里背出来,无求大夫捋着胡须就走上前来,悬指去搭郦天霄的脉。
君由绛心里一突,道:“大夫,何不进去之后再诊,这扛在背上,哪里看得出来什么?”
无求大夫却是眉头一紧,捏着郦天霄的手大声道:“且慢!这位壮士当真是得了肺痨吗?”
郦天霄不由一凛,饶是他刻意运气将脉搏调得紊乱不齐,可这大夫还是一下子就觉察到了不妥,倘若当众被人揭穿,只怕这武昌城是不好待了。
“倘若是肺痨,想必是阴阳两虚,阴虚不能内守,阳虚卫外不固,在脉象上,该是细数无力,呈心肺阴津亏虚之象,却不至于是现在这般忽快忽慢,倒像是有人用内息特意压制似的。”
君由绛到底有些沉不住气,挪了一手就准备发难,偏此时门里一个人影抢了过来,却是对无求大夫道:“师兄,你让我来诊治看看。”不由分说,他就将手搭在了郦天霄的另一只手上,道,“脉象时而作洪脉,气盛血涌,时而细弱游丝,为邪气阻压,当真不是肺痨,却是比肺痨还严重十倍的病,名唤大雾瘤,只怕这世上除了师父,无人能救了!”
旁人一听,不禁欷歔,只有凌书南瞠目结舌地看着眼前的人,竟然这么快就相见了!还是在这里!
那人正是无筹小和尚!
无求大夫很不认同,道:“无筹,你真正入门不过半载,你几时学的医术?我怎么从来没听过这种病?”
无筹道:“大师兄,这是师父新近教我的,听说这种病从前并没有,也是最近才发现的。好了,咱们都别站着说话了,我先带他们到后边去医治。”说罢,就冲凌书南眨了眨眼,领着郦天霄和君由绛入内。这个小和尚,之前一个劲地说出家人不打诳语,没想到,现在说起谎话来,倒是顺溜极了。
凌书南一进屋,见再无旁人,便立马高兴地拉着无筹道:“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回西山了吗?”
无筹红脸道:“西山便在武昌城外不远,我等大师兄看完病人,好一起上山去。”
是了,这个无求大夫也是黄昏的徒弟,在这里遇见无筹倒也算不得大意外。凌书南十分欣慰,“那日分别时太匆忙,都忘了问该如何寻你。现在可好,老天爷又把你送到姐姐面前了。”
无筹尴尬地挠了挠头,面色绯红,小声说道:“无筹也很挂念姐姐的。”
凌书南正觉得暖心,趴在君由绛身上的郦天霄却轻哼了一声,道:“放本王下来。”
无筹斜看了他一眼,见四下无人,对凌书南低声问道:“姐姐,你们为何乔装来武昌,若非无筹事先得知,只怕都认不出姐姐。”
对无筹自然不好说实话,倒是一旁的郦天霄开腔道:“我们特来此拜会黄昏大侠,只因我身份不便,恐生事端,是以乔装而来。”
无筹面色已缓,对郦天霄却是不冷不热,“我师父忙得很,倒不一定有空接见太子殿下。”他对郦天霄这番话倒是深信不疑,谁让黄昏盛名,郦天霄更是一早就表示过要上西山拜会。
凌书南想起无筹方才的话,不由奇道:“你说你事先得知,你怎会知道我们要来?”
“是孙大哥告诉我你们要来武昌。”
凌书南闻言心下一凛,“孙玉钦?!”她去而复返时孙玉钦已经睡死,他没道理知道他们的计划。难道这一路赶来,被他撞见了?她下意识地看了郦天霄一眼,他倒是面色不改,只是问道:“他现在何处?”
无筹撇了撇嘴,“他走了,怕是这里有他不想见到的人吧。”
凌书南默然不语,无筹感觉气氛不佳,越发觉得爱情这东西害人不浅。他在凌书南耳畔悄声道:“姐姐,你们放心在此歇息吧,有事叫我便是。”这便合上门,退了出去。
凌书南不禁忧心道:“没想到他已经知晓我们来此,那我们如何暗中寻访钟氏?”她实在不想孙玉钦卷入这龙珠争夺战,更不想他打乱自己集齐龙珠的计划。
“我们?”郦天霄倒是心情不太坏,头一次,这女人倒像是站在他这一边,为他忧心起来。
一旁的君由绛却是警惕地提醒道:“主子,这家伙躲在暗处,不会有什么别的意图吧?”
郦天霄斜睨了君由绛一眼,满眼笑意,他巴不得孙玉钦先对他下手呢!
他怡然自得地往椅子上坐了,“他故意躲着我们,自然是想伺机而动,好来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只不过,他不过是个没有一兵一卒的无用书生,怕他作甚?”
凌书南却是愁眉紧锁,咬牙道:“不管怎样,我们一定要先他一步拿到龙珠才行,到时候,再想办法糊弄他好了!”
郦天霄打量了凌书南一眼,奇道:“看不出来,你倒是比我还上心。哦,是了,还有三天就又是七日之期,你卖力些也是应该的。”
凌书南尴尬地笑了笑,推了君由绛一把,“当家的,你还不出去买些吃的?”
君由绛被她那一句“当家的”,叫得起了满身鸡皮疙瘩,见郦天霄也朝自己挥挥手,便连忙奔了出去。
因已经知晓钟氏下落,君由绛很快就将钟氏的现状和住处打探清楚。
孙聚德早死,其子孙淼下落不明。孙淼之妻钟氏改名换姓,另嫁给一个姓欧阳的富庶男子,隐姓埋名在武昌城中过活。
听闻当初,孙聚德与孙淼父子掌管吴国京畿守备,正值轩辕季南下之际,孙聚德忽然暴毙于府中。之后孙淼领兵护送吴末帝到瀛洲,因记挂留在武昌的娇妻钟氏,听闻武昌城破,便又领兵从瀛洲返回武昌,之后就再没有他的下落了。至于钟氏,因为平日里深居简出,又是个妇人,自然没有人关注她。只是前些日子,她因频频出门买安神药物,被人认了出来。孙淼乃是吴国掌权王族,手中自然也有一枚龙珠,只是他失踪已久,极有可能已不在人间,那他的爱妻钟氏,便是最有可能知晓龙珠下落的人。
若是贸然把钟氏捉来,搞不好,一无所获不说,还打草惊蛇,贻人话柄。最重要的是,明着来,得了龙珠,就只有乖乖交给郦圭。想来想去,还是要先想办法接近钟氏,探听虚实才好做打算。凌书南听君由绛说完,就已经拿定主意,“明日一早,我就去她家门口卖身好了!”
郦天霄一口茶喷了出来,“她是个女的!要你干什么?”
凌书南茫然地抬起头,“难道女的就不要下人干活了吗?”
对了,卖身还可以指卖身为奴,郦天霄端起茶碗缓缓地喝了口茶,一声不吭。
欧阳宅的门口一大早就传来了哭声,惹得欧阳宅的家仆们十分不满。
一个黑脸妇人跪在门口号啕大哭,见有家仆出来,连忙抱着他的腿道:“大哥,行行好吧,我哥哥病重不治,无钱安葬,奴家没有什么本事,就一双手有些力气,请大哥可怜我,收我为奴,只要五两银子做安葬费,奴家愿意终身为奴。”
那家仆十分为难,“我家不缺下人,这位娘子请回吧。”
黑脸妇人哪里肯放手,“大哥,只要五两银子,五两银子就可以买奴家终身,奴家砍柴挑水做饭,样样都是一把好手。”
那家仆气极,“我们都不知道还能干多久,哪里还能做主把你买了,你到别家去吧!”
许是这边动静太大,周围已经聚了些人,一个路人看不下去,走过来,将五两银锭子塞到黑脸妇人的手里,道:“你赶紧拿去把你哥哥安葬了吧。”
拿到银锭子的黑脸妇人凌书南顿时满头黑线,正主没反应,她却反被其他人买去,这可怎么是好。她连忙把那枚银锭子塞回那路人手里,“谢谢这位大哥的好意,奴家已有夫君,只能卖身为奴,不能……”
未等她说完,那路人就道:“我可没想要买你,这个就当是送给你的。”
背后的家仆也道:“娘子如今可以放心回去了。”
凌书南捏了把汗,差点忘了武昌城里民风极佳,压根轮不到她卖身。周围的人见她凝噎不语,纷纷慷慨解囊,不过片刻,她的裙里已堆了沉甸甸的一捧银钱。凌书南自穿越来此,就是两袖空空,此时平白得了这么多钱,心里冒出一个念头,在这武昌城里做个乞丐,倒是个不错的职业。
不过片刻的小差,背后那家仆却忽然发话道:“娘子留步,我家主母有请娘子。”
凌书南暗自心喜,没想到柳暗花明又一村!
端坐在堂上的欧阳夫人,也就是钟氏,是个四十岁上下的和蔼妇人。见凌书南捧着一摞银钱进来,忙命人给她备下了褡裢。她上下打量了一下凌书南,说道:“从来只听说卖身葬夫,女人家既然出嫁,娘家就是外姓人,怎么你却要为了兄长卖身?”
凌书南一怔,为什么,这还不是因为郦天霄是扮她的兄长,而不是夫君嘛。来的时候,所有人都瞧见是她的“兄长”得了“不治之症”,而她的“夫君”还活得好好的,她当然只好卖身葬兄了。但见钟氏问得认真,她也只好十分悲痛地答道:“我自幼便和兄长感情极好,只可惜我这兄长成日里不务正业,名声也不好,嫂子不堪忍受跟人跑了,可他到底是我的兄长,又生了这样的重病,我怎能不管?”
“话是如此,可你卖身,你夫君岂肯?说到底,你是他的人,只怕如此做,于礼不合,倒是要为人诟病的。”
“我没有想那么多,只想着兄妹间旧日的情分。”凌书南觉得钟氏挺无聊的,替她考虑这么多。
“旧日的情分……”钟氏沉吟着,忽而道,“可见在你心里头,怕是你兄长的分量要高于你的夫君。到底是个可怜的人,你先回去好好安葬你兄长吧,若是有什么难处,再来找我好了。”
凌书南听钟氏的口气,自己又捧着这许多银子,一时间倒是找不到理由留下来,说起来,没什么事比“安葬兄长”更紧迫了,她只好起身告辞。此时,一个家仆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夫人,他又开始乱咬东西了!”
钟氏神色一黯,朝凌书南挥了挥手,跟着那家仆就往后院去了。
凌书南随着另一家仆出来,发现这欧阳宅虽大,仆役却只有几个,不由好奇道:“夫人家业这么大,为何不多招些仆役,我看光这院子里的落叶就该请两个专人去扫才行。”
那家仆苦笑一声,自语道:“还多招?只怕就我们几个夫人也嫌多呢。”
“这是为何?”看起来,这欧阳府宅不像是家道落败,但那家仆却不敢再多说一言。
回到回春堂,凌书南忙把欧阳宅的情形说了。
“看起来,这个钟氏倒是对兄妹之情很在意。”郦天霄听完便吩咐君由绛再去打听,凌书南忙叫住他,补充道:“我看欧阳家的仆人是近期内才打发出去好些的,可寻一两个问问缘由。对了,你既说钟氏近来频频买安神药,只怕也有蹊跷,一并问了。”
君由绛颇为不情愿,自己是太子亲卫,只听命太子,怎么这女人倒搞得一副女主人的架势,命令起他来了。郦天霄见他杵着不动,斥道:“没听见吩咐?还不快去!”
君由绛虽然委屈,只得吞声退了出去。
一时回来,倒是带了大消息,“卑职寻了一个旧仆,他说欧阳夫人自嫁入欧阳家,就将一个昏睡不醒的男子安置于东厢。据说那男子是她兄长,多年来从未苏醒过,但欧阳夫人却一直亲自照料,每日要为他净身、洗面、喂食。欧阳夫人也为他找大夫看过,但一直不见好。听说还去回春堂瞧过病,到底是黄昏大侠的高徒,没过多久,那男人突然醒了。只是男人一醒来就像发疯一样,成日里破口大骂,特别是一见到欧阳夫人,口中都是一些污秽之言,他不吃不喝,欧阳夫人只好命人强灌。他手脚被捆,牙齿却利得很,碗都咬碎了不知多少只。欧阳夫人的安神药就是给他买的,每次多少强灌下去点,待他睡着了,才能喂他喝点东西。不过,因着他大吵大嚷,欧阳夫人只恐府中人听到传扬出去,便将府里头大部分仆人打发出去,而东厢,一般人也是不让去的。”
“那人都骂些什么?”
“说得最多的就是狗男女三个字,还有就是数落欧阳夫人背叛他,说她不知廉耻,乱伦悖逆,和姓欧阳的那人是奸夫淫妇……”君由绛的话让郦天霄和凌书南心下一凛,不由面面相觑,即便是妹妹,男女有别,又岂能亲自为他净身洗面?而他醒来后说的话就更加不像是一个做兄长的说的。
郦天霄心念一动,立马便明白过来,只怕那个人根本就不是钟氏的什么兄长,而是失踪已久的孙淼!
凌书南则想,完了,怪不得钟氏一个劲地对她提什么兄妹之情,没想到,原来她和他的兄长有这样见不得光的事情!
此时,无求大夫的童子来报,说是外边来了个欧阳府的丫鬟。因无求和无筹已经前往西山,整个医馆只剩下几个童子、学徒,他们得了无筹的吩咐,并不来打搅,郦天霄安顿于此,倒也安心。
凌书南心中有了主意,一边扯过被子就往郦天霄头上蒙,一边对君由绛一阵耳语。郦天霄见君由绛刚开始还瞪圆了眼,后来竟然有笑意浮出来,也不知他们说了什么,正要探问,凌书南却使劲地把被子往郦天霄头顶一盖,按倒在床,哭喊起来,“我的哥哥啊,你死得好惨啊!你怎么能丢下我一个人,就去那阎罗殿啦!”
被子里的郦天霄一僵,正要发作,却听外边脚步声已近,只好忍气吞声地乖乖躺下,心里头直喊晦气,他堂堂太子居然要在这里挺尸,这女人是故意整他的吧?
“哭,谁许你哭的!”背后的君由绛破口大骂起来,“你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居然还敢跑到外边去卖身葬他?我呸!你是我娶回家的,就是做猪做狗也是我家的,谁许你卖?”
那丫鬟已走到门口,只好轻咳一声,凌书南抹着泪回头看她,那丫鬟忙道:“娘子早上走得匆忙,我家主母特意命我送些银两和布匹给娘子。”
凌书南感激地接过,抚摸着那锦缎道:“倒是该好好给哥哥做件寿衣才是。”
被子里的郦天霄心底一抽,君由绛却是一把将银两和锦缎抢了过去,恶狠狠地道:“做什么寿衣?!就他也配?”
凌书南忙去抢,“你快还给我,还给我!那是恩人给我的!”她话未说完,就被君由绛踢了一脚,凌书南顿时就恶狠狠地瞪向君由绛,吃痛道,“你……你踢我?”
“踢你怎么了?”自凌书南要君由绛演这出戏起,他就已经打定主意要出口恶气,他本来就瞧凌书南不爽,而这女人更是害他多次遭到训斥,这会儿是她主动要求的,他当然不能白白浪费这样的好机会,“你这女人做出这样乱伦苟且的事来,坏我门楣,居然还敢收人家东西,踢死你也不为过!”说着,一掌就又往凌书南挥过去。
随便演出戏而已,用得着这么认真吗?又没有人给他颁发奥斯卡奖!眼见君由绛气势汹汹,凌书南忙不迭地往后一退,她脚底一踉,重心不稳,一屁股坐在郦天霄的身上。
郦天霄听他二人的对话,终于明白凌书南给君由绛出了个啥主意,正哭笑不得,忽然腰间一阵剧痛,凌书南滚圆的屁股直直压了下来,差点没把郦天霄给惊得“诈尸”,虽然气得不行,却也只好捂在被子里不敢发声,直到凌书南拉着那丫鬟,哭喊着求她相护,他身上才一松,腰间的酸痛消除了些。
待凌书南哭哭啼啼地被君由绛赶出去,随着那丫鬟走了,郦天霄才一挺身坐了起来,眼见君由绛脸上的笑意尚未收回,郦天霄猛地一脚便朝他面门踢过去,许是太大力,腰间还隐隐作痛,“混账东西,胆子越发大了!”
君由绛吃了一脚,连忙跪倒在地,忐忑道:“卑职该死,卑职没想到会冲撞到主子,这个,都是那女人的主意!”
“做错事还只会推给旁人。”郦天霄重坐回床上,忍着痛道,“本王不过是让你们俩假扮夫妻,掩饰身份,你别失了分寸,还真当自己是一家之主了!”
君由绛听得两腿发抖,“卑职万万不敢!”他心底发凉,即便郦天霄知道他是为了配合凌书南演戏才数落了一下他的“大舅子”,可演员到底是太子殿下,即便是这样,他也不能忍受话语中对他的大不敬。
“知道就好。”好在郦天霄并没有发难,他闭着眼稍稍休息了下,待痛楚小了些,这才舒了口气睁开眼。他朝战战兢兢的君由绛瞟了一眼,见他脸上还挂着半个鞋印,轻描淡写道,“这一脚就当本王替那女人还给你的。”
……
君由绛有点跟不上郦天霄的节奏。
钟氏见丫鬟带着凌书南回来,又听得丫鬟一五一十将所见所闻汇报完毕,脸色已经铁青,“你那丈夫实在不像话!怎么这种兄妹乱伦的话也说得出口?”
凌书南叹了口气道:“我与兄长感情是好,有时候我自己也说不清是不是真的如他所言。”她抬起眼偷睨了钟氏一眼,却见钟氏瞪大了眼睛,“那可是你的亲哥哥!你怎么……”
凌书南一愣,难道她的猜测是错的?但钟氏最终只是摆了摆手,“也罢,感情的事,向来就是说不清道不明的,那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能有什么打算?我是有家回不得了,疼我的哥哥又死了,夫人,你待我这样好,你若是不嫌弃,就让我在你身边伺候吧!”凌书南恳切地望着她。
钟氏早已动了恻隐之心,眼见她无家可归,哪有不答应的道理,“也好,你先在我这儿待着,以后的事再慢慢看吧。不过,当下最重要的,是将你兄长安葬。”
凌书南一喜,忽而听到他们要帮她安葬郦天霄,连忙道:“不必!”见钟氏和丫鬟都狐疑地望着自己,她才满脸愁苦道,“回春堂的大夫说,他得的是比肺痨还要厉害十倍的顽疾,这世上除了黄昏大侠无人可医。可是他没等到黄昏大侠,就……大夫说了,他的病太重,不能随随便便就埋进土里,必须由他们亲手火化才行。”
“阿嚏——”回春堂中,正在揉腰的郦天霄身上忽然泛起一股寒意。
凌书南主动要求去厨房帮工,一来切菜切肉这种白案红案的活是最基本的,于她而言,手到擒来。二来,人总是要吃饭的,想要知道东厢那人的情形,饭食或许便是最佳突破口。
为了表达对钟氏的感激之情,凌书南带着“沉重的伤痛”当晚就开工了。因她刀工厉害,只是随便剞、劈、剔、拍,也比寻常人好太多,以致厨子每一样菜炒出来,都比寻常精致得多。钟氏正在前边用晚饭,一时高兴便将凌书南叫了过去,当面夸赞。
与钟氏一起用膳的,还有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看他坐在主位,想必就是欧阳宅的主人欧阳老爷了。凌书南上前行礼,道了声:“老爷,夫人。”
钟氏笑着向欧阳老爷道:“她就是我刚刚跟你提到的南嫂,真是个可怜的人。”
欧阳老爷扫了凌书南一眼,轻轻地捏了捏钟氏的手,对凌书南道:“夫人同我说了,你只管在这里住下,有什么难处直说便是。”他面色和善,看得出来,他对钟氏十分在意。
凌书南好容易挤出两滴眼泪,对欧阳老爷与钟氏又是一番感激涕零。
欧阳老爷忽然问道:“听夫人说,你与兄长感情极好?”
凌书南心里打了个突,钟氏因“兄妹之情”而怜悯她,欧阳老爷只怕不喜欢吧?她尴尬地笑了笑,“看起来不过比旁人好那么一点点,不过,其实也不怎么样的。”
“若不怎么样,你又何必卖身葬他?”欧阳老爷摇了摇头,眼中带了几分严厉道,“感情好便是好,何必理会其他人的目光。”
凌书南一怔,怎么欧阳老爷对“兄妹之情”的尺度比钟氏还大?他好像对“兄妹情深”深有同感似的,难不成他和钟氏是兄妹?那……钟氏藏着的那个发狂的男子却是谁?她心里一凛,猛地就有一个名字跳入她的脑海——是孙淼?!
见凌书南木木的,钟氏还当她是难为情,忙用手肘子撞了欧阳老爷一下,低声道:“这是我们女人家说的体己话,你问来做什么?”一面忙打发凌书南下去。
此时,一个婢女慌里慌张地跑了过来,满脸惊骇,欧阳老爷看她的神情,便明了道:“看来他又没吃。”
钟氏面色顿时犯苦,“做得如此精致,他也一口不吃?他就这么厌恶活着……”
那婢女又道:“他又把碗咬碎了,奴婢只要把他口中的布条取出来,他就到处乱咬,见什么咬什么,这一次……牙齿也崩断了一颗,满床都是碎屑和血……”
“什么?”钟氏有些坐不住,眼眶一瞬间便红了,“再这样下去,他非把自己弄死不可!”
此时不开腔更待何时,已经走到门口的凌书南折了回来,对钟氏道:“夫人府上可是有什么宠物不肯好好吃饭?我倒是有法子,让他不得不吃。”
“宠物?”一旁的欧阳老爷忍着笑意看钟氏,钟氏则十分尴尬,虽然想要隐瞒,但对凌书南的法子却又十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