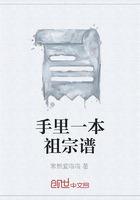清的手机号码 ◎文/曹兮
记住一个人的名字并不重要,关键是你能否记住那个人……
—题记
当什么都不再属于自己,只有身体这具空壳是自己的。
抬头望向天空,被我们称为誓言的星星,静静地闪烁着,仿佛在持续着多年前许下的心愿。
昏暗的路灯下,破碎的啤酒瓶散发着异样的色彩,鲜血落在翠绿色的玻璃上像是绽放着的玫瑰,我触摸着那血,贪恋它离开身体后残存的温度。
小心翼翼地将沾在手中的温暖贴近脸庞,但它却顺着泪痕蔓延开来。
我安静地掏出手机,拍下这一切,取名为“冷艳”。选择了那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号码,大拇指颤颤巍巍地按下“发送”。
酒精在血液里翻腾,它麻痹了神经,只让我晓得摇摇晃晃地走向远方。
远方……是一片曾开满铃兰花的地方。
如今,那里只剩荒草遍野。
铃兰花的根是永远不分的,每一对铃兰都是分不开的。清那曼妙旋律般的声音仍在我耳边,挥之不去。
懒懒地躺在草丛中,青草香掺和着泥土的腥味驱去了三分酒意,摊开满是鲜血的手机,等待着回复。
但我知道,我永远也只能是等待回复。
每一次想起清的时候都是这样,把自己搞得如此狼狈,犹如丧家之犬,明明知道她不会再给我任何回复,却又一遍遍地重复这无意义的举动,像是等断了线的风筝,明知它会迷失在风里,却还傻傻地在原地奢望着它会逆风回来,却不知它早已在风中离自己越来越远。
什么弱智的誓言,什么不变的承诺,都不是真的……
为什么……还叫我这样想她。
泪,涌出眼眶,无节制得像是长长的思念。
忽然觉得自己很没用,放了几年的手机号码到现在都不舍得删去,生怕它一旦从电话本中消失,清也会彻底从生命中消失一般,哪怕对方一直是关机,还是会不断地发短信过去。
不知为何,竟觉得这可笑的行为像是一场痛苦的单相思。
手机铃声在空旷的草地上响了许久,酒精使身体感觉不到力气,只好让它在那里孤独地响着。
因为知道永远都不会有她的来电,索性连接都不接。
已感到倦了,无论是这样的怀念,还是千篇一律的生活……抄起手机,踉跄着离开,朝着相反的方向,踏上回家的路。
醒来时,意识昏沉,昨日的种种也已记不起,身上的血迹干透后粘在身上,我拿起毛巾擦拭着满是鲜血的手机,用OK绷将伤口覆盖,洗去脸上的泪痕,盯着镜中的自己,仿佛昨天的颓废不复存在。
路过那片铃兰花海,突然觉得对于她的思念我要记下来,就算她看不见,我也会发到她手机上,哪怕每次都是关机,哪怕没有回复。
我一直都有种错觉,我们不过是分手,她一直都存在。
某月某日,下了很大的雨,和你离开时的那场雨一样。
我仰躺在床上,和朋友发着无聊的短信,当不知还要和朋友说些什么时,忽然想起,家里没有酒了。
外面的雨不是太大,没有拿伞就进了雨里,还没走出多久,就看到举着花伞的萱,她是清的妹妹,也是我的秘书,我明白她是打电话找不到我才来的。
“经理……”
“抱歉,我现在没心情谈公务。”我疯狂地奔跑在远去的路上,将她甩在身后,看她不再追来后,我便停了下来,浑身都已湿透又不想再回去,环顾四周才发现走岔了路,来到了那片铃兰花海。
还记得清曾告诉我的铃兰花语是永远相守。啊……对了……当时我还笑着骂她白痴,她没有还嘴只是甜甜地笑了。这里铃兰还都没有开,我想它是永远都不会开了吧。
昨日的悲伤原以为它已成过去,却没想到它会在心里扎根发芽,我莫名地笑了,凄凉且僵硬,我为什么这么傻?明知她已不会再回来了……
脑海里关于她的记忆模糊得只剩下一片铃兰,曾那么想要记住,曾那样告诫过自己不能忘记,但我却未能敌得过时间的冲洗,越想要记住的,忘记得越快。
“干吗要淋雨?”萱还是赶了过来,将伞移到我头上,“你这样会感冒的。”
“习惯了……”我离开她的伞下,继续走远。
“别这样,姐姐知道会伤心。”
伤心?若真是这样她也不会就此轻易地离开了。
但……如果……如果有一天,患病的人是我而不是清,她会像现在的我一样,还是会忘记我?我情愿她忘记我,就像不曾存在过,因为相思一个人,太苦了……
今天的雨很大,可能会下好几天。
银河中有一个淡蓝色的星星,你为它起名叫做誓言。
某年的七夕,天上的星星多得令人难以想象。
清拉着我到郊外的河边去看星星,我虽不停地骂她是笨蛋,却还是跟着她坐在草地上望向天空。
我不懂她为何要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些光亮点,不一会儿她突然拽住我指着银河里一颗淡蓝色的星星,她说那叫誓言星。
“岚,我们许个愿好不好。”
“不要。”
“哦。”清低着头不说话。
“生气了?”
“没有。”她歪着头天真地笑着。
我最后还是屈服了,她那唯美的笑容,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拒绝的。
“好了好了!我输了!我许,我许还不行吗?”
“嗯。”她依旧笑如春花,“我先许!我说……嗯……要永远幸福……”清说这话时,看了看我。
“白痴!许这种愿干什么!”
那个夜晚,她许下要幸福的誓言,而我却什么也没说,直至现在我也不知该许些什么,或许我也该和她许同样的愿,因为从我们分手那天,我认定了真实,从认定真实的那瞬间起,平凡的幸福就不复存在了,我挺羡慕清的,永远活在梦里,永远笑着,永远翻开手机看着我的手机号码,她或许已经得到幸福了,或在梦里的人是幸福的,因为真实要比梦幻残忍且脆弱,让人无法忍受甚至崩溃。
隔年的七夕,清离开了,那天没有星星,下了场极大的雨,将盛开着的铃兰都一个个地打掉,雨停后,草地上白花花的都是铃兰的尸体。
今年七夕,我和萱一起去墓地看她。
她的墓周围都是铃兰,我放了一束玫瑰在墓上,它在雪白中显得很尴尬,是一种刺眼的不融于周围的存在。
“为什么要送玫瑰?”萱蹲下身子,恭敬地擦掉墓碑上的尘土。
“不为什么……”我不想再多待一刻,转身坐上了车。
其实,我在等待那束玫瑰枯萎,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痛……
二月十四日,情人节。
她离开后的多少个情人节我已经记不清了,虽然总会收到萱给的巧克力,但最后总是会因为放的时间太久而被当做垃圾丢掉。
没有目的地游走在大街上,到处都有巧克力的身影,清和普通女孩子一样很喜欢巧克力的味道。
脚步,在看到一家熟悉的店面后停留,那是清常来的巧克力店。
轻盈的铃声响起,一句温柔的“欢迎光临”,货架上摆着五颜六色的巧克力盒。
“你好,是准备买巧克力送人吗?”
“啊?算……算是吧……”
“那您看中哪一款了?”我随手指了一个褐色的带有白色花边的巧克力,服务生拿了起来进了工作间,问我要在巧克力上写些什么。
我想了想翻开手机给他看了那个手机号码,他皱皱眉但还是写在了上面。
“谢谢惠顾……”
手中紫色的礼盒中放着不知该送给谁的巧克力,看了看街上似乎多了很多情侣,也许本就那么多,只是我没注意到罢了。
“萱,你在家吗?”黑色的情人节,我不知该去向哪里,只好打电话给萱。
“在。”
“我想去你家。”
“好,我等你……”她等我先挂了电话,她才挂断,和清的习惯一样。
当我到达她家门前,她正疑惑地盯着我手中的盒子。
“送给你的。”我侧着身进了屋,缩在沙发上换电视看。萱小心翼翼地拆开盒子,当她看到巧克力上的号码时,明亮的双眼挂着泪花。
“姐姐好幸福。”她又将盖子放回,按原样将盒子包装好。
“为什么这么讲?”
“她都已离开这么久,你却还能记得她。”
我没有告诉她我早已忘记清的模样……
“我们……结婚吧……”
“你……”她奇怪地看着我,然后笑着摇摇头,“但是……”
“放心,我从未把你当做她的代替品。”
萱没有回答,只是像清一样,微微地笑着。
今年的我过的依旧是没有情人的情人节,萱打电话过来说她将那盒巧克力埋在了那片铃兰花地里。
那个巧克力上写着的,是清的手机号码……
海边,我悄悄地走向海的中心,只为能体会你所讲的幸福。
“清,来海边干什么?”
“看海。”她脱了凉鞋,奔向海浪,像是一朵飘在风里的花。
天气一热,连海风都是热的,我一屁股坐在沙滩上,汗珠挂满全身。
“岚,你说海的颜色漂亮吗?”
“反正我不喜欢。”我看见清迷茫地盯着远方,白皙的脸上不带有丝毫的血色。
“那你喜欢什么颜色?”
“黑色……”
“好单调呀……”她起身走向海,“要是海能变成紫色就好了……”
她继续向前走着,我不明白她要做什么,只能坐在沙滩上看着她,海浪轻轻地打着她的裙边,清的长发肆无忌惮地飘散。
她一直平静地走着,我不知道这海有多深。海水漫过清的肩膀,她抬起头凝视远方,我如梦方醒般,却见到她转过头,淡淡地微笑。
“岚,你看……”
“清!快回来!”我快速地跑了过去,生怕她会从我眼前消失。
“海变成紫色的了……”她在水中摇摇晃晃,那一刻,双眼模糊。
那一次,差一点就失去她,但清却跟我讲她只是为了看到紫色的海。
我问她,你看到了吗?
她说,没有。
我知道她要找的不是什么紫色的海,而是幸福。
我一直都无法给她幸福,她却说跟我在一起就是最幸福的。
可我早已忘记……什么叫做幸福……
如果爱有天意……
久远的事全部都发生在昨天,直到现在我还没醒,我不愿意清醒,总害怕一旦醒来,我便要把过去抛弃,总想着我的现在永远也不要来,就像被封印在了那个手机号码上,永远沉睡,不会解开。
铃兰花,在五月的不安与骚动中一串串地开了。
我站在其中,想象着清还会回来,我不想忘记,她曾是我的唯一。
“花……很美……”萱站在身旁,抚摸着手中的花朵。
“你说……清希望我忘记她吗……”
“是呀,姐姐会希望你忘记她,希望你幸福。”我清楚地知道清的占有欲,她如此贪婪地从我身上得到幸福自然也不会想让我轻易忘记她。
“你骗我……”
萱毫无掩饰地笑了,和清很像。
“你呀,又不是小孩子了,这种事还是别问我的好。”
“她说过会记得我……你记得吗?”
她停止微笑,转过头:“我……忘了……”
“真的吗?”
“嗯……我忘记了……”她不安地离开我身边,奔跑向远处。
她还不知道……自己就是清……病死了的不是清而是萱……
清视萱如己身,萱死去的那天,她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一言一行都和萱分毫不差……我知道她太爱萱了,她受不了妹妹的离开,就这样,一人扮着两种角色。
“岚,快过来。”她蹲在花丛里,指着地面,“我把你给清的巧克力埋在这儿了……”
“白痴……”
她又那样笑了,美丽,妖异,只绽放给我的笑。
我深吸一口气,伸了伸懒腰,今天阳光很好……
“清,我们结婚吧……”
她愣了,蹲在那里半天不说话。
“默认啦?”
她一下子扑进我怀里,放声大哭,像是个受了天大委屈的孩子,不停地拍打着我的胸。
“明年……我们去看萱……好吗……”
清没有说话,默默地点了点头。
今宵别梦寒 ◎文/徐筱雅
周先生搬进来的时候是个中午,那个时候梅子刚放课。前些天,房东连太太就开始忙活了,说家里有人要来。几个搬运工抬着几个木头箱子呼哧呼哧地从院门外进来,连太太在院子里叉着腰,指挥这指挥那,让搬运工们轻拿轻放。连太太的厨娘宋妈在做菜的时候跟母亲叨叨,说是连太太的侄子要来。梅子想起学校隔壁的中学里,男学生们穿着精神的制服,看起来风度翩翩。她想象着连太太侄子的样子,觉得他一定也是那样的。
周先生站在大院的门口徘徊着,脸上的表情扭在了一处。他的手里拿着一张便条纸,他伸着脖子朝里看,又把脑袋缩回来,看看手上的便条。那一定是地址,梅子想。梅子攥紧了书包带,然后就要往院子里走。他看见梅子,便一把拽住她的袖子。
“小姑娘,你等一等。”他说。
梅子看了看他拽住自己的手,撅起了嘴。他立刻反应过来,赶快抽回了手。他的表情有些不自然。他被梅子注视得有些不好意思,低下了头去。梅子弯下腰,然后把头凑到他低下来的脑袋上,问:“你要干吗?”
他的脸好像红了一红。他看见梅子,又赶紧把头抬起来。梅子觉得他有点手忙脚乱。他满口袋里找着什么东西,梅子觉得他是要找手上的那张纸。果然,他翻了半天,发现纸条被紧紧握在自己手里。他赶紧拿了那张纸条给梅子看:“这地址写的是这个院子吗?”
梅子点点头。她看到上面写的屋子,正是房东连太太的屋子,于是问他:“噢,你就是连太太家里人呀?”
他愣了一下,赶紧说:“嗯,她……是我姑妈。”
梅子点点头,给他一指,说:“那间,东边的那间就是。”
他冲梅子点头笑了笑,提着行李进去了。梅子觉得挺奇怪,他的手里就提着一个学生模样的黑手提袋。梅子的小学校附近就有一所中学,那里的男孩子都拿着类似的手提袋。梅子把书包带攥紧了,往院子里一跳一跳地进去了。
下午的时候天气变了。天空里盖着一层浓重的阴霾,风吹过来,也没有吹散。天一下子黑了,怎么吹也亮不起来。梅子的妈妈赵太太推开窗子,看了看天,把脑袋缩回来,对梅子说:“梅子,去把衣服收回来。要下雨的。”
梅子在里屋练大字,头也没抬:“您手又没占着,您不会自己收去?”
赵太太说:“小姑奶奶,你越来越不让人省心了。”说罢便走了出去。
院子里闹哄哄的,梅子一下子就听出了连太太尖厉的声音。她抬起窗户去看,几个搬运工人抬着一个巨大的木头箱子从门外进来。连太太在屋外尖声尖气地指挥。母亲见状,凑了过去,跟连太太招呼。不知道母亲和连太太说了什么,连太太尖厉地笑着,笑容堆了一脸,梅子觉得,她脸上的褶子一定都挤在了一起。连太太冲着屋里招呼了一声,有个人从屋子里走出来。就是刚才在门口她遇到的那个人。梅子把脑袋探了出去,想看看仔细。那个人显得有点怯,说话打着结巴,像是班里来的新同学。上半年里班上从济南来了个男同学,长得结结实实,人却羞答答的。老师让他在同学们面前作自我介绍,他半天了才从老师背后走出来。人还没说话,脸倒是羞红了一大片。母亲和那人说着话,不知道说的什么,母亲笑成了一朵花。
母亲说完了,从屋外抱着衣服走了进来。梅子听见了声音,立刻把窗子关上,接着练大字。母亲走进来,把衣服放在床上,一边叠着衣服一边说:“梅子,你多和人家周先生学着点儿。人家周先生学识好,你跟他多学点儿没坏处。”
梅子瞥了母亲一眼,说:“您不就想巴结连太太她们家吗?您还不识字儿呢,您怎么不跟周先生学去?”
母亲用眼睛使劲儿剜了梅子一眼,说:“我不跟你置气。我就巴结了,您怎么着吧。”她说着,继续叠衣服。架在炉子上的水突突地响了,她走过去提起来,走到屋外去了。
大院里一共三家人。连太太,赵家母女,还有一家做买卖的。整个院子都是连太太的,母亲说连太太当初给一个什么大官做妾,这是给连太太买的外宅。后来大官死了,外宅也就留给连太太了。连太太带着厨娘宋妈住着,现在又多了一个周先生。她一个人用不上这么些间房,于是把房都租了出去。北屋住的那家买卖人,男人长年累月地不在家,就是一个女人带着三个老姑娘。北屋的人家和其他人不太来往,三个老姑娘盼着嫁人,盼久了吧,脾气也就不好了,仨人成天闹架。老妈子腿脚不灵便,声音也不及她们响,根本就管不住。连太太也琢磨着到期了就把房子收回来,成天这么吵,听着就闹心。
宋妈跟着连太太很长时间了,年纪一大把了,是个寡妇。她唯一的乐趣就是跟母亲说别人家的长短。从连太太以前的私房事说到北屋的三个老姑娘,胡同里只要是认识的,就没有不被她说过的。梅子不喜欢她,觉得她满嘴里跑舌头,一天到晚胡吣。除了这点之外,她倒是个称职的厨娘。她做的菜,肯定要比得上胡同口的那家大馆子,梅子这么想。
梅子没有进过馆子,但是连太太常常从馆子里带来一些点心,悄悄塞给梅子。
“我妈说了,不要拿别人的东西。”梅子对连太太说。
连太太把点心塞到梅子怀里,说:“这又不是你拿的,这是连太太给的。”
梅子很想尝尝那个点心的味道。虽然心里挺不舍得,但她还是把点心匣子递还给连太太,她怕妈妈说她。妈妈总是要拿爸爸说事。她总是一边哭一边说:“你为什么就是不听我的话呢?要是你爸爸在,你也这样?”她一边哭一边用力地喘气,一抽一抽的,让梅子觉得上不来气。她真怕妈妈也像自己一样。
梅子对连太太说:“别人给的也不许拿。”
连太太有些不高兴了,说:“你这小孩怎么就不开窍呢?那这么着,你现在吃了,就不算我给的了。”
梅子想了想,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她抬起头来看了看连太太,连太太冲她笑了。她的笑容真好看,就像太阳底下照着的桃花。
妈妈撇撇嘴,说:“笑得跟个狐狸一样,有什么好看的。年纪轻轻的做什么不好,偏要去给人做姨太太!”
宋妈做的小点心,就跟连太太给梅子吃的那些点心,差不多一个味道。有时候宋妈到家里来,顺带着给梅子带几块小点心,这个时候的宋妈特别招人喜欢。
周先生来了好些天,梅子也没看他出来过。梅子觉得挺奇怪,人老跟屋子里待着,不是要得病的吗?
宋妈和母亲买菜去了。梅子一边练着大字,一边想着周先生的事儿,想着想着心里就乱了,再也练不下去了。她把窗子抬了起来,朝连太太的屋子看了看。周先生的影子好像晃了过去。可是等了好一会儿,也没见周先生再从门前走过去。梅子把窗子放下,从家里跑了出去。
梅子走到院子里,探了个脑袋往连太太屋子里看。屋子里静静的,好像没人在。怎么会没人呢,刚才明明看见周先生往这儿过去的呀。梅子几乎要把身子探进去了,还是没看到人。她突然想到这有些不礼貌,母亲是最讨厌自己这样的。
回去吧。梅子一边想一边转过身子。可是她觉得有点不甘心,于是转过身来,又往屋子里瞄了一眼。周先生正站在那里,微微笑着看着她。
梅子吓了一跳,赶紧低下了头。
周先生说:“梅子,你怎么不进来呢?”
梅子低着头说:“妈妈说了,别人没请,不能到别人家里去,这样没规矩。”
周先生呵呵地笑出声来,说:“那我现在邀请你,好不好?”
梅子抬起头来看看周先生。他向她伸出一只手。他的上嘴唇和鼻子之间有一块很深很深的凹处,算命的涂瞎子说了,这样的人有善心。涂瞎子算命算得可准了,妈妈开始不信,后来带着梅子去了。涂瞎子眯缝着眼睛,抱着个拐棍,捏着手算了一下,就把家里的变故全算出来了。梅子在一旁听着,都愣了神了。妈妈听着涂瞎子的话,刷刷地掉眼泪。
他的脸怎么这么白呢,都快赶上自己写大字用的纸了。周先生站在那里,向自己伸出一只手,点点头:“赵小姐,我请你到家里来坐坐,不知道方便吗?”
梅子扑哧笑了,把小手搭在周先生的大手里。周先生的手真凉,像是冰糕一样。他的手怎么这么凉呢?一定是他不常出来的缘故。人哪能总在屋子里待着,这总是要得病的。就像花儿不见太阳,就要蔫儿了。这是一个道理。
梅子到周先生那儿去了几回,觉得他的脑子就像是一本厚厚的书,里面什么知识都有。她乐意跟周先生待在一块儿,觉得听他说话特别长知识。反正母亲让她多跟周先生学着点,现在她也乐意。
可是,周先生刚来了两星期,赵太太的态度就突然变了,不让梅子去找周先生了。梅子问她为什么,她也不细说。
连太太不在家的时候,周先生就一个人坐在堂屋里。堂屋里摆着一个巨大的木头箱子。每当周先生往前面一坐,里面就会传来叮叮当当的声音。学校的礼堂里也有一个跟这个长得差不多的大箱子,年轻的音乐老师坐到箱子前面,于是悦耳的声音就响起来了。
梅子在屋外站着,不敢进去。赵太太总是跟她说,别老瞅着房东太太家里来的那个人,他不是什么好人。好人坏人也没写在脸上,怎么妈妈一眼就看了出来?她不觉得他是坏人。以前涂瞎子说的,上嘴唇和鼻子之间有一块凹进去的地方,凹进去的越多,这个人的心越善。他的嘴唇上面凹进去了好大的一块,一定是个善心人。他还常常教自己功课,告诉她许多道理。这样的善心人怎么会是坏人呢。梅子想。
赵太太不在,和邻里的宋妈出去了。梅子不喜欢宋妈,她顶着一个古怪的头,用头油把头发弄得油亮油亮的。她眼睛小小的,但是亮得有些出奇,一把年纪了,却最爱用香胰子。她一走进来,梅子就闻到她身上的胰子味道。可是她还有狐臭,每次梅子遇到她的时候,总感觉那一股混杂着胰子香味的臭味冲着自己的鼻子直奔而来,让她觉得直反胃。宋妈老在赵太太耳边嘀嘀咕咕,眼睛滴溜溜地直转。
“我听说那个周先生根本不是连太太的侄子,是她在外头找的相好。”宋妈说。
赵太太一听,眉头立刻皱了起来,说:“年纪轻轻的,做什么不是谋生活,非得让人养着,女人也就算了,一个大男人……家里的颜面都被他丢光了。”
宋妈这时候给赵太太使了个眼色。赵太太抬起头,一眼就看见在门外站着的梅子,立刻轰她走:“大人说话,哪有小孩子听的份。去去去,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梅子没弄明白她们俩说的什么,她知道宋妈一定没给母亲说什么好话。宋妈走了以后,母亲把她叫到跟前,说:“以后你少和那个周先生来往,听见没有?”
梅子说:“为什么呀?您当初不是说他学识好,让我跟他多学着点。”
赵太太一撇嘴,说:“学识好有什么用,还不是……”说到这里,她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说:“小人家哪里有这么多为什么?去去去。”
周先生在屋子里坐在一个大木箱子前面。这个大木箱子在他搬进来的那天下午就送来了。连太太站在屋子的门口,叉着腰,样子很紧张:“喔哟,轻一点轻一点的,这东西好贵的,弄坏了你们赔得起?这边这边,轻一点放。”从那天起,院子里就常常传来叮叮叮悦耳的声音。梅子想起来,她透过街角商店的玻璃橱窗,看到一个小小的盒子,那里面站着一个跳舞的女娃娃。她一跳起舞来,盒子里就传来这样的叮叮声。
他一定会变戏法,不然,为什么他只要把手放在那个木箱子上面,就会响起好听的叮叮声呢?梅子在这样的声音里看到小溪,它从山涧里流出来,在石头上撞击出悦耳的声响。她看到小鸟,看到树林里的小溪流。
他肯定会变戏法。梅子想。她想进去问一问周先生,究竟那些声音是从哪里飘出来的。赵太太的话还在她耳边飘着,这使她有点犹豫。周先生看到梅子,向她招着手说:“梅子,来。”
梅子用手扶着门框站着,向院子里看了看,没人。她跑到院子门口,往胡同两头都瞧了瞧,也没人。宋妈和母亲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回来。应该不要紧的,周先生是好人。梅子想着,一蹦一跳地进了连太太的屋子。
周先生拍拍凳子,示意梅子坐下,自己也往椅子边上挪了挪。梅子坐下来,第一次看清了这个大木头箱子。箱子上面一黑一白的方块儿并排着,她真想伸手过去摸一摸。可是她想起连太太当时紧张的表情,又把手缩了回去。周先生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抓住梅子的手,把它放到琴键上。“叮”的一声,木箱子就响了。梅子挺惊讶,觉得又惊又喜。她转过头去看周先生,周先生冲她笑了一笑。
周先生说:“梅子,喜欢吗?”
梅子点点头,说:“周先生,这是什么?”
周先生说:“这是钢琴。这个叫琴键。梅子,我教你唱歌,好吗?”
梅子连忙着点头。周先生把手按在那些黑白的琴键上,于是就有一连串悠扬的音符从钢琴里飘了出来。周先生的手细细长长的,像是戏园子里戏子的手。他的手在黑白的琴键上来回地游走,接着就开始唱:
长亭外,
古道边,
芳草碧连天……
梅子想起来了。每年小学校里欢送毕业生的时候,低年级的代表都要上去唱这首歌。梅子不太明白歌里唱的究竟是个什么意思,但是,一听歌的名字,她就觉得让人挺难过的。《送别》。是送行的时候才会唱的歌。说了再见以后,人们还会再相见吗?梅子常常这么想。
梅子听着,抬起头来,一眼看见宋妈和母亲有说有笑地从门外进来。她想起母亲的话,赶紧站起来往门外跑。周先生站起来,叫:“梅子!”梅子也没来得及回头看一眼,直往院子里奔去了。
她快要跑到家门口的时候,被母亲一眼看见了。赵太太把手里的东西往地上一放,指着梅子的脑袋就骂开了:“跟你说了多少回了,让你少去招惹那个什么周先生,你不听,你就是不听!”
宋妈在一旁帮腔道:“赵小姐,您瞅瞅赵太太多不容易。我们这都是为您好。”
梅子鼓起眼睛看了宋妈一眼,一句话也没说,直接往屋里奔去。
梅子惦记着周先生那首没唱完的歌。母亲和宋妈一出去,她又往周先生那儿跑了。周先生的声音听起来暖洋洋的,就像是大雪初晴透出来的一缕温暖的阳光。
周先生平常里不太说话,对人很客气。但是梅子一来,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他告诉梅子家里还有几个跟梅子年纪相仿的弟妹,他多年在外读书,没有回去过。他说,他看到梅子就想起自己的妹妹。梅子听了,心里暖融融的。
梅子不知道宋妈又和母亲说了什么,但是她知道,宋妈嘴里就没过好话。午后宋妈把母亲拽到一边儿去了,嘀嘀咕咕说个没完。梅子坐在连太太的屋子里,坐在周先生的旁边,清楚地看见宋妈那根又粗又短的手指不断地向自己的方向指过来。母亲的表情随着宋妈的话而不断变化着,最后,恶狠狠地瞪了梅子一眼。梅子看着母亲的目光,心里凉飕飕的,顿时感觉一股凉气顺着脊梁骨蹿了上来,让她感觉脑门子发凉。她看见母亲的嘴上下翻动着,不知道她是不是想要对自己说些什么。梅子觉得有点害怕,往周先生身上靠了靠。
周先生转过头来说:“梅子,你怎么啦?”
梅子还没来得及回答,就看见母亲怒气冲冲地推了门进来。周先生看到她,立刻站起来打招呼:“赵太太。”
母亲瞪了梅子一眼,一把把她拽到自己身边,语气很不客气:“周先生,我家姑娘还小得很,请你不要招惹她。”
梅子听了,羞得不行,赶紧拽了拽母亲的衣服,低低地喊了一句:“妈!”
母亲一把甩开梅子的手,瞪了梅子一眼。周先生的表情有些慌乱。他的大眼睛此时看起来显得更大了,空洞洞的,表情像是一个无助的孩子。母亲接着说道:“周先生,梅子不懂事整天缠着你,是我没教好。您是有学识的人,您知道。”
周先生的表情很难堪,他咬着下嘴唇,脸色像一个重病的人。前年西屋里的孙老太太过世了,人们把她从屋里抬出去的时候,她的脸也是这么一个颜色,比梅子练习写大字的纸还要惨白。周先生说:“赵太太,您是不是听了些什么,对我有些误会?梅子来这儿只是学学琴而已……”
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母亲的咄咄逼人给打断了:“周先生,小孩子家的不懂事,跟着您,她心都玩儿散了。我们孤儿寡母的不容易,将来我还指望着她呢。您配合配合我,让小妮子收收心。”
周先生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梅子觉得他的眼睛里亮闪闪的,像是夏天胡同里被阳光照射着的玻璃碴子,发出破碎的光芒。他的额角湿了,有几滴汗顺着脸流下来,衬着他苍白的脸,让梅子觉得有些冷。看着周先生的模样,梅子快要哭了。她觉得自己对不起周先生。
周先生冲母亲笑了笑,笑得挺僵硬。他说:“赵太太,我明白您的意思。我配合您。”
母亲回给周先生一个轻蔑的笑容,用力捏住了梅子的手,说:“我这儿谢谢您了,周先生。走。”说罢,她使劲儿拽着梅子往外走。梅子回过头来看周先生,这个时候他一个人站在钢琴旁边,手搭在琴键上。周先生冲她挤出了一个笑容,说:“梅子,再见。”梅子觉得鼻子酸酸的,有什么东西一直冲着鼻子蹿上来。母亲拽着她的手像是一只巨大的钳子,把她的手夹得紧紧的,一刻也不放松。
回到家里,母亲嘭的一声把门关上。关门声震得梅子吓了一跳。母亲也不管还在屋里待着的宋妈,伸过手来指着梅子的额头,说:“姑奶奶,你让我给你跪下啊?你可是不知道,外面都把咱家说成什么样子了。人言可畏,人言可畏,你不要脸,我还得在胡同里做人呢!”
梅子不说话,眼睛鼓鼓地看着母亲。母亲白了梅子一眼,说:“你瞪什么眼啊?我告诉你,以后不许你到连太太家里去。你要是再往那儿去,留心我打折你的腿!”
宋妈上来劝母亲。梅子觉得她的表情有些幸灾乐祸。母亲为什么宁愿相信宋妈的话,也不愿意相信满腹学识的周先生呢?宋妈把母亲拽了过去,两人又低低地嘀咕开了。她们俩的声音嗡嗡地响着,像两只苍蝇。一只苍蝇嗡嗡地飞过来,直奔着梅子的脑袋钻了过来。嗡嗡,嗡嗡嗡。梅子觉得自己的脑子乱成了一片,就跟豆腐脑似的,被苍蝇这么一撞,全都散了。她觉得自己脑袋里传来了一声长响,像是烧开的水壶一样吱吱地叫了。她眼前一黑,向前倒了下去。
醒来的时候,梅子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屋里的炉子上坐着一个小水壶,水要开了,突突直响。宋妈和母亲还在外面说着。梅子掀了被子从床上下来,用抹布包住水壶柄,把水壶从炉子上拿下来,放在桌上。她走到门前,听到母亲在外头向宋妈哭啼着诉苦:“这孩子一点儿不叫我省心!您瞅瞅,我省吃俭用把她拉扯大,我容易吗我?她倒好,本事不大脾气还不小!”
宋妈说:“这孩子也是,都这么大了,还一点儿也不懂事。都是为她好的。”
母亲说:“您说说我这是图的什么?我上辈子造孽,这辈子就弄了这么一个冤家!”
宋妈说:“赵太太,您也别太着急了。以后多看着点她就成。那个周先生不是什么好人,哎哟,他和连太太的那些事,我都不好意思说。”
梅子觉得宋妈真讨厌,成天在背后说别人长短。有本事到人家跟前说去呀。梅子想。她厌恶地从门口折回来。梅子坐到床上,轻轻推开窗。通过这扇窗子,梅子正好能看见连太太家里的厅。厅里摆着钢琴,周先生还坐在那里。他的脸上似乎没什么表情,细细长长的手指很机械地在琴键上滚动,像个木偶。他停了下来,站起身,合上了琴盖。那个木盒子紧紧地合上了。梅子觉得,有一扇门随着琴盖也关上了,光明被隔在了门外。
做饭的时候宋妈又来了。她向梅子走过来,讨好似的说:“哎哟,瞧瞧我们赵小姐,模样一天比一天俊啦。”
“事儿妈。”梅子小声嘀咕,宋妈没听见。梅子白了宋妈一眼,带着毽子自个儿出去了。宋妈显然感到不满意,啐了一口,骂道:“德行!”骂完了径直走进了赵太太的屋。
梅子拿着毽子走到门口,又折了回来。宋妈每次来都要说周先生的不是,这回不是又来编排他的吧?她想着,又悄悄地倚回到门口,想听听她和母亲说些什么。
“赵太太”,宋妈说,“你可得留心着点儿。咱这个院子里遭贼。”
母亲显然没在意,说:“宋妈,我们家您又不是不知道,没什么值钱东西。那贼子要是看上我们家了,那可是不运气。”
宋妈撇撇嘴,说:“哎哟,话可不能这么说。小心点儿总是好的。”她说着,靠近母亲耳边,说,“我跟您实话说了吧,我去打听了,院子里这几家都没丢东西的。就我们家。”
母亲会意了,说:“您的意思是……”
宋妈意味深长地点点头。
梅子一听,知道宋妈没有说下去的,还有母亲已经会意的那些话究竟是什么了。她果然是来编排周先生的!梅子这么想着,觉得很生气。哪儿有这么样的人,不说话别人也没把她当了哑巴的,她怎么还整天吊着个舌头满处跑?梅子越想越生气,她决定去告诉周先生,让周先生来训训这事儿妈。
梅子想着,着急地往连太太的屋子里跑,可没成想,嘭地一下撞上个人,那人手里的包袱叮叮当当地撒了一地。梅子连忙抬起头来看,是周先生。她的脸刷地红了,赶紧说:“周先生,对不起。”接着弯下腰去捡。
周先生看起来很慌张。他的额头上沁出了细细密密的汗珠。他的手有些抖,捡起来的首饰又掉地上了。梅子手脚麻利地帮着周先生捡,一边捡一边问道:“周先生,你这是要干什么去呀?”
“我……对了,我姐姐要出门子,我给她寄点首饰过去。”周先生回答说。
“是要做新娘子啦。新娘子可漂亮啦。前些日子里胡同尾的苏家小姐做了新娘子了,胡同里可热闹了……”
周先生把掉在地上的首饰一把抓了包在包裹里,慌张地打断了梅子的话,说:“梅子乖啊,我今天忙着,回来再教你唱歌,好吗?”
梅子觉得周先生有什么话藏着没说。她不知道该怎么问,只好点点头。等周先生出了门,她才想起来,宋妈那一状她还没告诉他呢。
一清早的时候,梅子就听见院子里闹哄哄的声音。梅子推开窗子去看,发现院子里的女人们都堆在了一处,当中自然少不了宋妈和母亲。连太太站在院子中央,双手叉着腰,嘴里骂骂咧咧,听不太清楚。周先生低着脑袋跪在一边。女人们把脑袋凑在一起,用手对着他指指点点。梅子心里沉了一下,赶紧穿了衣服从床上跳起来,跑到院子里去。
连太太一边指着周先生一边骂:“日防夜防,家贼难防!我说家里怎么东西见少呢,就按着你这个偷法,我有多少家产也得给你拿光了!要不是赵太太……”连太太说着,一时气不过,把放在地上的包裹捡起来,猛地往周先生头上砸过去。包裹松开了,里面包着的细软全部落到了地上,发出叮叮的声音。
“哎哟……”院子里的女人们看了,不由得发出一声叹。
梅子从那群女人当中挤到前面去,一地的细软在阳光的照射下直晃人眼睛,那亮光像是把筷子放进了杯子里一搬,折了一截。太阳照在周先生的脸上,他的脸在太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更惨白。周先生的表情显得很轻松,像是把一个很沉的包袱给放下了。
连太太接着喊,那声音,仿佛要全院子的人都知道:“要不是人赵家太太来告诉我,我还逮不着你!你说,你到底往外搬了多少东西?你说!不说是吧,不说?好,好好,待会儿警署的人来了,有你受的!”
警署里来了人了。院子里又一片欷歔声。连太太怒气冲冲地对巡警说着话。巡警们把周先生绑了,架起来往外走。周先生回头看看梅子,说:“梅子,再见。”
女人们听到周先生这么一说,把目光都集中在了梅子身上。她们意味深长地看着梅子,指指点点的。赵太太没想到有这么一出,使劲儿拽了一把梅子,示意她快回家。
“听说是连太太不给他钱,他才做的贼。”
“年纪轻轻的,做什么不好。唉……”
“我听说他家里有六个妹妹,他是老大,父亲死了,母亲又是病摊子……”
“穷也要穷得有骨气,您说是吧?”
“……”
院子里的女人们唧唧喳喳地议论着,仿佛什么都知道。梅子的脑袋里乱哄哄的,她跑过去,冲着那群女人大吼了一声:“周先生是好人!”
赵太太一听见梅子的声音,顿时一脸的尴尬。她一边拽着梅子往屋里走,一边给屋外的女人赔着笑脸。梅子想要挣脱她,却觉得母亲的力量前所未有的大。她喊着:“周先生是好人……”赵太太赶紧在她胳膊上狠狠扭了一把,硬是把她拽回了屋。
屋外的女人们说:“多可怜的,还是个孩子……”
“就听说那个姓周的小子没被警署带走以前,赵太太的小妮子跟他走得特别近……”
“您瞅瞅,我当初说什么来着。小姑娘一生都毁喽……”
赵太太嘭地一下把门给摔上了。门外的女人的话仍然嗡嗡地从门缝里传进来。赵太太数落着梅子,梅子看着她的嘴张张合合,却也不知道她在说的是什么。她委屈地小声说:“周先生是好人……”她不知道母亲听见没有。母亲仍然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显然,她没听见。
梅子想起周先生教她的《送别》,觉得那好像是周先生给她留的话:
天之涯,
地之角,
知交半零落。
一瓢浊酒尽余欢,
今宵别梦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