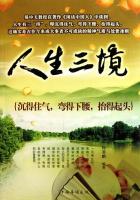热爱旅行的生活,没有缘由,如果一定要问个为什么,我们一定是在追寻着梦境中那个属于自己的香格里拉。
时光也打不败爱情
2011年的深秋,天气已经略显寒冷,我与芝麻拖着薏米前往陕西的一个小县城,去见一位已十多年没有见面,且此间毫无音信却突然得到消息的挚友。我与这位挚友,应当算是多年的难兄难弟,从刚相识那阵到今天,已快二十年,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那时的我与这位哥们儿都还是十几岁的毛头小伙儿,那几年两人几乎天天厮混在一起,读书喝酒胡吹下象棋。后来因为都有了新的前程,各奔东西,再后来因为生计奔波忙碌,联系渐少以至音信杳无。他就是老陕。
老陕,陕西人,那会儿这家伙总喜欢充老,动辄憋着嗓子用陕西话来一句“我说你个小朋友”之类,我索性不呼其真名,一直就老陕老陕地喊过来了。那会儿还是20世纪的90年代初期,我与老陕同在新疆的某个小城当兵,两人都在这个部队的机关,不同的是我管文件档案,老陕管放电影、放集合起床号。两人办公室兼宿舍门靠门,真是那种放个屁都能相互听见的空间和距离,我们住的那栋机关大楼中间高,两边低,中间有五层,而两边只有四层,大楼门口日夜都有两名哨兵执勤,进出都非常麻烦,于是两边的四楼楼顶就成了我们二人的自留地。房子里没空调,加上是顶楼,在夏日被晒一整天后十分闷热,根本无法待。北方的夜晚倒是凉爽,于是两人经常借着夜色掩护,卷着被子从窗口跳出去到楼顶睡觉。我很是怀念那些年的夏天,与老陕一起伴着舒缓的乐曲(录音机放的那种磁带版的《梁祝》之类),数着天上的星星,举着啤酒瓶海饮。老陕一向故意把啤酒称为“牌酒”,夏夜喝“牌酒”几乎成了两人每天必修的功课。酒至半酣,天南地北不着边际瞎吹,当然偶尔也默不做声,听风从远处捎带过来的声音,间或还隐约可听到都市传来的欢声笑语。大多数时候,两人都在有一搭没一搭的神聊中召见周公,偶尔也有半夜三更突然刮起风下起雨的时候,两人或在睡梦中顶着被子往屋子里窜,或因酒精作用产生的英雄气概,干脆临危不惧视死如归,裹紧被子继续大睡。
最开始这四楼的楼顶就我与老陕两个独享,“不幸”消息泄露,成员不断增多,最多时有七八个人加入这个行列,当然这人一多,话题也开始五花八门光怪陆离,也更有了夜半磨牙放屁说梦话甚至从楼顶往下撒尿的不雅行为。那会儿这堆人最高兴的事,莫过于有机会顺着白水河一直走,去看那些巨大的柳树、挺拔的白杨,去老乡的果园里看杏花红、梨花白,或者趁着野外驻训、演习的机会,在荒野里没有目的地游荡,在戈壁滩上挖跳鼠,在沙漠里看枯死的胡杨,无数次凝望天山上亘古的冰川,在塔里木的湖泊中看那成群的野鸭大雁天鹅。年轻时,所有的梦想都是自由的,所有的梦想都是快乐的,因为大家都渴望在路上。老陕曾扬言要写一篇《睡在四楼楼顶的兄弟》,只是至今也没有人看到他的大作。
老陕个子高大,为人爽直,只是他每次憋着嗓门儿的陕西腔“我说”,总被我听成“饿说”,于是没等他说完就回他一句“你吃饱再说吧”。那会儿年轻饭量大,老陕养成一特大“恶习”,很多次打饭时,趁食堂的人不注意,竟然用他那脸盆大的碗直接伸进饭盆里,挖泥似的掏一碗就走。当然有时候也会趁人没注意,飞快从菜盆子里夹上一块早瞄准的肉扔进嘴里,这让我很是难过,因为那手说不定刚擤过鼻涕抹过鞋底。
那时部队有严格的规定:禁止在当地找对象。我牢牢记住了这个规定,因为我想当个好兵。但那个年代文学青年是比较流行的,我有着当“文学家”的梦想,加上那个年代电话稀缺,没有电脑没有手机,闲得无聊,成为文学青年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我总是幻想着仗剑走天涯,或如徐霞客一般周游天下,或如李白那样浪迹四海。某张与文学沾边的小报,是我当年经常光顾的地盘,通过书信,我认识了一位出生在湖南、求学在成都,同样也做着文学梦的女孩,两人书信往来,从文学聊到人生、理想,相互诉说各自的生活,分享彼此的快乐,倾诉彼此的忧伤。书信使两人的日子简单而快乐,就这样,芝麻成了我的笔友,交笔友在那个年代很流行,亦如现在的网友。
老陕也是个好兵,但老陕唯一没有记住的,就是那条不能在驻地找对象的规定,他经常夜半三更翻墙而出,去会新认识的女朋友。老陕的女朋友叫燕子,我对老陕的口才佩服得如滔滔黄河之水连绵不绝,因为燕子就是他用传说中的三寸不烂之舌忽悠来的。我曾与老陕一起去逛书店,回部队的路上,老陕突发神经言语道,离开书店时,那个卖音像制品的女孩子曾冲他一笑,一定有戏。我便开始损他“四处撒网,重点培养”。结果第二次去,老陕还真与那女孩聊得挺热乎,我凑过去一听,老陕说听听那盒磁带,女孩就放来听;老陕又油嘴滑舌地说好香,这磁带是加香的吗,引得女孩笑得花枝乱颤,从此这两人算是熟人了。后来有个地方单位搞文艺汇演,送来些喊人去凑数的票,有人给我两张,我给了老陕一张,结果老陕死活要我为朋友两肋插刀把票全给他,还要我担任什么爱情大使,到书店给女孩送票。我最怕和女孩子打交道,就问老陕自己为什么不去,老陕答刚从书店出来,不好意思再进去。斟酌半天,最后商定由他到图书馆偷八本书给我(老陕还兼管图书馆),成交。后来我真去了,只是转了一圈,愣没敢把票给人家。老陕在书店对面眼巴巴地等,结果我出来说燕子不在,老陕气急败坏地说刚才都在,我答不信你自己去看呀,可老陕又不敢进去。
后来老陕居然对芝麻说燕子是他撞电线杆撞的,让芝麻很是为我惋惜了一阵,我自己也非常惋惜,因为老陕替我偷八本书的诺言到今天也没兑现。
后来燕子与老陕终于跳进了热恋的大坑,过着紧张而刺激的生活。只是老陕因为经常夜半出去约会耽误瞌睡,以至某天中午睡过头了,到下午4点迷迷糊糊起来放午休起床号,结果领导将他痛批了一顿,并责令他写出5000字的检讨。老陕也经常在星期二、星期五晚上放电影时因为想着约会,把一部电影放得颠三倒四(老胶片电影,有很多卷那种),让第一次欣赏的人看不出前因后果,有时看到人明明死了,放到后面居然还在战斗;让看过几次的人老是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云里雾里,搞不清哪一次看的是正版。
而我与芝麻随着书信的联络,越来越依恋彼此,也很期待见面。
此时的老陕与燕子如影随形,早已顾不上和我共享四楼的星星与月亮了。
数年后,老陕转业留在了那座西北小城,进了公安部门。燕子也公开了与老陕的关系(但还瞒着家里,因为燕子家是信某个教派的民族,不与汉族通婚),两人偷偷租了属于自己的房子,自己买菜,自己做饭,俨然老夫老妻。我与一些玩得好的战友经常借着各种由头去老陕那里改善生活。燕子与老陕过得幸福而甜蜜,阳光已经出现在他们眼前。
我也在那时考上了大学,暂别了那座小城。只是那时的芝麻因毕业实习,已经离开成都去了湖南的一个小城,两人依然书信往来不断,只是见面仍遥遥无期。再后来,芝麻毕业了,分回了湖南老家的小城;而我也即将从学校毕业,大家都面临着新的抉择。那年夏天,我只身一人,在路上折腾了一个星期去了湖南,与从未谋面的芝麻相会。出发前,很多人劝我,但我不为所动,我坚信芝麻也一定这样执著。从一开始,我们俩的爱情就不被周围的人看好,不管是我周围的人,还是芝麻周围的人,都认为我们不过是年少无知,逢场作戏,尝过爱情的滋味后,最终会劳燕分飞。那年夏天,虽然我们还是第一次见面,却已经在内心把对方视作了自己的亲人,而不仅仅是朋友或恋人,因为在书信里我们已熟识多年。
从见面那一天起,铺天盖地的劝导接踵而来,然而所有的苦口婆心或冷嘲热讽,我们都只当做耳边风。因为在我们看来,只要有梦想,天空就能升起幸福的云朵。
再后来,我被分配去了喀什,一个更遥远更陌生的城市,两人在空间上的距离越来越远,但心越来越近。在到达那座城市不久我就以自己的能力与才华被周围的人认可,前途一片光明,但我一直为情所困,不知该何去何从。芝麻家里也已经知道我俩的事,自然是反对她跟着我走。芝麻是个孝顺女儿,不忍伤家人的心,但她也是个坚韧无比的人,不愿放弃自己的爱,对周围所有的鲜花与笑脸、压力与劝说一律视而不见,只是对未来,我们都有些茫然。
那段日子,我经常与一同分配去的同学借酒浇愁,每天靠和芝麻来往的书信与文字活着。那些发呆时随手写下的文字,零零散散,居然汇集成了一本专属于她的文字,我取了个名字叫“无题的恋歌”。在最前面有一段这样的题记:爱人,为了爱你,我情愿与你在爱的栈道上被风雨磨砺成岁月的雕像。虽然我把心砌成路,可仍然怕它硌伤你的脚。我把这些文字打印并装订起来,在封面上写下了一段话,鼓励自己,也算是鼓励芝麻:不要以别人的眼光去审视爱;不要以别人的标准去衡量爱;不要以别人的观点去验证爱;不要以别人的模式去寻找爱;不要因别人的艳羡而追求爱;不要因别人的非议而逃避爱。请记住: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从喀什的花开到花落,我一直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要么留在喀什,好好工作,在仕途上一帆风顺,放弃深爱的恋人,把痛苦留在心底,直到遗忘,然后选择一个新的女友,结婚、生子,教育孩子成长;要么放弃所有的一切,到湖南去,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除了芝麻,一无所有。
夏天即将结束,我终于不顾一切,坐了一天一夜的长途汽车,去见老陕,要这位难兄难弟帮我拿个主意,虽然我早已知道自己的选择。去见老陕,无非也是给自己一个理由和借口。几年不见,老陕已在公安部门混了个要职,那个年代刚流行的BP机与大哥大,已经晃眼地挂在了他的腰间。
我与老陕连喝了两天的酒,直喝得云里雾里。酒醒之后,我坐上了返回喀什的车,中途又去了克州,见了一个朋友,无所事事待了两天,散了两天心。或许是厌倦了漂泊,我坚定信念:宁愿在爱情的道路上去寻找事业,也决不为了所谓的事业放弃爱情。那年夏天,我带着最珍爱的东西(她写给我的100多封信),放弃了工作、档案,抛弃了行李、书籍,离开了喀什,离开了新疆,去了湖南一个小城。在新疆到湖南的路上,刚好看到一篇纪念探险家余纯顺的文章《英雄永远在路上》,那时我突然觉得,这或许就是自己想要的生活。自己不是英雄,但或许是行者,也可以一直在路上,只是自己不会是一个人走在路上。在我看来,只要有梦想,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或者是一家人,都可以在路上。
经过艰难的奋斗,数年后我与芝麻有了自己的小家,有了女儿,过着简单、平凡却快乐、充实的日子。但命中注定,我们都是不安分的人,从一开始就注定一直会在异乡游走漂泊,因此不断的行走,成为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至于老陕,也因为种种原因,离开了那座边陲城市,在20世纪末回到了生他养他的故乡,燕子也义无反顾地跟随老陕去了那个小城镇。那年秋天,燕子与老陕到我落脚的小城来看我们,那时我与芝麻条件很差,租了一套大约30平方米的房子,有个小厨房可以做饭,但没有独立卫生间,上厕所要跑很远,半夜起来就是苦差事,冬天更是如此。因为两人都是从农村出来的,时常还需要帮衬家里,芝麻刚参加工作不久,我尚未立足,经济上常常捉襟见肘。最艰难的一次,我们两个人身上加起来不到2块钱,而家里又刚好没油没菜,于是两人用剩下的2块钱买了一些豆腐干、一些生菜,中餐就变成了凉拌豆腐干、凉拌生菜,那应该是我们这辈子吃过的最难吃也是最好吃的菜吧。即便是在后来的户外生活中,我们也从未有过如此窘境。老陕他们只待了几天就返回陕西去了。
不久,接到老陕电话,说燕子母亲病危,燕子很心疼自己的母亲,无论如何要回去,说去看看就回来,老陕因为别的事忙着没有一起去。结果燕子一去杳无音信,老陕说很想去找她,可不知道如何能联系上她。我劝老陕亲自跑一趟,回一趟西北边陲小城,老陕回答一定会去。
不知道是我与芝麻当时的处境,让燕子对未来没有信心,还是燕子回到那座城市后遭遇变故,无法再回到秦岭深处,总之从此老陕失去了燕子的消息,我也失去了老陕的消息,只隐约知道老陕在老家找了一个农村女孩结了婚。
那座西北的小城,就这样停留在老陕的梦里,同时也停留在我与芝麻的心中,只因为我们都曾经年轻和快乐过,只因为那里有我们青春的回忆。
不知道老陕是否会看到这些文字,也不知道燕子能否看到这些文字。但我想,或许在这个平淡的故事里,我们所有人都是主角之一。
我与芝麻的生活幸福而温馨,虽然两人都是比较落伍的人,是典型的老土,不会唱那些流行歌曲,不过两人都很喜欢一首歌——《最浪漫的事》:“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我们老得哪儿也去不了,你还依然把我当成你手心里的宝……”也许对我们来说,这才是最美的开始与结束。
在平凡的生活中,我与芝麻也喜欢玩点小资,偶尔小酌,在杯光烛影里,时常会想起老陕,想起自己走过的路。在我与芝麻看来,徒有爱的热望和激情,并不能造就爱的持久和坚韧。那种没有任何标记的,以赤裸本真相对的爱,也并非是不堪一击的,虽然人永远都不可能彻底地纯粹和本真。婚姻或许只是而且只应该是爱的归属,它不是一种改变现实状况的功利出路,婚姻之绳其实非常细弱,它维系不了那么沉重的期望,它只能依靠两个人共同的心愿和努力来加固。但现在还有几个人,会去努力加固呢?
人生本身就是一段单向的旅程,在行走的路上,除了风景,更需要无边而坚韧的爱,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拥有自己的香巴拉,或远或近,或明或暗。拥有,就一定要珍惜;有机会,也一定要把握;错过,你再不会有回头的路;爱过,就不要后悔。在岁月这条道路上,时时铭记和品读我们内心深处的香巴拉,无论走得多远,走得多久,我们的心依然会淡泊明净似雪莲,只因那一路行走的风霜雨雪,能涤荡我们心灵淤积的所有尘埃。
我们走过的那些风花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