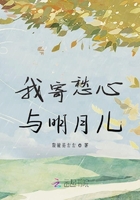东陵。
东陵府从接到宫里传来的消息开始,便阖府以待王世子与世子妃的到来,可已比预计时间晚了两日——东陵矞便无法淡定了,散出去打听消息的人一拨又一拨,却也探听不出王世子一行的准确消息,他想,是不是路上出事了,才致延误了回城时间,如此一想,便更是冷汗涔涔,急忙又加多人手分三路往世子可能来的路线去迎。
思锄虽然用心劝着郡爷不要忧心多虑,可自己心中也是吃不准,按理说世子下城应不会逗留太久,怎会过去了这几日,人都还没到呢?
一府人都心情惶惶间,却有人来报说世子殿下进城了,东陵矞连忙携府中人悉数出府迎接,果然远远看见一小撮队伍拥着一辆马车而来,那从马车中探头出来冲自己挥手的人不是叆儿又是谁呢?!他心中欣喜,却无法表达,按规矩跪地迎接。
思锄亦是高兴异常,她跪在后头,想着不月前她在此送走她亲爱的郡主,如今,竟再有福气在此迎已身为世子妃的郡主回来,不禁泪湿眼眶。她稍稍抬头看,东陵叆正由世子搀扶着从马车上下来,虽然华服精妆,但面上稚气,仍旧是她那个永远长不大的郡主大人;再看王世子,对她悉心照拂,眼神亦是温柔似水,想必,夫妻之间相处应算融洽吧……她一颗心,终于放下,与众人一道,请世子殿下与世子妃安。
府上宴请也是少不了的,虽然温融知会过不必大张旗鼓,但东陵矞依旧备了足足二十四道菜,请世子与世子妃上座。东陵叆看着坐在下首的爷爷,心中百般滋味,不知从何而起,虽然菜色明显是偏向她的口味的,但总不如当时在家时吃的香甜,再加上近日睡眠不好,胃口便更差了,她勉强自己吃了几口,便扯扯温融的袖子,说不舒服,不吃了。
温融低头看她,的确没甚精神,握了握她冰凉的手,让肃鸢陪她下去休息。
东陵叆由肃鸢扶着起了身,特地对东陵矞说了声没事,只是旅途劳累了,才进了内堂。
东陵矞担心着孙女儿,自然之后也没有什么胃口吃饭,与温融之间的交谈也相当敷衍官方,到最后,只剩温融一人独饮独酌——他看着这诺大的东陵府,无一个人不是对他拒之千里的,尤其是东陵矞。是呵,他夺走了他最心爱的孙女,换作任何人,应该都不能淡然处之的吧。连他自己,也是这样想的:他夺人之好,强人所难,理所不应当,情所不能忍,所以啊,所以,他才从最开始便告诫自己,无论东陵叆是什么样的女人,既然要了她,便要一生一世照拂她安好。——他下棋是高手,可棋局中从没有一场是牵涉人的感情的,他料不到,他会动情,会对一个不久之前于自己而言还不过是陌生人的女子动情……那不像他的作为,更不像他的性格,他不懂,无法明白,却,清清楚楚地感受到自己对她的在乎在与日俱增;那么,这不是喜欢,不是情动,又是什么呢……?就连现在,她食不下咽,精神恍惚,他都会挂心难过,甚至理智全无地吃另一个男人的醋。
他心思纠结间,杯盏数更,一下便醉了,东陵矞不敢再让他喝,忙的叫下人来扶他进房。
温融被人搀扶住进来时,东陵叆正拉着许久不见的思锄倾囊说话,见他步履轻摇,且浑身酒气的模样,立刻起身去迎,问旁人道:“这是怎么了?怎么喝得这样?”自己认识他以来,他从未曾这样没有节制地喝过酒,哪怕是大婚之时,也不过接人敬酒,从不酗饮。她心中莫名一紧,再问道:“是和郡爷说什么了?”
旁人还不及回答,思锄便立刻迎上来偷偷地扯了扯东陵叆的袖口,吩咐下头的人道:“都下去吧,这里有我。”
东陵叆看见了她递过来的眼神,明白了自己所问不妥,立刻噤了声,往身后叫肃鸢道:“你也来帮帮手。”
肃鸢听见立刻上来,帮助思锄将王世子扶上了床榻。
东陵叆看他醉得不轻,对肃鸢道:“肃鸢,你去叫厨房打些热水来,再温些醒酒汤。”
肃鸢看了眼醉倒在床的温融,福身退下去办。
东陵叆这才沿床坐下,用自己的手帕替温融擦脸。他酒后虽不上脸,但是汗却如雨而下,不一会,一条丝帕便湿透了。东陵叆想这样下去非要着凉不可,于是叫思锄过来帮手,替他更衣。
思锄却犹豫了,回道:还是等肃鸢姑娘回来再说吧。
东陵叆不解,但见她执意,也就不勉强,待肃鸢打了热水来,与她一同替温融更了衣。一直等温融睡熟,酒气过半,东陵叆才松了一口气。她又想了想这情景,想必府上不明白宫中规矩,以为她是要与温融同房的,便对思锄道:“思锄,你去把我原来的房间收拾一下,我今晚睡那儿。”
思锄一惊,道:“郡主……不、世子妃为何不与世子住一块儿,怎么……?”
“思锄姑娘,这是宫中规矩,世子与世子妃同房需求天时,在此之前,是不可以……”肃鸢解释道。
思锄这才恍然大悟,忙歉意道:“是思锄疏忽了,只备了一间房。我立刻着人去准备。”说完携了一众郡府奴婢下去张罗。
东陵叆看着她下去,眼神中的活力与精气神似乎也与她一同走了似的,立刻气力全无。肃鸢看出来不同,上来对东陵叆道:“世子妃与思锄姑娘,大概情同姐妹吧……?”
东陵叆听见她问,稍微回了些神,对她虚无一笑,道:“是……思锄……从小照料我,于我而言,与其说是姐妹之情,更不如说是……我依赖着她,她的存在,就好像弥补了……我这么些年没有母爱的缺口一样……呵……”她忽然傻笑,接着道,“可有时候,她却也比父亲更严厉,说起教条来,简直要把人念死……”
“原来是这样……”肃鸢会意道,“难怪,难怪世子妃见了她,就一下子什么病痛烦恼都没有了……”
“我也不知道……”东陵叆叹一口气,低头看了睡熟的温融一眼,“我以为,回了东陵,我就会很开心很开心,可是……并不是那样的……其实,一切都已经变了,从我嫁出东陵起,就都已经变了……我可以坐在马车上对爷爷挥手,可爷爷……却只能跪在府门口,等待着我的莅临……同样是东陵府的菜色,可与从前相比,府人也罢,爷爷也好,对我都不再是从前的态度了……他们……在他面前……永远只能诚惶诚恐……我的身份,永远是他们跨不过的一条鸿沟……肃鸢……你明白吗……我有这样一种感觉……我似乎,在选择成为他的世子妃之时,便已经割断了与东陵的一切关系了……我似乎……那时不明,如今,才深刻体会……如今,哪怕与爷爷只是院墙之隔却不可见面——这样的心痛,我如今才体会到……”
肃鸢站在她的面前,将她眼中的落寞与孤寂尽收眼底,她颇为心疼地握住她的手,道:“世子妃不要如此多虑多思,事情远没有您想象的那样严重和复杂……一切只是您的多心罢了。您要知道,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不是对面不可相认,而是,心远了……奴婢相信,只要您依旧崇爱着郡爷,郡爷依旧疼惜着您,便没有什么是可以被这场婚姻改变的……就像思锄姑娘,难道她会因为您成为了世子妃,而对您的心意有任何改变吗……?不会的……绝不会的……”
“肃鸢……你说的话,总是这样有道理。总是在我软弱彷徨的时候,如此受之有用。”东陵叆有些无力地笑,“我有时候真怀疑,你是不是万能的……”她起身,步子缓慢地走到窗边,看那皎洁明月,似乎直照进她混乱的心里,“或者是我想多了……或者是这几日总是萦绕我的那个梦,令我再度多思彷徨了……我总梦见……初见他时,他晶亮的眼神,戏谑的语词,那个他……你不知道……是我十七年以来见过最令我动心的男子……可如今的他……世子身份似乎给了他尊贵与高高在上,但也……总是剥夺我对他最初的感觉……那日被掳走,他紧张担心,我欣喜他这样的用心在乎我,可是……这几日,他……虽然态度依旧,可是你不知道……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我、我能感觉的到……包藏在他温和态度里的,是一种让人难以靠近的冷漠。”她转过身,眼内,已经是闪闪的泪,“我真的能感觉到。我也知道,他为什么冷漠——因为东陵……他与东陵之间,与爷爷之间,绝不是表面那样的简单……肃鸢——我的境地变得好尴尬,我舍弃东陵,舍弃爷爷,站到了他的身边,可他……却对我若即若离、永远有所保留……我都对他坦白过那样的话了……他到底,仍有什么放心不下的……为何回到东陵,就披上他的盔甲——为何不可信任我、信任爷爷、信任东陵——为何……”
“郡主——”东陵叆的话到一半,思锄忽然闯入,急忙打断了她的话,“房间已收拾好了。”
“……”东陵叆的情绪发泄到了一半,但看见思锄的眼神,却也不再说下去了,抹干脸颊上沾留的泪,对她说好,就来。
趁肃鸢去备洗澡水之时,思锄才敢放心地拉东陵叆到内屋坐下说话。她心思细腻,想的事情便多,对东陵叆的一切,都充满了不放心:“那个管文肃鸢是何底细郡主有没有弄清楚,怎能那样掏心掏肺的与她说那些话呢……?”
东陵叆笑她多虑,道:“你想多了,她是个好姑娘,而且聪颖,这些话,说给她听无碍的。况且,我说这些话,也是为了听听她的意见啊。”
思锄皱眉道:“才多长时间,她便能够取得您这样的信任,仅凭这一点,思锄便不可掉以轻心。”
“思锄……”
“郡主,这些话您爱听也好,不爱也罢,思锄都是要说的。我……”
“你看,你说话的开场白,与她都是一模一样的。”东陵叆摇摇头,笑道,“难怪人都说,同类难处。”
“郡主——”思锄的表情严肃起来,“思锄没有说笑的心情。您可知,您一去王宫,思锄在家日日都是担忧。蔻笙虽办事牢靠,但到底心思不够玲珑,恐怕宫廷之事根本无法于您有益。每每念至此,思锄心中都是悔恨内疚,此情可令思锄痛不欲生您明白吗……?”
“……思锄……”东陵叆似乎也有些愧疚了,不再戏言。
思锄见她终肯听自己一言,道:“这个管文肃鸢,思锄查过,身份地位绝不简单。虽然如今她父悬官家道中落,但您可知道,她父亲管仲鞠十年之前是何等风光。她管家世代袭公爵之位,在管仲鞠之时更是赐封‘文’号,从此复姓管文,何等殊荣啊……更重要的是,管文家背后有当今衍王后撑腰,十年前逃过一劫,便是王后相保。既然关系如此密切,衍后又怎会甘心放管文肃鸢在您身旁只做个宫人呢……?所以这个管文肃鸢绝不简单——”
“思锄。这些话,肃鸢都已经跟我坦白过了。或许对她的身世做了些许隐瞒,但我想,并不影响她的品格,我相信她,绝非居心不良之人,否则——凭她的聪颖、容貌、身世,哪一点,不是温融收了她的理由呢……?她又何必屈居我之下,委屈自己做一个卑下宫人……?”
“就算坦白,思锄也不能不思考——她是以退为进,还是真的真心相对。”
“至少现在……她并没有做出任何有害于我的事情。相反,我跟温融之间,若不是多亏她疏通调节,恐怕……”
思锄眉心一拧:“郡主与世子之间有疙瘩……?”
“……没、没有。”东陵叆把脸扭向一旁,“只是初相处时,总是会有些磕绊嘛。现在没事了……都没事了……”
“是吗……”思锄将信将疑,却也不再多问,却道,“另还有一些话,思锄也要告诉郡主……”
“恩……你说吧……”
“郡主在家时,心思单纯毫无心机,可嫁入宫廷,不说宫中规矩众多,只说宫中人心难测,郡主便要学会保护自己,不能让自己完全裸露人前,遭人算计。像方才,您脱口便问世子殿下是否跟郡爷之间有何不妥了,这话传出去,可是了得的……?再有,替世子更衣之时,思锄为外女,怎能逾矩替世子更衣呢?若是做了,传到王后耳朵里,郡主会落一个什么名声?挖空心思向世子献媚,以巩固自己后宫主位、抑或是想尽办法在世子身旁安插东陵奸细……?这些郡主或许都未曾考虑过,可从现在开始,思锄不在您身边,您就要学会自己思考斟酌这些问题了……王宫之中,规矩大过天,这是思锄在您出嫁之时便告诫过您的。宫中之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思锄听您方才……直呼世子名讳,这于规矩,便是大大的不合。世子虽未登基,但是是一国储君,君为上,臣为下,您虽是他的结发妻,但更是他的臣下,所以这样不着规矩的事,是万万不能的……”
“……”思锄,果然是思锄。东陵叆在听着她不停唠叨的同时,深深感觉到。她庆幸,思锄并没有拒她千里,依旧如从前一样,对她的行为言语提携规定,不遗余力……虽然这些话,她听得心中沉重不堪,但,总有一样好处吧,她忽然精神一震,扑上去搂住正在滔滔不绝的思锄——“思锄——思锄——思锄——你还是你啊……真好——你养一只叫思锄的鹦鹉让我带回去吧——我爱听你唠叨、我要听你唠叨、我太喜欢你在我身边说我这也不对那也不好了——”
“……”思锄被这样突如其来亲热热情的举动怔愣了神,一时要说的话都忘在了脑后。她目光中的精光渐软,伸手抚上东陵叆的头,气息都渐渐地变得轻薄——她忽然不忍心,再说出任何话。她明白,自己总是在打击郡主,总是希望她能够做到最好,给了她莫大的压力,从小到大。那现在……她是不是也应该开始学会相信郡主,相信这个顽强可爱的小姑娘,其实已经可以把握住自己的命运了呢……?她的下巴磕上她的头顶,忽然眼泪一滴一滴地落下来,落入她的发丝里。
——原来这个思锄,当真是个亦父亦母,睿智多思的存在。——笃笃笃。管文肃鸢在门外镇定地轻轻地敲门,道:“世子妃,洗澡水已经备好了。”